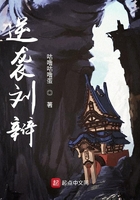隆冬。
白雪皑皑的雪原上,两匹骏骑蹶雪飞驰,追逐着几只狼狈逃蹿的饿狼。一只瘦骨嶙峋的老狼,气喘吁吁,耷拉着血红的长舌,不断回头仇视着逼近的人马,眼露绝望的凶光。
它几次试图冲上高岗或蹿进长满灌木丛的河谷,逃脱猎手的追杀。无奈两个猎手总是占尽先机,每每封死路口,逼它在没膝的积雪中吃力逃命。
当马蹄将要踏到它的股骨时,它突然反转身一跃,凌空转体九十度,利爪探出,向马背上的乔玉扑来,乔玉冷斥一声:“好畜生!”一侧身形,右掌迅疾一挥,只听一声惨嗥,老狼腰骨被拦腰斩断。象根折断的树干,飞出数丈,扎进雪壳,眼、鼻、嘴同时冒出血沫。乔玉瞅都不瞅,飞马盯住另一只大狼追去。眼见刚才的那一幕惨景,另一只狼吓的股窜稀屎,一溜歪斜,顾头不顾腚地逃跑。
“师父,看我的。”巴特热斜刺里冲来,放下弓箭,撩起袍襟。斜身弓腰,左手探出,当黄骠马奋力蹿出几步,与狼平行的一刹那,他手臂电疾一挥,一掌拍在狼头盖骨上。一声闷响,狼顿时栽倒在地,一动不动。
“好,巴特热。”乔玉勒住马缰,朗朗大笑,又说:“狼有铜头铁背之称,为师那一掌是打在背上,与你这拍在头上的一掌相比,倒是占了便宜。”
“师父又取笑徒儿啦。”巴特热面色发窘,翻身下马,拔出短刀准备剥狼皮。
远处,驰来几匹骏马,马上人拖着套马杆,几只死狼的尸体划出道道雪沟。
“大师神技,在下望尘莫及。”博尔奔察见这师徒俩一不用刀枪,二不使用套杆,就用双掌打狼,由衷地赞叹。
“雕虫小技,何足为道。”乔玉谦和应酬,在这些朝夕相处的猎手面前,无所顾忌。“各位为何在这个时候下山?”乔玉知道大雪封山季节,正是狩猎的黄金时刻,对他们突然下山感到十分惊讶。
“不瞒大师,我们也是恋恋不舍。无奈总管急召我等。据说岭南近来匪盗猖獗,商号、畜群屡屡被劫。怕波及此地,付都统衙门严令各旗抽兵协助岭南卜奎都统衙门围剿。”博尔奔察满腹怨气。
“这个冬天没了收获,开春就不好过喽。“
“我等不去不行呵,食君俸禄,为君分忧。军令如山,没法!”
猎手们七嘴八舌。
博尔奔察取出皮口袋递给巴特热,对乔玉说:“顺便给大师带些熊胆鹿茸,此物去毒御寒,还望大师笑纳。”
“有劳各位,敝人无功受禄,实在是受之有愧。乔玉一脸真诚。”
博尔奔察恳切地说:“大师何必自谦,巴特热视你如父,教养之恩无以为报。好,我等告辞。”
望着众人消失在雪原深处,乔玉才同巴特热缓缓向自家牧包走去。
巴特热瞅了瞅沉默不语的乔玉,忍不住问:“师父,徒儿的入门功夫是不是差不多啦,该可以习练正宗武功了吧?”
“咹,是不错。”乔玉眯眼望着远方的山林,若有所思地说:“是该加紧的时候喽。你的根基不错,又能吃苦,只是习武之人,当以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才是。如果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最后定然后患无穷。特别是内功的习练尤为凶险,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忧。”
“是,徒儿谨记。”巴特热点了点头,又问:“反正闲来无事,师傅,江湖自有江湖的规矩。青龙帮为什么不精研自家武功,偏偏处心积虑抢咱们的武功秘籍?”
看着巴特热稚嫩的神情,乔玉觉得有必要尽快让他成熟起来。开口道:“自古中原武林延续一种陋习,那就是门派观念太强,又喜好争强斗胜。因此,都养成了睥睨别派武功,自负本门功夫,不外授又不汲取的劣习。久而久之,本派武功只能固步自封,加上失传。落得日益衰败的下场。我师清风道长摈弃世俗拙见,独辟蹊径,在精研各派武功精髓之后,自创出迷幻剑法,掌法,内功心法这武林三绝。这本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原以为可以惩恶扬善,造福苍生。”
“当然,这确实是一件善事。”巴特热随口赞叹。
乔玉摇了摇头,叹道:“此事哪有那么简单。我师是宅心仁厚,直以为是给武林做了件好事。没想到这套武功一出世便惊世骇俗。震惊了整个武林,纷争也接踵而至。武林中黑白两道都视其为瑰宝,都已剑法中有自己门派的招数为由,索要剑谱。我师自知武林人士良莠不齐,一旦绝技落到宵小手中,贻害无穷,自己反倒成了罪人。恼怒之下,击伤四大门派强行索要剑谱的高手,隐遁山林。”
巴特热一听,急问:“那么师祖从此再没出现在江湖么?”
“没有,就连我们师兄弟四人也没见过。记住,从你师祖的教训中可悟出一个道理:藏匿锋芒,豪气内敛,高处不胜寒呵!”乔玉怕巴特热涉世不深,有意让他了解江湖的凶险。
“师傅,他们逼迫我师祖,待徒儿练成武功,把这些人一并收拾掉。”巴特热信誓旦旦。
乔玉听了脸色大变,喝道:“胡说,记住,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就象刀走白,剑走黑那样,天下武功强者多着呢。佛门武功博大精深,高深莫测;而道家武学柔中有刚,刚柔相济,不但妙趣横生,而且启迪愚顽。比如说无招胜有招,就是开封心智,提高悟性的方法。学无止境,达者为师。我师门讲究的是扬长避短,不断以别派的长处完善自己,日后不论成就如何,切不可夸耀,更不许持强凌弱,懂了么?”
“是,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过了春寒料峭的季节。四月里,冰雪融化,草莽复苏。
乔玉见天气渐暖,粮油将尽,便有心带巴特热到镇上走一趟。一来备些粮油菜蔬,向掌柜孙浩禀报畜情,二来顺便让徒弟多见见世面。还有件心事则深埋心底。
把畜群托付给邻近的牧人之后,师徒便驱车上路。
师徒说说笑笑,不知不觉过了五头山,三个时辰后,呼伦贝尔城遥遥在望了。
“师父,讲讲两个师伯和一个师叔呗?”巴特热对师门的事情有独钟。
“你大师伯和师傅一样,当年我们都在年羹尧帐下效力。西北战事了结以后,我们分别在川北、川西任总兵官。”乔玉停了停又说:“你二师伯原是读书人,却不愿走仕途,自称是化外方士。痴迷武学,在功夫方面,我们四人之中,当属他的功力为最。至于你那个小师叔么!”
“怎样,小师叔怎样?”巴特热紧追不舍。
“哼,别看她身为一个女子,川陕一带名气大着哩。日后你倘若有机会去川陕,就知道她的名头有多响!”
“看样子师父对小师叔颇有成见哩?”
“倒也不是什么成见。同门学艺,朝夕相处,即便情谊不深,也并无多大隔阂。师妹脾气暴躁,行为乖张,虽然也嫉恶如仇,但由于过于执拗,往往给人一种刁蛮的感觉。在师父老人家的溺爱之下,我们也不与其计较。”乔玉说着摇了摇头。
巴特热似懂非懂,但不住地点头。
乔玉爱怜地看了看爱徒,正色道:“原本为师也不着急,可现在改变了主意,过几日开始给你传授内功心法。”
呼伦贝尔城建城才几十年,是北部边陲重镇,南接卜奎城,西北直通喀尔喀蒙古大库伦。二道街宽敞的青石路两旁,清一色是晋商,河北、山东一带的商人由于晚来一步,被挤在边缘地带。
福生利商号就是吃了这个亏,位于街尽头,也许靠边把头的好处,倒是圈起了个大院。
乔玉赶车进了后院,早有伙计迎上来。
孙浩嘴含玛瑙烟嘴,听完乔玉的讲述,又细又小的三角眼仔细打量了一会儿缄默不语的巴特热,似乎马贩子看马那样,挑剔般地看完头又瞅胳膊和腿。
“咹,这小子长个喽,也壮了不少。”孙浩转动着灰黄色的眼珠,等巴特热被支出去后,低头琢磨了一会儿,问:“冬场完事了,现在匪盗闹到咱们这啦。我看!趁春天,附近的草场马上返青,还是把畜群赶到这里妥当些。你说呢?”
乔玉一听,知道孙浩担心在草原深处畜群被抢,想利用近处的官府的势力。
“好吧,就照掌柜的意思办。“乔玉答。
“哦!你说,这小伙子还行?“孙浩欲言又止。
“当然啦。怎么,掌柜的意思是!”
乔玉心头一紧,猜到孙浩对巴特热不放心。于是抢先说:“我说掌柜的,我放的这群牲畜总得有个帮手,巴特热吃苦是没得说,我很喜欢他。除了他,什么人我都不要!”
一看乔玉把话说死,孙浩愣了一下,随即干笑两声,尖声细语说:“乔兄弟想哪儿去啦,我不是那个意思。索伦人能吃苦、人实在。我的意思是说这小子乍一看是虎头虎脑,细看不得了!你看他天庭饱满,剑眉鹰鼻;两耳不说垂肩吧,可也像骆驼嘴唇似的又肥又大。不是!池中之物!倒像!”说到这里,他抬头向厅堂墙上的一幅褪了色的老画斜睨了一眼。那是一幅年深月久,不伦不类的玩意儿;深秋皓月,古墓苍松下,嶙峋怪石间,一只瘦虎缓缓立起,呲牙鼓须,愤然长啸。画中左侧,居然有一行谈不上高雅,却也雄浑苍劲的行书:虎瘦雄心在。
此作出自何处无人知晓,若在书香门第之家,自然不屑一顾,可在孙浩眼里绝不亚于郑板桥的真迹。这是当初他寒酸之极,决意创业之际,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画的。不但字画含义相同,更酷似他当年穷困潦倒境遇中,仍怀雄韬伟略的写照。因此,他对这幅画特别珍爱,百看不厌。一帆风顺的时候,更令他信心倍增,恨不能将天下的银两全都赚来。碰到挫折之后,每日仰视着它,则有卧薪尝胆的味道。
乔玉看透他的心思,心中暗笑。表面却郑重其事地说:“其实,巴特热日后真的发迹,第一受益当属掌柜的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