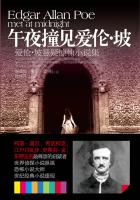离飞往香港的空中巴士起飞还有一个小时,罗少清携太太东方明瑶和两个儿子一起安静地坐在高雄小港机场候机厅里,等着检票。新年将近,机场南来北往的人流明显多起来。太太东方明瑶和儿子文汉文杰都是第一次到大陆探亲,三个人都显得异常兴奋,只有罗少清表面看起来很镇定,其实他的心也一直悬着。最近这几年,台岛政治气氛有些紧张起来。离罗少清一家不远,一个赴大陆进香的庙宇组团十多人也安静地等着检票。罗少清装着若无其事地环顾一遍大厅,猛然发现有两个戴墨镜的男人大摇大摆地走近庙宇进香团,接着那十来个人就被来人带离了大厅。
“快要登机了,那些人被带到了哪里?”东方明瑶也发现了异常,隐约感到了不安。
“情况有些不妙,”罗少清坐着没动,压低嗓音说。“那两个戴墨镜的来路不正,你叮嘱文汉文杰,让他们坐着不要乱动,一切由我来应付。”
二十分钟后,带墨镜的人又折回来了,这次他们径直走到罗少清一家跟前。
“请问,您是罗少校吗?”一个戴墨镜的问。
“你们是?……”罗少清望着来人,脸色十分平静:“请问有何贵干?”
“你们这是要到大陆探亲?”其中一个似不经意地瞟一眼坐在一旁的东方明瑶和她的两个儿子。
“不,”罗少清回答,“我们到香港维多利亚湾度假。”
“别演戏了!少校。你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大陆。你在大陆一个叫戴紫山的旅游风景区投资了一个名为‘戴紫山分时度假村’的公司,拥有五十年的土地经营权。你们是要到那个地方度假。”那人咄咄逼人地盯紧着他。“你在大陆注册的那个‘锦绣制衣’也赚了不少钱吧?你们这次前去又打算做什么呢?”
“说到这里,先生们!”罗少清悠闲地点燃一支雪茄,“如今谁还怕钞票扎手?况且,先生们,眼下到大陆投资做生意的台湾人有三四十万之众,已成公开潮流。像你们这样盘查来盘查去的,恐怕只会对台岛的前途有百害而无一利吧!”
“少跟我啰嗦!”对方恼羞成怒地喝道:“跟我们走一趟。我们要检查你的行李。”
“请便。”罗少清说。
在候机厅旁边的一间小屋里,那两人当着罗少清全家的面打开了罗家携带的行李箱。皮箱里有几斤台湾乌龙茶、几件佛肚竹雕琢的工艺品。一个特工拿起一件笔筒状的工艺品,翻来覆去瞅了半分钟,喉咙里迸出一声冷笑:
“这是什么?”
罗少清淡然答道:
“一件工艺品。”
对方步步紧逼:
“什么工艺品?”
罗少清吸一口雪茄,不紧不慢回答:
“不就是一件竹雕笔筒嘛……送朋友的小礼物。”
对方狡诈的一笑:
“哼哈!笔筒——‘必统’!你罗少校也太低估我们的智力了,这套把戏骗得了谁?!
那人把手里的竹雕顿在桌上:
“对不起!少校。我们代表‘调查局’正式通知你:你们这一趟香港之行被取消。回家等候调查。”
罗少清一家返回冈山的时候,罗茜如正由唐子萱陪着在山上滑雪。
二人沿着牵引索道升到山半腰,然后顺着中级滑雪道飞速滑下,罗茜如坐在雪上飞艇的小舱室里,吓得闭上眼睛尖叫起来。唐子萱坐在她后面,用自己坚实有力的胳臂从身体两旁紧紧护住她,两只手稳稳地抓住她握方向盘的手,飞艇一直滑驰到山脚的平坡地带才缓缓停住。
“吓死我了。”罗茜如从飞艇上跳下来,双腿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
“胆小鬼!”唐子萱一边笑她,一边说:“下一步度假村打算组建一支女子滑雪队,专门为游客提供指导。”
“我害怕这种冒险运动。我是不会加入你的女子滑雪队的。”罗茜如心有余悸地说,“我们去泡温泉吧。”
唐子萱走过去拥住茜如的肩,指着峡谷里冒起的一片蒸腾的烟雾:
“你不说我也要带你去的。到戴紫山不泡温泉是个遗憾。温泉的水温常年保持在38℃,每日有七百余吨泉水打地底溢流出来,从地眼里翻涌而出形似盛开的白牡丹,故而我们这里的人称它牡丹泉。度假村在开发温泉之初,罗总裁认为牡丹泉的名字很富有诗意,就沿用下来。走吧!我们现在就过去。”
在离峡谷口约一公里的北东断裂交汇处,五十平米内的谷底有泉眼三处,泉上建有四间浴池和池旁亭台,亭台泉边竖有一座汉白玉石碑,碑上复刻有民国二十年乡俚邑人《牡丹吟》诗一首:
无枝无杆顷刻开,
骚人搁笔费评猜。
明知蕊自波中出,
不解根从何处栽。
国色难容鱼玩赏,
天香莫遣蝶飞来。
姚红魏紫终尘幻,
散作流泉绕钓台。
“这个自称‘乡俚邑人’的,大概是个不得志的文人。”罗茜如站在石碑前,猜度着说。“为什么不是一个喜好舞文弄墨的乡绅呢?‘邑’是都城、城市的意思嘛!很显然,这个乡下的‘都市人’很不愿意与卑贱的下里巴人为伍。”唐子萱笑着反驳她。罗茜如沉思道:“你看这后面两句,更像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这是借诗抒怀。当然,身临此境,只求字面意思好就行了。哎,这温泉怎么没有管理人员?”罗茜如转过脸四周寻看,“门锁着,怎么进去呀?”
唐子萱狡黠地冲她挤挤眼,变戏法似的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
“我已经打发管温泉的老头回家去了。反正眼下大雪封山,没有游客来。”
“哎呀!你真狡猾。”罗茜如戏谑道。
他们进入一间浴池,池上雾气腾腾,空气中飘散有一股温暖的硫磺气息。唐子萱脱光衣服,“哧溜”一下溜进浴池,“来呀!”他冲茜如招招手,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迫不及待地喊另一个害怕水池太深的伙伴儿,同时从水里站起来,让他的伙伴儿看清池里的水只齐他的腰深。“真是太舒服了!我很久没有洗温泉澡了。”他开心地说,把身体慢慢浸入水中,只露出一颗毛茸茸的脑袋在水面。
受到他欢乐情绪的影响,罗茜如很小心地坐到浴池边一块圆火山石上,试探着向池底伸出一只脚,她怕池底打滑;猛不丁的她感觉到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拉住她并把她整个儿的身体托入水中——唐子萱托住她,水的浮力有效的减轻了她的重量,她感觉她就在他身体的上方飘逸……飘逸,飘飘然中,她本能地伸出双臂缠绕住他的脖颈,把沾满了水珠的脸颊贴着他的脸颊……他们开心地浸泡在温暖的泉水中,像两条自由的鱼儿在略显浑浊的泉水里快活地游弋,静下来,他们一起聆听泉水打泉眼里突冒出气泡的“咕嘟”声,大口呼吸着带硫磺味儿的空气,互相打趣着对方在学校在乡下的那些幼稚好笑的往事。天色将晚,唐子萱的手机响了,总台告诉他,度假村一下子涌来了七十几个游客,都是冲着百年不遇的大雪和滑雪场、还有温泉来的。唐子萱看看时候不早了,二人连忙穿好衣服往回赶。
“茜如,”走在森林步道上,唐子萱揽着她的腰,充满柔情地望着她,“山里陆续有游客来了,我们的推介宣传起了作用。这一段事情会很多,人多眼杂,我陪你的时间可能会很少,你要有思想准备。”
“后天我也该走了,”罗茜如抬头看着他,咬咬嘴唇,语气有些伤感:“东方伯母她们一定遇到了麻烦,我的假期只剩一个礼拜,也该走了。你放心,我既然得到了真爱,今后若是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不会再来打扰你的平静。幸福大家分享,痛苦自己承担。”
“事实上我已经不能够平静了,”他说,眼睛里透出一丝悲凉,刚才还熠熠发亮的眸子瞬时暗淡下来。“直至离开这个世界。”
沉默半晌,他似乎鼓足了勇气,脸上露出一抹羞愧。
“你看,我到现在还是一无所有,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送你,”他说着,从贴胸羽绒袄里掏出一只小木盒,打开,小心翼翼地掀开包裹了几层的红绸布,露出一串古香古色的橡子项链。“这串橡子项链是我亲手做的,二十四年前就想送给你,可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我把它给你,做个纪念吧。”
罗茜如轻轻抚摸着棱角磨得有些泛亮的小盒,托举小木盒的手微微颤抖。她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也许今天一别,彼此的缘分就尽了。这时她听见他说:
“这东西很脆弱。每年六月间,我都要把它们拿出来,放在熬滤过的清桐油里浸泡一天。”
这是一串由六十六颗小橡子串成的项链,橡粒籽实匀称,颗粒呈肚腹圆两头略尖的流线型,每一粒橡壳上都有天然漂亮的花纹,可能是多次浸泡清桐油的缘故,没有被完全掏空的橡实连同古铜色的壳衣变得坚硬如铁;一阵山风吹过,橡子串儿发出好听的“琅儿琅儿”的清脆声响。
“快收起来吧。”他轻轻催促她。
他看到她把小木盒揣进衣兜才松了一口气。罗茜如略一迟疑,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前几天唐子萱送给她的照片,照片已经微微泛黄。递到他面前:
“我要你题个字留做纪念。”
他迅速打量了一眼自己二十几年前的照片,那时自己远没有现在这样成熟,但却显得英姿勃发,对世界和人生充满了憧憬……还有野心,跟眼下这副模样真是天壤之别!他掩饰住内心里冒出的一丝伤感,把照片迅速翻扑过来,腾出一只手垫住,掏出钢笔写下两行字。
“好了!宝贝,”他微笑地看着她的眼睛,故作神秘地说:“还给你之前,我要你做出保证,回到房间里再看。”
她也笑了,
“好吧,我保证。”
接着,她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无意中瞟见了人家的秘密又忍不住要说出来,大笑道:
“我喜欢爱和永恒的话题,只不过你太悲情了一点儿。”
他弓起一根指头,刮了刮她的鼻尖儿:
“好哇!你偷看!耍赖!”
她狡黠地说:
“不过是一不小心瞥见了而已!”
然后她把照片小心地装进衣袋里,调皮地瞧着他:
“看来,你陪我滑雪,送我橡子项链,都是有预谋的呀!”
他大笑。
“你不也是吗?”
从那天滑雪到离开,罗茜如再也没有见到过唐子萱。听楼台小姐说,唐监理很忙,陪同外省来的一拨客人去了温泉。罗茜如知道他是在躲避自己,默默收拾好背囊,便独自坐出进山的旅游大巴离开了戴紫山。
转眼到了新年的二月尾,离初春还有一些日子,气温已经创下了连晴九天持续回升,五天迈过10℃大坎的奇迹。气象学家和天文学家又喋喋不休开始了他们关于是否入春的学术争论。气象台发布的预警说,近期将转阴并向多云天气过渡,但气候仍然干燥闷热。山里春意已经很浓了,山涧峭壁间迎着冰雪开放的金腰带花逐渐凋谢了,婀娜披挂的纤细枝条上有嫩蕊儿冒出来,连翘、山茶、闷头花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药药草草的花儿也陆续开了,只是落叶乔木和草根植物还未泛青,冬枯的草木更是到了一遇火星即燃的危险境地。火警的等级也从二级一下子跃升到了橙色五级,据说这是最高的火险等级了。
为了山场和度假村的安全起见,戴紫山开始了严格的封山。封山令严禁村民人等在山场砍伐树木和吸烟,进入旅游区的游客也作了严格的烟火限制。眼瞅着物干风燥,老天爷又拧拗着滴雨不降,唐子萱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每年的春秋两季是防火的重要时节,人的神经整天就得绷得紧紧的,生怕出一点儿纰漏。
3月1日,市旅游管理局林业局联合通知有一个重要会议,内容主要是森林防火防灾方面的。唐子萱安排好山里的事务,让司机开出管理处的一辆桑塔纳,打早往市里赶。车子启动的时候唐子萱还在想罗茜如——他在脑海里像过筛子样细细密密地梳理跟罗茜如厮守的日子,那一段心旷神怡的日子令他终生难忘,这样的亲密接触以后不会再有了,每每想到这一层他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痛一下。噢,是的,连旁人都看出来了,他唐子萱最近像换了个人,一改往日那种呆板严肃的表情,整日里满面春风,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是罗茜如改变了自己还是爱情改变了自己,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但是他喜欢在这类貌似糊涂的回忆中消磨宝贵的时光,这些甜蜜的回忆像一个一万年一亿年都解不开的谜,源源不断地把一些人生中最愉悦的感受打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深层释放出来,总之,他变得豁达了,原来心底里一些阴暗晦涩的东西全跑得无影无踪,头一次感觉到了天和地的开阔,爱与恨的伟大,甚至于有了一种慷慨赴死在所不辞的豪气。
会议要在明天才开,从山里到市里开车的路程也就三个多小时,时间很充裕。他答应过茜如一年去看她一次,但只过了两个月,他便忍不住想要去看她,决定只见茜如一面就走。
拐过前边的山咀就离开戴紫山度假村了,他忽然有些不放心,便让司机左打方向盘朝“大卫城堡”开去,临时到那里查看一下城堡的安全防卫工作。在那里他不会逗留太久,半个小时足够了。车子左转弯的时候,透过车窗唐子萱看见一个头戴旧毡帽、布腰带上别着一把镰刀的老汉蹒跚地避让到路边,隔老远的他就认出了他的叔丈人。虞腊贵原本住在山外的仓湾,前几年儿子闹分家,乡邻看笑话,他老脸上抹不开,一赌气便跟老伴儿搬到了界山冲,在女儿的村里起了两间土砖屋住下了。
虞腊贵脸无表情地扭头看了一眼后面开过来的汽车,顾自顺着公路往前走。一清早起来他怀里揣了两块老伴烙的死面馍腰别一把磨得锋快的镰刀,到山冲里砍田坎子。他要去的山冲就在城堡脚下,跟城堡隔着二道低矮的坡梁。山冲里有一溜儿十来块狭长的梯田,其中有女儿家的两块责任田,眼下那里的麦苗已经长得寸把高了。山冲里的田多是寒僵田,山洼子里寒水冷浸的,光照也不足,庄稼的长势总比平畈上光照充裕底肥又足的大田晚个一候二候据南朝《荆楚岁时说》记载:每个月有两个节气,每一个节气有三个候,每一个候为五天。的。田坎子上的杂草去年一年没有砍过,大田里忙的时候顾不上砍,今年再不砍掉就会影响庄稼的长势,趁着二月里闲省,草们还没发青,砍掉它们,一来可以堆积了沤肥,二来也给麦田腾出了光照。桑塔纳屁股后头扬卷起一股黄沙龙般的灰尘,在他旁边停下了。唐子萱摇下车窗玻璃,喊他:
“大爹,到哪里去?”
虞腊贵一愣,看到是侄女婿在喊他,便朝路边“啐”了一叭痰,说:
“到山冲里砍坎子。”
唐子萱打开车门,说:
“上车吧。我带您一程。”
虞腊贵摆摆手:
“我走小路,吸袋烟工夫就到了。”
唐子萱若有所思点点头,关上车门:
“那我走了。”
虞腊贵再次摆摆手:
“走吧!走吧!”
虞腊贵赶到责任田砍完了小半条坎子,歪靠在田埂旁歇了一袋烟功夫;这会儿唐子萱正和大卫城堡的经理登上被称做“大王塔”的圆柱尖塔旁的城头堡,站在塔台上朝远处的山峦了望。唐子萱叮嘱了一些城堡安全防火的话题,转身准备离开。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惊呼!对方大惊失色的叫喊引起了他的反感,于是他停住正在下楼的脚步,头也没回,皱眉问:“怎么了?”
“不好!山上在冒烟!”城堡经理惊恐地指着山下,声调都变了。
唐子萱急忙转身奔上塔台。不用指点,他已经看见了远处山洼冒起的浓烟!冒烟的山洼跟大卫城堡隔着二道起伏不大的山梁,山冲里有当地农民的十来块责任田。他叔丈人的责任田就在那条山冲里。他不敢肯定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越冒越浓的黑烟让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立即启动火警预案!”他快速地对城堡经理命令道,“紧急通知城堡所有人员,拿上铁锹砍刀,把城堡外围的防火带清障拓宽。让大本营那边的人马迅速赶到失火现场扑救!同时向镇党委报告火情、请求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