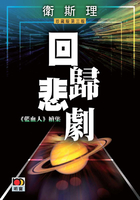“咣隆——,咣隆——”
“呜——”
天快亮的时候,苍穹笼罩在幽邃沉凝的黑暗里。雾浓浓的,雾粒挟裹着寒意凝聚成水滴纷纷洒落在地表的山川万物上,空气湿漉漉的像刚下过一场细雨。小城东北角传来火车进站减速的鸣笛,沉重的钢轮在轨道上滑行迸发出刺耳的撞击声,寂静的小城在车头粗大的喘息震颤中有了一丝儿轻微的骚动……卢西鸿熬了整整一个通宵,赶写一份部长催要得很急的发言稿。昨天在部长办公室领受这份差事时的激动不安,熬到深夜时只剩下疲惫焦躁的份儿了。
城关报时的钟声敲响三下的时候,卢西鸿顺利的脱出了底稿。文章的框架搭起来了,成功的文字游戏——他把文人墨客精心构思的这些用来扬名利己或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东西称做“文字游戏”——如行云流水般的文思从脑子里喷涌而出的滋味儿真是妙不可言。他又体验到了在大学里完成某篇得意之作后的那种感觉:亢奋,躁动,又包容有莫名的宁静,这些混血感觉带给他的好心情把此前的惶惑不安统统化解得烟消云散。
他起身冲泡了一杯浓苦的咖啡,搅凉后一古脑儿喝掉;在他身上十分难得地保留着不抽烟的良好品性。
不可否认,从党报刊物上剪辑拼凑出文稿并不会损害他的人品,没有谁会因此追究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因为大家都这么干。尤其是涉及方针政策性的东西,从文章的立意布局到措辞都应该严谨到无可挑剔——要知道,“代言人”的水平经过各种公众场合抑或新闻媒体的传扬检验后,就直接代表了领导的政策水平!这就需要你具有很大的灵性、悟性、韧性……他卢西鸿就做到了这一点。凭借天生的一份聪颖和勤奋,他是县委大院里获得上下口碑极佳的几个年轻人之一。那些老成持重的科股级同僚都是他要尊敬的上司,他们都是从全县几十万人中间选拔出来的人尖子,像许多平凡人一样,他们之间明里暗里也会有矛盾,但有严明的纪律约束着,他们不大可能做的太显眼,结果就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大家都把友善的目光投射到对彼此都毫无威胁的年轻人身上。卢西鸿呢,似乎更适合充当中间的斡旋人。结婚前在罗少弼那个老共产党人那里碰了一个软钉子以后,他现在采取了多听,少说,当着倾诉对象根本不评论张三李四的隐蔽策略。当然——偶尔,这个谦逊的年轻人在一些重大场合表露出来的才能常常令那些热衷于挑剔的人大吃一惊:他善辩,能言,滔滔不绝地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地推出某个论点……少年时代留下来的喜好浮华的缺点,不但没有引起非科班出身资深科员的反感,他们反而把每年一次评先表模的有限名额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都投给了他。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除了有一些喜好虚浮噱头的小缺点外,对他们的恭从几乎达到了让人感动的地步……凡此种种,同事相争遗留的豁隙无疑怂恿了年轻人勇于攀登的野心,但他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这中间刺激个人欲望的也有一些明心不明口的繁琐小事,包括有一天他无意间从一个资深科员的慨叹中感到了一丝儿怜悯以及对自身前途的恐惧,猛然醒悟到在人尖子堆里等待提拔是一件何等愚蠢的事情!打那以后,他毫不迟疑地打心底里重新掏捧出学生时代那颗蓬勃向上、激情涌溢的心,审视它的每一次搏动程序,小心谨慎地剔除掉不合时宜的预激征侯群;他开始瞧不起那些日渐走向衰落的老同事,“你愿意亦步亦趋步他们的后尘吗?”他不止一次地追问自己,“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像他们那样,从镜子里读出一张饱经风霜愁苦潦倒痛悔万分的老脸吗?不!那决不是我卢西鸿的脸;决不能让比我更年青的后来者窥见我头上耻辱的白发。”
整个夜晚,卢西鸿除了搁下笔杆想一阵子心思外,都在伏案赶写他的文章。天麻麻亮的时候,他完成了自己的杰作,接着又仔细斟酌,修改了一些词句,让它们读起来更上口一些。尔后,骑上崭新的风凰牌自行车,趁早把材料送到部长家里——他掌握得很精确,五点一刻部长就起床了,此刻恰在楼前草坪旁散步呢。部长看见他的到来,很亲切地停住脚步,接过厚厚一叠材料马上返回到客厅仔细审阅;卢西鸿怕文章有需要改动的地方,便跟随部长一同来到客厅,部长在审阅文稿时脸上没有表情,但卢西鸿从部长偶尔扬动眉心的细小表情里,看出部长对手头的东西很满意。只是,部长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由他卢西鸿去担纲文稿的起草,想想所担当的风险也足以让他后怕一阵子的了。
他对自己拥有的能量不再怀疑了。
从部长家出来,他首先想到要填饱肚皮,然后呼呼睡它半天。
大街上秩序很糟,行人占了自行车道,骑自行车上班的男女趁势蹿上街心并不宽畅的机动车道,在一段街坡斜缓的路段几辆高级轿车夹杂在拥挤不堪的人流里尖声摁着喇叭,它们拥有再高贵的身体也无可奈何地蜕变成一只低贱的蜗牛。三十年前栽下的法国梧桐已经在大街两旁篷空架起巨大的浓荫,那是一些高大阔绰的速生树种,卢西鸿有很多时候走在大街上喜欢抬头老远地、长久地凝望它们,心下很为这些冠名“悬铃木”的中国树被洋人引种出境后滑稽地取名“法桐”而忿忿不平;他弄不懂林学界为何不把它的冠名权夺回来。——不过说心里话,卢西鸿没有更多的闲情逸致搅和进这样一桩国际学术悬案上去,因为从根本上他并不喜欢这些悬铃木,讨厌那些盲目骄傲的灰黄色精灵,秋末春初把果实上的茸毛弄得漫天飞舞,那玩意儿随风吹洒进行人的脖子里眼里,刺痒刺痒的难受……卢西鸿这会儿眼睛里就钻进了一粒悬铃木茸絮,他只好停下车子揉弄眼睛。
卢西鸿心情很好,他一边善意地诅咒那些该死的果球,一边锁上车子,顺势拐进街旁边的“工农兵”汤包馆。空气中飘出的骨头汤浓腻的香味儿强烈地激起了他的食欲。是的,他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从昨天傍黑到现在仅仅只喝了一杯咖啡提神。
“工农兵”汤包馆是一家老字号“知味观”更名而来,上下两层楼营业。底层门面口一溜字儿摆开四只废旧汽油桶改造的炉灶,每只糊了耐火泥的灶沿平台都煨煲着十来只黑不溜秋的尖嘴小砂罐儿,每只砂罐口沿儿盖有一爿薄瓦石,煮沸的汤汁从尖尖的罐嘴豁八处往外“噗嘟噗嘟”冒着烟气儿,不断有倒腾空了的砂罐重又添满搁放在炉灶上,油腻的汤沫子溅洒在燃得很旺的炉火上“滋滋”直响,四周的空气里便掺和了略带焦糊味儿的骨头汤的醇香。
绕过炉灶往前走是大餐厅。
十来个过早的食客很随便地围坐在木条连钉的框形窄凳上吧叽吧叽喝着热汤。卢西鸿要了一笼香菇汤包、一瓦罐心肺排骨汤,独自端上二楼。楼上食客比楼下少了一半儿,三、五个老年男人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今儿个汤包皮儿擀得透不透、馅儿掺了多少精瘦肉、笼屉垫底儿的松针是新采摘的还是现成的闲话……各自时不时的故意拿镇江宴春楼的蟹黄包子、扬州名副其实的用麦秆吸汤汁的汤包……炫耀一番,以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尔后严肃地往汤包上淋倒滚烫的骨头汤汁,等到汤包薄皮儿浸透了一层油淋黄,再拿竹筷夹起慢慢品嚼。卢西鸿饶有兴味儿地瞅着那些老食客不厌其烦地重复枯燥繁缛的套路,也尝试着把汤包淋上排骨汤汁儿,味道果然比他蘸酱油佐料鲜美得多——不过他没人家那份儿耐心,三下五去二吃掉了笼屉全部十二只汤包,接下去大口喝光了瓦罐里残剩的汤汁。
一顿早餐花去了四块多钱,满嘴弥香的骨头汤让他有一种意犹未酣的感觉。现在他又想起了妻子。虽然他们夫妻不算十分和谐,但这并不妨碍他爱她,这种感情在维系夫妇之间法律纽带的大红结婚证书被他收藏进箱笼里的那一刻起,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些许疏淡,很多时候他无从获知妻子心里在想些什么,她眼里渐次显凸的淡漠似乎永远是一个谜。
“隔着千山万水,还有一条台湾海峡,”扶着车把他发了一阵呆,“她会想我吗?”这个念头一冒出来,连他自己也有点儿脸热心跳。妻子经常搬出种种借口拒绝丈夫的爱抚,弄得做丈夫的尴尬之余,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而妻子呢,每一次的托辞总是那么的得体,让他无法把自己的意念支撑下去。久而久之,激涌的潮汐几乎不再有了,他在家里变得郁郁寡欢。
独自叹息了一阵,他打算回家躺下以前,看看信箱里有没有茜如寄来的信。
收发室设在医院大门旁侧一处矮平房里,负责收发的门卫是一个干瘦老鳏夫,鼻梁上架一副老式花光镜,佝偻着腰正在分发厚厚一摞报纸。
“老师傅,有我的信吗?”卢西鸿隔着一层玻璃窗,问。
门卫低了头,从镜片后上方瞅了瞅来人,认出了他,“嘿”地一笑,打诨说:“耐心等着吧!它们还在路上走咧!”
卢西鸿有些失望,转身准备离开。
“哈!等一下。”老头儿叫住他,“有你爱人一封信,你捎回去吧。”他从一只高大木柜抽屉里拣出一封信来,递给卢西鸿。
卢西鸿随手接过信,瞟一眼投信人的地址,不由满腹狐疑。谢过门卫,回到家里,他把那封署有“上紫溪管理区”的信扔在桌子上;躺在床上却无法安睡,不知怎么的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唐子萱那家伙!猜忌的念头一闪,他被它吓了一跳。索性从床上翻身爬起,迫不及待地抓过桌子上的信,“卑鄙的家伙!”他骂了一句。
动手拆信的时候,他有些犹豫。假若信里并无他猜疑的那种男女私情,那他怎么跟妻子开口解释呢?可是,男人的妒嫉一旦冒出来便无法缩回去,它会比女人小肚鸡肠式的阴毒更加可怕。
他坐在床沿上思索了一会儿。尔后迅捷跳下地,从写字台抽屉里翻找出一只剃须刀片儿,又找来一块干净毛巾,稍稍弄湿,小心翼翼地把来信的封口处夹压在湿毛巾中间——做完这一切,他便一屁股坐到藤皮圈椅里,静静地等着。时间不长,纸头稍微润湿了一些,他用稍稍颤抖的手指捏着薄如翼蝉的刀片儿,轻轻切拨开糊精粘住的封盖,抽出纸笺。
他读到了这样的内容:
罗茜如同志:
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