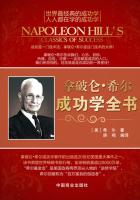春茶采过三遍,凭它多嫩的芽头也算是夏茶了。经过一个春季阳光的反复照射,苍老的茶树沉积凝析出浅浅的褐色素,顶芽停止了生长,完全展开的老青叶红梗子渐渐多起来,整株茶树只剩下树梢少量嫩叶可采了。——采茶人有时候也顺带撸几把见嫩一些儿的老叶子混在嫩叶子中间充数,老叶子的茎蔓比起油软的嫩叶来脆生得多,稍用一点儿力就脆裂成了碎渣片,茶成品也多是零杂的粗叶片子和炒得焦糊的青梗红梗的混合物。茜如她们管这种粗采粗制的夏茶叫大叶煸。大叶煸分清汤红汤,茶汁清绿的叫清汤,酽红如马尿的称红汤。
炒茶锅被砌嵌在一个倾斜成150°的土灶台上,罗茜如几乎是半站半趴着在翻炒锅里的青叶。锅里的温度差不多达到了200℃,她快速松散地抓起一把青叶,叶子在手掌跟烧红的锅底之间擦出“咝咝”的声音。翻炒的老青叶子在半秒或者更短的时间里漫过炒茶人的双手,不一会儿功夫便变得蔫里巴叽的了。这已经是第五锅了。山上还有新采摘的叶子在源源不断地运送回来,堆在屋角落一只大篾筛里。在她旁边,还有一口大锅在做着跟她同样的工序。下一道工序就是把杀过青的茶叶倒在一个大案板上,由其他人捻揉成形。
汗珠子牵着线儿地往下掉,她完全顾不上去揩了。摔进锅里的汗珠子“嗤”的一响,巴在锅底的盐渍很快被翻炒的老青叶子覆盖掉了。炒茶间弥漫了一股青叶子的香气,罗茜如的嗅觉似乎变得迟钝了,只觉得头晕脑胀的难受,她害怕自己支撑不住栽进炒茶锅里,便跟在案板旁揉茶的叶蒿芙替换了一下。趁着青叶还没倒进锅,叶蒿芙压低嗓子对罗茜如说:“听说场里要发茶叶了!”罗茜如昏头昏脑地问一句:“要不要钱?”叶蒿芙答道:“鬼晓得!我也是听他们说的。听说大队每年都分茶叶到户。”
中午收工,罗茜如看到几个采茶女一窝蜂地朝场长办公室那边跑,便问叶蒿芙:“她们跑什么?”叶蒿芙说:“可能是要分茶叶吧?走,我们去看看。”
二人来到场长住的屋子时,屋里已经挤满了人。挤在前面的人都在兴奋的“叽叽喳喳”的说笑,场长李向阳站在一个两屉木桌旁边,桌上堆了一堆分包好了的茶叶。会计唐子萱在一旁往领过茶叶的名单上划“√”作记号。场长一边发纸包一边喊:“莫挤!莫挤!人人都有份儿!”拿到茶叶的人喜笑颜开地走了,到屋子里只剩下叶蒿芙罗茜如时,罗茜如分明看见场长看她的眼神儿怪怪的,连旁边的唐子萱也怔在那里。罗茜如扫一眼桌子,桌上只剩下最后一包!她扭过脸跟叶蒿芙对瞅一眼,叶蒿芙也是一脸疑惑。场长极不自然地冲叶蒿芙干笑一声,话却是说给罗茜如听的。罗茜如还从没见过场长像今天这样结巴:“……罗茜如,你……大队里没……说要……分……”
罗茜如立刻明白了对方话中的含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转身就走。叶蒿芙使劲一拽,扯住罗茜如的衣裳。愤愤不平地质问道:
“凭什么不发罗茜如的?!”
唐子萱低头不语。场长“吭哧”了半天,才呐呐地说:
“这也不怪场里。场里也就是多发半斤茶叶子的事儿。不发罗茜如的,是大队里的规定。”
叶蒿芙穷追不舍:
“大队里什么规定?”
场长似有难言之隐,嘴里咕哝了一句连他自己都听不清的话。
唐子萱这时抬起头来,说:“罗茜如,你拿我的那份儿吧。”
罗茜如脸涨得通红。她使劲甩掉叶蒿芙拽住她的手,转身跑了出来。
“叶蒿芙,”场长对站着不动的知青说,“把你的一包拿走吧。不分罗茜如的,那是大队里早就有规定。不光是她,大队里被戴上‘四类分子’坏帽子的人以及四类分子的子女有一百多人,都没有分茶叶的资格。贫下中农就是分了,年底要扣掉三毛钱,也不见得就舍得喝。我屋里的就把它里三层外三层拿旧报纸裹了吊在屋梁上,逢年过节还等着拿它招待客人呢。你瞧我,不也是跟大伙儿一样喝白开水么。”
茶叶事件没几天,夏季中耕就开始了。往年地里残留的白茅、狗牙根、马唐以及莎草经过一个冬季的凋蔽,一俟过了立春雨水就发疯地蔓延滋长。起初它们只在松软的泥土下悄无声息地抢夺地盘,贪婪摄取茶农们慷慨施给茶树的养料,等到它们尖利硕白的茅尖得意地拱爬出地面,向空中伸展开密密匝匝的、窄细柔韧的叶片,成了生命又一轮新生覆盖的杂草时,便成了茶农们最憎恶的东西……阴暗潮湿的茶根隙间莠竹狗尾巴草也争相繁衍。成熟的狗尾巴草在微风中摇曳毛茸茸的穗头,数不清的草籽便遗落在土壤里,遍生出更多的狗尾巴草子孙……五月里,这些杂草到了非除掉不可的地步。
上工的钟声响过,人们三三两两拖了锄把,懒散地钻进茶树丛里。一年里长达六个月的除草、中耕叫人厌恶得直想找个地缝儿躲起来。上头分配下来的化学除草剂又少得可怜,各小队自然都打算截留下来撒在比茶叶重要一百倍的稻田里,——在人们看来,茶叶子充其量是大田经济的一丁点儿补充,绝对没有必要把宝贵的财力物力浪费在茶盅上头,场里十来个劳力就是现成的除草机器。而茶场里这些廉价的人,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逃避每年几道的劳作工序,唯有把锄头拖得“咣铛”响来发泄胸中的牢骚不满。尽管人人都晓得这些只是图了一时泄愤,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百把公顷茶园的草还得一锄一锄地除掉,好脾性的场长对众人几次三番带抗议性质的胡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连一句狠一点儿的话也没有,拖一拖也就过去了。——“茶地不挖,茶芽不发”嘛,每年6-7次的锄耕才开了一个头儿呢!至少春茶前、春茶后和夏茶后的三道是逃脱不了的。让人最难以忍受的还是5月初已经升高的气温,毒辣辣的日头当空照着,停下了采摘的茶树越发茂盛了,苍绿的梗叶上落满了肮脏的灰尘,人一钻进去,暴露在外的脸和胳膊上划拉出一道道又黏又黑的污迹。
罗茜如钻进茶垅里先是站了一小会儿,密匝匝的茶树间宛若一个闷热的大蒸笼,烤焦了的泥土散发出枯叶腐肥的霉烂气息,直熏得人气短胸闷。两行茶树间的地垅里长满了浅浅一层杂草,春茶前的一次中耕只锄掉了才刚萌动的浅层草根,几场春雨和春茶采下来,一些深根性的杂草和夏季开花结籽的杂草又窜起了老高,人们必须在结籽成熟以前将它们铲除掉。罗茜如叉开双腿,弓着腰,开始用力挖地。春上踩板结了的土壤翻挖起来很困难,干硬的土地一锄下去只溅起一股尘烟,一锄深的土层才渗出些许潮湿的痕迹。在板结的阳坡地牵刨白茅草根须得格外的小心,那些盘根错节的草茎脆生生的,稍一使劲儿就扯断了,若想再把它完整地刨出来就麻烦了。阴坡低洼地省事一些,牵起一蓬草根慢慢地悠扯,最长一蔸茅丝草林林总总可以扯起一丈多长——每每遇到这样的好事儿,罗茜如便像打了胜仗,扯草的欢乐便一时冲淡了茶叶事件带给她的伤害——不过这样打胜仗的概率小得可怜,而那些进化了千百万年的茅丝草们总是伸出分蘖发达的根系紧紧抓住泥土,让企图铲除它们的人望而生畏。往前挖过一截地,罗茜如转过身把刨起的草根碎屑耙拢到一堆,等回过头来搂到地头暴晒,晒蔫了水份的草根就失掉了繁活能力,这也不失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的笨办法。——罗茜如就那么一直缓慢地往前挖呀拣呀,身上的衬衫早已汗得透湿,头也嗡嗡作响。于是她停歇下来,扶了锄把大口喘气,一边腾出一只手捶打酸疼酸疼的腰背。猛抬眼瞅见姜鸽手里攥了一把白嫩的甜草根,擦掉根上的泥土,正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儿的嚼着。姜鸽也瞟见了罗茜如,冲这边扬扬手中的草根,“喂——,甜的!”她咋咋呼呼地喊道。也许是只顾剥草根吃,姜鸽的锄把斜拄在腋下,明显地落到了众人后头。
罗茜如勉强回笑一下。她知道姜鸽不屑于去跟旁人争抢那一丁点儿可怜的工分养家糊口,一个棒劳力辛辛苦苦、脸朝黄土背朝天又能挣得了多少呢?姜鸽根本懒得去计算是八分钱还是一角伍分钱,这些对她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要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知道省革委主任的千金一筒饼干就抵他们十天半月的辛劳,不定会气成什么样子。
山脚那边水库的水位消退了一半,裸露出一轮一轮水浪浸蚀过的痕迹和大水渍死的枯矮灌木。空气对流层有一层火焰样炽热的气流在粼粼流动。水库下游的田畈里,即将收割的麦子金灿灿的。这时的罗茜如心里只顾盘算着往后两三个月里艰苦难熬的除草工作,当然不会知道全大队二千多双眼睛都眼巴巴的盯在即将开镰的小麦上:大部分田亩的麦子是瞒了上头偷偷种植的,公路沿线一些大田栽种的双季稻那才是留给上级检查的“样板田”。丘陵盆地的气候远比平原地带寒冷,季节温差和日间温差相对要比那些温暖地带平均低上摄氏3℃——5℃。早春里,农民们把在温棚里用干柴温火育出的秧苗移栽到大田的那阵子,田里的水温还寒僵手脚呢!7月里人们抢收罢了早稻又慌忙火急地栽种下晚稻,上头日头晒、田里水温蒸,秧蔸子就那么要死不活的在田里耗着,赶上好的年景,晚稻的分蘖性也赶不上中稻,到了10月间收割起来的多是一把低矮瘪壳的干草禾!除去每年交的国家公粮,剩下的连全队老少的基本口粮都成问题。所以大家伙儿掐着指头算来算去,栽种双季稻大不如一季麦一季稻来得划算。再说,仓湾地处偏远,平日难得有区上一级的领导来此走动。虞腊贵每年带领各生产小队的队长会计到区里开完三级干部会回来,对各队的双季稻亩数总是象征性地指手划脚安排一番,暗地里他们都是通的,在显眼地带弄上十几二十亩样板田应对上头走马观花式的检查,年底再往生产队会计的年报表上做一些手脚,年年也就这么糊弄过来了。猛不丁的听说省革委主任的千金挑中了仓湾这地方插队锻炼,起初确实在一些生产队长中间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但时隔不久,人们就大大落落地把悬起的心放回了肚皮。嗨!大半年过去了,乡下人不仅连冯写樵冯主任的影儿没瞧见一次,就连他的红旗牌轿车屁股后头冒的烟儿也没瞅到过,只听说他到紫溪区视察过一回农业学大寨的情况,在区上逗留了一个上午的工夫就掉头回了省城。这当口自然不会有人把姜鸽指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讲给他听,区干部还不至于傻到自讨没趣儿的地步。趁了主任大人高兴的当口,瞎编一通谎话极力夸奖姜鸽在乡下怎样怎样的虚心,怎样怎样的吃苦耐劳,是一棵革命的好苗子等等等等。心里巴不得县里马上给下个指标好让她上大学或招工回城,才不辜负省委老领导对这块红色土地的垂顾呢!
早晨上工不久,大队书记虞腊贵带着民兵连长到茶场来了。茶园除草中耕似乎不是他们此行最关心的话题。
“今儿个春上银芽产量超过往年,”虞腊贵拣一块地势高的岗坡地站定,喜形于色地大声宣布说。他的话整面山坡的人都听到了。“区上捎信来了,我们场里的琵琶魁尖已经送县里、省里展览了。据说亚非拉朋友很欢喜喝我国产的绿茶哩。”停下进度缓慢的手头活儿,人们很高兴有机会得到短暂的休憩。出于恭敬,他们大多懒洋洋地把下巴搁在锄把上,尽量把身体躲在齐胸深的茶树荫里。只有场长一个人在全神贯注地听,其余人的懈怠一开始就藏掖在无精打采的眸子深处,无聊地去瞅老青叶梗子上的纹络,或去瞧头顶上没有云彩的一片天空。看得出来,大队书记今儿个很高兴,笑眯眯地在密匝的茶垅间搜寻姜鸽的影子,直到看到她了,这才又兴致颇高地接着往下说:“能够跨入支援世界革命的战斗行列,是我们贫下中农最大的幸福,——姜鸽哇,放你两天假,给你老爹冯主任捎两斤芽茶尝尝鲜,也算是我们仓湾全体贫下中农一片心意呦。”说到这里,连他自己也禁不住哑然失笑,刚才脱口说出了“老爹”的称谓,是当地人最通俗最亲切的乡间俚语,明显地蕴含有对尊敬的冯主任充满亲情的阶级感情在里头。
姜鸽抿嘴一笑,高兴得差点儿扔掉手里的薅锄。忙乱中她用一只脚背勾起歪倒在树枝间的锄把,掩饰突如其来的喜悦。她的尊贵究竟没有被人遗忘,尤其在苏静虹、罗茜如两个身份低贱的走资派子女面前,她姜鸽的高贵显赫更显得鹤立鸡群了。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剩下的就是尽快逃避掉繁重单调的除草中耕——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演变,原本绷得紧紧的大脑神经一下子松驰下来,好不容易才树立起来准备吃一阵子苦的意志顷刻间溃退了,本来就够勉强的心里也填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欢喜,以前多次有过的懒散的惬意重新渗扩到周身每一个细胞。面对当地土皇帝的当众奉承,姜鸽没觉着有什么不妥,反倒有些洋洋得意。因而,在听到让她回家的话以后,姜鸽只是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在另一茶行间悠闲闪着一条腿儿的叶蒿芙。令她诧异的是,对方脸上也表现出一种亢奋神情。叶蒿芙起先把注意力放在脚下新翻起的泥土上,翻松了的泥土里裸露出几簇白嫩粗壮的茅根。寻常咸菜萝卜就饭甚至白开水泡饭的日子实在太寡淡了,那些带了甜味儿的草根的诱惑真让人抵挡不住。她连忙扯起几根,迫不及待的擦净,塞进嘴里大嚼;嚼碎了的草根汁儿甜甜的,沁出一股青草淡淡的芬香……她的注意力完全沉浸在淡淡的、略带芬香的甜草汁儿中,书记的一番话只像一阵轻风刮过耳旁,让她阴差阳错的听岔了意思。天真地想,既然大队书记放了姜鸽的假,接下去就会放其他几个知青的假,要知道,她们自打下乡以来,半年多了还没有回过一次家呢!再说,大队里不那样一碗水端平的话,怎好意思当着众人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