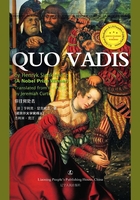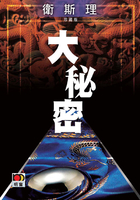惠娟倚在床上抚摸腹中孩子的时候,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黑漆漆的窗外偷窥着自己。这种怀疑使她在随后继续对腹内的孩子进行爱抚的几分钟里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宁。于是她关掉了房间里的电灯,悄悄摸索到通向走廊的那扇房门口,冷丁拉开了门,果然发现那张脸还迟钝地贴在窗玻璃上。她无比厌恶地低低喝了声:“贼头贼脑的,你在这里张望什么?!”
年迈的杨幼春这才扭过头来,出乎意料地朝媳妇笑了笑,那双眼睛一眼看去像骷髅头里的两个漆黑的小洞,令人不由得毛骨一阵悚然。在媳妇生气地瞪视下,她依然带着那种令人恐怖而又迷惑不解的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的大肚子,讷讷地说:“当年我怀着大原他们兄弟几个时,肚子也跟你一样圆一样尖哩!”她在说着这句话的时候又慢慢地朝惠娟走近了些过来,一只鸡爪般瘦骨嶙峋的小手冷丁朝媳妇的大肚子上狠狠地一把摸去!惠娟近乎恐怖地“嗳”了声,倒退了一步,那只鸡爪般的手还牢牢抓着她的一角衣服不放。浑身顿时又起一层鸡皮疙瘩,将那手死命打了下去,又喝了句:“你该下去睡了!”便逃似地退进房里,转身飞快地重新关上了那扇房门。一会儿就听见走廊里响起一阵惯有的嗯嗯的喘息声和拐杖叩在楼板上的橐橐声响。
多年前,惠娟就对婆婆长年住在他们家里而喋喋不休。大原其实对娘也比她孝顺不了多少,但他凡事都喜欢跟她对着干。很多时候他们本来都完全可以不谋而合的,可是一旦话由她先说了出来,那么他无论如何也要改变原先的主张。何况这些年来,每次他们夫妻吵架,娘总会在背后替他出谋划策。为了对付妻子,大原一次又一次地打消了要把娘赶到志原家里去的念头。
孩子生下来后,慧娟越发不愿意和婆婆一起居住在这同一幢房子里。好在机会终于出现了。她在那天早上抱着孩子去娘家前把一矮箩花生薄薄地摊晒在水泥道地上。下午回来时,发现那花生一下子少了许多,且用畚篼盛过的痕迹都还在。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时,她还故意让花生留在那里保持着原样,让大原卖完肉回来亲眼目睹。他们趁杨幼春不在时,突然袭击了她那间堆满了纸箱和塑料袋的屋子。果然搜出了一竹篮还来不及送到志原家里去的花生。共同的利益和看在那个已经会牙牙学语了的儿子的份上,这回大原终于跟女人站在了统一战线上。每天出门之前,他们都很有共识地拔下了一个个的房间的钥匙。把那些锁不起来的米缸谷缸麦缸豆缸的缸面都抹平,一一做上记号。他们由此推断出杨幼春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充当着搬运工的角色。她把志原家里的烟酒鱼肉偷偷地搬运过来,再把他们家的粮食土货悄悄地搬运过去,以此分别来讨好两个儿子。每次她把这一个儿子家里的东西搬运到另一个儿子家里去时,都会用一种充满了惊险的口气告诉受惠者——
“这是我趁他们都不在时拿过来的。你那兄弟家里多得很,可是他们宁可烂掉也不肯拿过来给你们!”
两个儿子只有在这时才都变得极其听话温顺,在老妈的嘱咐下,果然都是守口如瓶。
有一天夜里孩子哭闹起来,惠娟下楼去倒开水,见婆婆房里的灯还亮着,便往那门缝里张望了一眼,只见杨幼春正光着上身带着她不久前刚被莫名其妙丢失的一个海绵胸罩在房间里得意地走来走去。那胸罩像两个望远镜一样垂挂在她那早已是一败涂地了的胸前,显得无比宽大而又滑稽。但那两个坚实的虚假轮廓使她一再无比自恋地一再扭头望着映现在玻璃窗上的自己。惠娟不由得又好笑,又一阵寒毛凛凛。当她怀着那种无法形容的厌恶和恐惧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大原也正在为家贼难防深感头痛。夫妇俩的决定终于得到了统一。
志原尽管同样不欢迎娘住到他家里去,但他没有理由拒绝。他在镇上和县城里都分别拥有了一个大套后,又在村里批了块地皮花了六七十万块钱盖了幢小别墅。他跟白歌住在二楼,儿子亮亮住在学校里,寒暑假回来了就住在三楼。杨幼春过去后自然是住在一楼了。每次和白歌在一起的时候,杨幼春那两个漆黑的小洞总会一眼不眨地盯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媳妇。她相信自己年轻的时候肯定也跟小媳妇一样漂亮迷人,要不然那时候的骆家三兄弟、剃头阿坤、箍桶阿三怎会围着自己团团转?她甚至常常觉得白歌就是自己的过去:乌黑的长发、袅袅婷婷的身姿和一双烟雨迷濛的眼睛。有一次为了证实这种幻觉,她又伸出那只鸡爪一样的小手,在白歌露在无袖衫外的修长而又雪白的手臂上狠狠拧了一把!她感到了一种饱满和温润如玉,使得她对自己年轻时的肌肤的印象得到了吻合。于是她又咧开嘴笑了,笑声嗡嗡,如呻吟。疼得差点儿落下泪来的白歌那一刻里努力克制着自己没有像她的妯娌那样发作。
那天晚上志原和白歌刚行完房事,两个人正躺在那里养精蓄锐,白歌忽然缩进志原怀里惊恐地说:“志原你听听,什么声音?”志原睁大了眼睛:“有什么声音?没有的。”白歌说:“你再听听,好像就在窗外。”志原凝神听了会儿,似乎果然隐隐约约地有那嗯嗯的喘息声,便说:“是什么虫子在叫吧,要么老鼠。”白歌说:“不是的!”志原说:“不是那又会是什么?难道是人?”白歌想想是人也不可能。福龙轻轻拍了她一下说:“放心睡吧,别疑神疑鬼了!”
翌日一早,白歌正在厨房里做泡饭,杨幼春拿着个碗过来了。当她嗯嗯地呻吟般喘息着走到白歌身边的时候,白歌怔了怔,倏然变了脸色,随即扔下手里的锅盖就往楼上跑,一把推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志原,又羞又恨地告诉丈夫:“昨天夜里是、是你娘!”此后,一连有好几个晚上她都拒绝和志原做爱,任是志原怎么安慰她、爱抚她,她都坚信杨幼春就站在漆黑的窗外嗯嗯地呻吟般喘息着,透过窗帘一眼不眨地偷窥着他们,即使后来每次志原都把窗关结实了,把窗帘也拉得严严的,她还是摆脱不了被那两个贴在窗玻璃上的漆黑的小洞盯视着的幻觉。偶尔有一两次她实在拒绝不了志原,也总是慌张得仿佛跟人在路边苟合。
于是志原和大哥经过商量,各自拿出一半钱来,给娘单独造了两间小平房。杨幼春对儿子们给她这样的安排十分不满,她喜欢住在他们那漂亮、洋气的楼房里。
晚年的杨幼春在她儿子媳妇们的眼里是以一种恶作剧的姿态离开人世的。若干年后,他们对她死之前的那些恶摆布还耿耿于怀。他们只津津地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并没有过多地去想这个垂暮老人,在那两间小平房里过着怎样寂寞枯燥的生活,在自怜自赏和絮絮叨叨中逐渐枯萎,对她的变态有的只是厌恶和痛恨。他们以比饲养一只猫还要花得少的精力给她提供着一日三餐,并为此而感到理直气壮。如果她满足于这些提供并无声无息,他们也许会更加置她于不顾,这使得对寂寞有着跟年轻人一样不耐烦的杨幼春,在她最后那段日渐枯萎了的岁月里,必得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出来,才能重新赢得关注。
她第一次坐在大原家屋门口号啕大哭时,邻人们都以为她跟大原或者慧娟吵了架。但随即发现大原家的门关得紧紧的,除了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大哭外,再无一个人。遂问她为何而哭,说:“大原志原我都囡囡呀、心肝宝贝地从一尺三寸抚养大,又辛辛苦地给他们一个个地成了家,盼着他们能有个出头之日。如今官也当大了,房子也都气气派派地造成起来了,就都一脚把我往外踢了!”
随后她又躺在大原家的屋檐下大哭。再次闻声赶来的人们根据她所哭的凄厉程度都相信她刚刚挨过大原的一顿打。当人们把她从地上搀扶起来,并再次问她为何而哭时,杨幼春抹干了眼泪说:“我哪里在哭?没有人理我,我是躺在地上嬉戏的。”众人面面相觑,话尽管未从口里说出来,却都能从对方目光里读出一句话——“这个老太婆神经有些不大正常!”
她第三次又坐在大原家屋门口哭泣时,就有人跑去告诉大原。怒气冲冲的大原铁青着脸一回到家里,便将一面盆冷水哗地夹头夹脑地泼在娘身上,又操起一把扫帚,厉声喝道:“你再哭!”邻人们远远望见杨幼春一声不吭地从地上爬起来,拄着拐杖湿淋淋地走向她那两间小屋。
她开始坚决不在自己那两间小平房里做饭,也不上两个儿子家里去吃轮饭,整天都哼哼哈哈地躺在床上呻吟着,以此来告诉他们她病得不轻。她知道儿子们不敢不把一日三餐都给她端过来,因为旁边都有邻人们的一双双眼睛看着的;她也不怕他们故意迟迟地给她送来,稍迟一些她就打开了所有的门窗,拍着床板在那里“肚皮饿煞哉!肚皮饿煞哉!”地大叫,喊得半个村子里的人都听得见。大原给她端饭过来了,她瓷着眼睛望着他:“你是谁呀,怎那么好送饭来给我吃!”大原瓮声瓮气地说:“我是大原你看不出来了么?”她还是一脸的茫然,望望窗外近在咫尺的大儿子家自言自语:“我儿子大原的家到哪里去了呢?我刚才找了好几个钟头怎么都找不到?”大原回到家里跟惠娟说:“老太婆神经不正常了,连我也不认识了!”惠娟说:“你相信她你才有毛病!她是有意在调排我们!不信你试试看,让人拉一车桔子过来叫卖,还起价来比你还要好!”
直到有一天中午和傍晚都不再听见她叫唤,也不再看到端进去的饭跟重新端出来时数量上有多少变化时,他们才确信她真正病倒了。那是在她跟大媳妇一次口角之后。忍无可忍的惠娟在那天早上一只手艰难地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吃力地端着一碗米粥走进那两间小平房里。杨幼春瞧瞧大媳妇一张绷得紧紧的脸,故意将那粥碗打翻在地上,碗没有碎,粥倒是流了一地。惠娟盯了婆婆一眼,把孩子放在地上,蹲下身去将地上的粥一把把地掬起来放回碗里,再让杨幼春吃。杨幼春一扬手,又哗啦一声抹了那碗和筷。惠娟忽然笑起来,对婆婆说:“怎么不愿意吃?我还想着那个车水棚可惜已经没有了,要不然你也可以住到那里去,饭也不用我们顿顿给你送了,你可以跟上山人一样饿了自己爬到草棚门口去挖泥吃!”她看着婆婆的脸慢慢变成死灰色,便抱起孩子正要幸灾乐祸地离去,忽然听见背后低低地骂了句:“你这个烂婊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怀里的小杂种是怎么来的!”她微笑着扭过头去亲切地望着这个年轻时像蝴蝶一样招展在男人们面前的老女人,那两个漆黑的小黑洞似乎是她这一辈子的两个句号,她忽然跟男人一样嗬嗬地笑起来——“再能烂也烂不过你啊!你烂死的那些人要是都过来咬你一口,你就只剩下半具骨架子了!”
她随即就看见婆婆的身子像冬天里的蛇一样迅速收缩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连好几天里,杨幼春都表现得出奇的安静。这使她那两个儿子和媳妇们都看到了一道他们盼望已久的希望的曙光。他们抑制着内心的无比欢喜,将那几碗饭菜端了来又原封不动地端了回去。直到第三天,他们看见她一直昏迷不醒的样子,这才装模作样地请来了乡卫生院里最蹩脚的一位医生。巴不得那些平时经常可以听到的医疗事故这会儿也在这两间小平房里发生。期盼着的事情不但没有出现,那位庸医破天荒地也有了妙手回春的时候。第一瓶盐水还没有挂完,杨幼春忽然睁开了脸上那两个漆黑的小洞,直起头来大声叫道:“超度!”
接着她把头重新落在枕上,眼泪汪汪地望着守在她床边的志原说:“上山人带着张凶神恶煞的脸几次三番地拿着个索命的套子想把我套走,都亏我爹在旁边护着我。他说他在阴间里还是只能吃泥块,身上也没有一件好衣服。我答应给他做一回道场超度他。这道场你们要替我给他尽快做呵,免得他再拿着那个索命的套子来套我!”她说完这话的时候,目光已经开始在饥饿地寻吃的了。她吃完了一碗稀饭、一盘番茄炒蛋和一个几乎跟柚子差不多大的苹果,才感到心满意足。她又告诉小儿子,她刚才在阴间里还见到了二儿子中原和金凤,说中原的小孩子有多大了,金凤的哮喘病已经好了,也结了婚,跟女婿两个人一起来接她到他们家去。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精神饱满、声音响亮,全然不像是一个刚刚从昏迷状态中醒过来的病人。神情沮丧的志原在后来离去时,她还不忘嘱咐他一句——
“别忘了超度你爹的道场!”
她后来跟前来探望她的那些邻人们谈论起她过去的那些都已撒手而去的情人们时,不无得意地说:“他们都在那里一个一个地等着我,为了夺我他们都打起来了!”
但当她最后跟死亡之间还相差那么一口气时,她又气喘吁吁地惊恐地睁开眼来——
“我过不去了,他们都一个个凶巴巴地挡在那里要跟我算帐!”
她对儿子和媳妇们在她忽然重新有了食欲后表现出来的冷漠和失望耿耿于怀。即使在临终前的几天里,她也没有放弃折腾他们的机会。她故意把大小便拉在床上,作出奄奄一息的样子,看着他们快快乐乐忙进忙出地为她准备后事。而在他们万事俱备只等她把那口气咽下时,突然又忽地像火焰一样精精神神蹿跳起来!但这场游戏里最后吃亏的还是她自己。经过几次欺骗后,两间小平房里最后只剩下她自己响亮而又孤独的哭喊声——
“肚子饿煞哉!”
“我要死了,大原志原惠娟白歌你们怎还不来!”
隔了老远的路,张家听到了,李家听到了,住在福龙家的兰香也听到了,却没有人再来搭理她,都在那里笑道:“杨幼春又来了!”
兰香最后一次见到杨幼春就在那两间小平房里,那是间跟简易房差不多的小屋子,里面光线很暗,印象里还有一股刺鼻的尿臭。涎水从嘴角边一直挂到胸口的杨幼春似乎已经不认识了她,脸上那两个乌黑的窟窿更深了些。这个曾经骄傲、风骚一时,曾经从她身边夺走过一个又一个男人的女人,现在终于也落到了这般地步,变得跟一只飘荡在枝头上、被秋风抽打得干干瘪瘪的老茄子一样丑陋可怜了。可是那一刻里她怎么也幸灾乐祸不起来,她分明看到了自己不久也将会到来的同样一幕。
后来看见志原,她忍不住数落他:“你现在虽然算不得是我的女婿了,官也当大了,但我还是要说你——你娘啊,你们还得多进去看看她。”
但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她跟志原说着这话时,杨幼春已经无比孤独落寞地走向了那个有她父母、男人、儿女和情人们的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