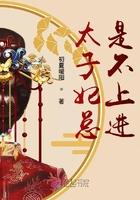“我低头望着蒂洛,”月亮说,“在山坡高处座落着一所修道院,两位修女站在钟塔上面撞钟。在大道上,有一辆旅行车在行走,喇叭一直呜叫着。修女往下盯着车子,年纪最小的那位眼里,含着一颗泪珠。汽车喇叭声小了,修道院的钟声还在回响。”
第二十四夜
月亮说:“几年前的哥本哈根,我从一家贫苦人的窗子望进屋里,父母亲都睡了,只有那个小儿子没睡,伸出头向外望着。开始我还以为他看的是那摩落地钟,可是孩子看的是母亲的纺车。它是孩子最心爱的东西,可是他不敢碰它,怕挨打。母亲纺线时,他看着嗡嗡响的纺锤和转动的轮子,心想,要是自己也使用纺车就好了。过了一会儿,一只小赤脚,又一只小赤脚,伸下床来,站到了地上。原来是小男孩,他穿着破衬衫,轻轻走到纺车前面纺起来。纺车发出嗡嗡声,母亲一下子吵醒了,她往外看,‘我的上帝!’她说着,惊慌地推了推身边的丈夫。他睁开眼睛,看着那忙碌的小家伙,‘是伯特。’他说。
“我的视线离开简陋的屋子,看到了梵蒂冈的厅堂。那里面大理石神像有劳孔组雕、缪斯。我又把光线移到了尼罗河组雕上,这是一位大神。靠在狮身人面像上,他沉思着,在回想那流逝的岁月。一群小女童在他的周围与鳄鱼嬉戏。在伸入河中一块三角形地上,一个小男童手臂交叉着坐在那里,望着河神,与那个小男孩坐在纺车旁的表情是一样的。这里大理石雕成的小孩是多么的生动可爱,它自诞生以来,岁月已走过了几十年。当然这是多年前的事了。”
“昨天,我望着锡兰岛东海岸的一个海湾,”月亮接着说,“那里有树林,有海堤,有古老的地主庄园,有小镇和教堂。许多船只点着火把在水面驶过,船里音乐飞扬,一只船里坐着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他让我想起了梵蒂冈尼罗河组雕和大理石神像,让我想起了那间简陋的小屋,格伦尼街上,伯特穿着旧衬衣,坐在那里纺车。时间的轮子转过来转过去,大理石里雕出了新神祗,他是伯特·曹瓦尔森。”
第二十五夜
“请看一幅法兰克福民用建筑图,”月亮说,“它座落在一条犹太人居住的狭窄街道入口处,主人叫罗特希尔德。你从大门望进去,楼梯两旁挂着灯,仆人捧着银蜡台,向坐在轿椅里被抬下楼梯的老太太鞠躬。房子的主人光着头,恭敬地亲吻着老太太的手。老太太是主人的母亲,她和蔼地看着儿子,看着仆人。仆人们把老太太抬进街上一间狭窄黑暗的小屋。老太太原来住在那里,她的孩子在那出世的,她们的幸福之花在那儿开放。她想,如果她离开街上的破烂小屋,也许幸福就会离他们而去。”
月亮今天只讲到了这里。而我满脑子是狭窄、破烂街里的老太太。她只要说一句话,泰晤士河畔就有一所属于她的房子,波利海湾就有一幢属于她的别墅。她说:“如果我离开那间破旧的屋子,我的孩子说不定会远离幸福!”这虽然只是一句迷信话,但我们能从这句话里看出一位母亲的良苦用心。
第二十六夜
“昨天早上,那座城市所有烟囱都还是冷的,”月亮说,“忽然,一只烟囱里有一个男孩的小脑袋冒了出来。男孩把胳膊歇在烟囱的沿上,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妙极了!’他说。这是他长这么大头一次爬上烟囱。‘现在我可以看到全城了,’他说,‘太妙了。’”
第二十七夜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座中国城市,”月亮说,“我照在那些长长的、光秃秃的墙上,一条街道有时也会有一扇门,但门是紧闭着的。连房子墙后面的窗子都被软百叶窗帘遮着,只是寺庙的窗子透出一丝灯光。我从那里望进去,一只只神龛里供奉着神像,全被花缦幢和垂蟠旗遮得看不清楚。每一尊神像前都有一个小祭台,上面供着圣水、鲜花和蜡烛。大厅里高高在上面的是佛陀,在他脚下,坐着一个年轻的出家人。他在念经,可是又心不在焉,他的脸绯红,头低垂着。这个可怜的宋弘,他在想着街上长墙后面小花圃里是否有活干。干那样的活,比他在庙里照料香烛更显得自然。他又在想,是不是他的罪孽太深,如果讲出来,便会受到惩罚。他的思想是否敢和洋人的船一起飞向他们的家乡,那个遥远的英格兰国度?不会的,他的思想没有飞那么远。然而说回来,这种思想引出的罪孽很深,它在寺庙里,在诸佛神像面前犯下了罪过。我知道,他的思想在城边上,在乎坦的阁楼上。那里,栏杆用瓷砖铺贴,摆着插了大朵白色风铃花的花瓶。栏杆边上,坐着漂亮的裴小姐,她正看着面前的玻璃缸,里面养了四条金鱼,她用筷子慢慢搅动鱼缸里的水,眼神发愣。她在想什么呢?也许她在想,金鱼穿得多么时尚,它们的生活多么安逸,不想吃,不想喝。这种生活,裴姑娘十分向往,现在她的思想飞出家门,飞向寺庙,但不是因为那里有神的缘故。可怜的裴小姐,可怜的宋弘,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却被我的寒光阻隔断了。”
第二十八夜
“海面十分平静,水透明得能让我看到水底下奇特的植物,”月亮说,“这些植物就像树木一样,将它们粗壮的树干向我伸来,鱼儿在它们的顶上游来游去。天空中,飞过一群野天鹅,其中有一只天鹅的翅膀沉下去,落到了水面上,它把头埋在双翅之间,静静地卧着。晨曦透出彤云,这只天鹅鼓足力量飞起,飞向喷薄欲出的太阳,飞向空中航队飞去的蓝色海岸。”
第二十九夜
“你再看一幅瑞典的画。在靠近罗尔克森河岸边,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女修道院。”月亮说,“我的光线从格子窗射进宽阔的拱室里,一些帝王长眠在这里的巨石棺柩中。墙上,悬挂着一顶王冠,那是人世间权力和金钱的象征。但是,它是一件木制品,只是被涂上漆、镀上金,蛀虫已经蛀穿了那只王冠,蜘蛛在皇冠与棺木之间结上了网。当蒸汽船顺河而上行驶在山脉之间时,经常有一位外地人来修道院观赏这拱形墓室,打听帝王的名字。外地人看着被虫蛀穿了的皇冠,微笑着。逝者,安息吧,月亮记得你们。”
第三十夜
“挨着大道有一家小旅店,它的对面是一间大车马棚,”月亮说,“我从敞开的天窗望进去,里面是一间肮脏的屋子。火鸡在梁上睡觉,马鞍放在马料桶里,屋子中央停着一辆旅行车,主人在睡觉,车夫也伸直了四肢在打呼噜。男佣人的房门大开,床上乱糟糟的。厩棚那边的地上,睡着流浪音乐师一家人,竖琴靠在他们的枕头边,狗儿躺在他们的脚旁。”
第三十一夜
“一个小城镇里,”月亮说,“我是去年看见它的,今晚我又在报纸上读到了它,却很不清楚。在小旅店里,耍熊的艺人坐在那里吃晚饭,熊被拴在柴火堆的背后。那可怜的熊,它谁也不会伤害,尽管它看去很吓人。在阁楼上有三个小娃儿玩耍,最大的有六岁,最小的最多两岁。门开了,原来是那大熊,它上楼来了。”月亮说,“孩子们被吓得要死,纷纷爬到一个角落里。可是它还是把他们三个全找到了,用它的嘴去碰他们,但是一点儿都不会伤害他们!他们轻轻地拍拍熊,它躺到了楼板上,最小的那个男孩翻身爬到它背上,玩起捉迷藏来了。最大的那个男孩拿上鼓咚咚地敲了起来。熊立起来,用后腿开始跳起舞来,这真好玩!孩子们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同伴,就开始操起步来!一、二,一、二!’有人来扭门,门开了,是孩子的母亲。她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脸色刷白,口半开着。可是最小的那个男孩高兴地大喊:‘我们在扮土兵操练!’紧接着耍熊的艺人就来了!”
第三十二夜
寒风袭人,云块在飞奔。偶尔我可以看见月亮一眼。
“我低头看那些飞驰的云,”月亮说,“我看到大块的影子掠过大地!最近我看见一个监狱,门口有一辆门关得死死的车子,它正要把一个囚徒带走。囚绕在墙上划了几行什么东西作为告别。那是一支曲子,他的心声的流露。门开了,他被带到外面,朝我望着。云飞到我和他中间。他踏上了车,车门关上了,皮鞭响了起来,马车进入了浓密的树林里,我的光不能追随过去。可是从监牢的铁栅我看到了里面那划在墙上的最后的告别。我的光线只能照亮几个音符,绝大部分对我都处在暗处。他写的是安魂之曲,还是欢乐的颂歌?他是奔向死亡还是奔向亲人的怀抱?我低头看着那些飞驰的云,我看到大块的影子掠过大地!”
第三十三夜
“我喜欢小孩,”月亮说,“小家伙们特别有趣。在那些娃娃想我时,我就从窗帘和窗框之间悄悄地溜进屋子里去。看他们脱衣服是很有趣的。小肩膀首先从衣裳里露出来,接着胳膊便滑了出来,或者袜子被脱掉,一只可爱的小腿露了出来,我亲吻了它。
今晚我从一扇窗户望了进去,见一大帮小家伙。有一个四岁小姑娘已经能很好地向上帝祷告了。母亲每晚坐在她床边听完祷告,她就可以得到母亲的一个吻。母亲一直坐到她入睡。今晚最大的那几个有些闹,一个穿着白色的长睡衣,用一只脚在那里跳;另外一个站在一张椅子上,他在表演,让别的孩子猜;第三个和第四个把玩具整整齐齐地摆在抽屉里。母亲坐在小家伙床边,让他们都安静下来,小家伙要做祷告了。
那四岁的小姑娘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白白的细被单,两只小手叠放着,小脸很是严肃,她高声地祷告。‘怎么回事,’母亲打断了她,‘说完请赐给我们每日的面包后,你还说了点别的,我没听清楚,告诉我!’小家伙很不好意思地望着母亲。
‘别生气,亲爱的妈妈!’小家伙说,‘我请上帝在上面多抹些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