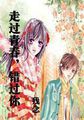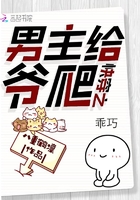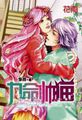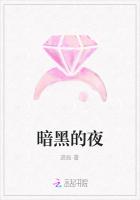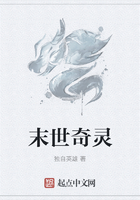在我带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即将离开东圩工区的前一天晚上,我的老上级那位曾经给我做过革命思想教育的孙工长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了我。我是东圩工区有史以来第一位通过上大学而改变命运的出生于草根家庭里的青年,因而工区里曾经的同事及其家人都将我视作一名努力拼搏奋发进取的成功人士,尤其对我从千里迢迢的远方赶来吊唁有一种莫名的钦佩甚至感动的情结。
煮海为生的盐工与大海相依相守数百年,已然被波澜壮阔的大海坦荡的胸怀所感染,形成了盐场人独有的粗犷豪爽热情坦荡的性格。他们与生俱来地崇尚朋友间两肋插刀义薄云天的友谊,虽然他们只是些凡夫俗子并不能够真正理解亮平日里所流露的思想和表现出的某些荒诞不经的举止,但他们在心灵深处毫不例外地都将亮这位诞生在咸土地上的知名作家视作一种荣耀,并因此对我这位亮生前的好朋友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
这是我在东圩工区工作几年来见过的最为丰盛的一顿晚餐,文明食堂雅座包间内的圆桌上摆放了二十几道飘浮着荤猪油香味的菜肴。除猪牛羊等肉类是孙工长让人从场部的副食店购来外,其它的菜品都是海边或盐场常见的特产。既有野鸡野鸭野鸟野兔这些野味,也有鱼虾贝蟹这些海产品。虽然我是只未见过大场面的菜鸟,但我知道工长今晚的宴请规格已超出场里制定的接待标准,也明白工长对我的热忱接待出自于故人的一份真诚的情谊。
包间里坐着我熟识的工区党政工领导和本地有点身份的人,还有一位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却显得异常精明干练的贵宾,他是来自省公司党委宣传部的景副部长,是省公司党委宣传部派来吊唁亮的代表。饭桌上的氛围其乐融融,众人热热闹闹地喝着俗称小美人的洋河酒,那是当时我所见过最好的接待用酒。大家相互之间或分享各自听来的奇闻趣事和少许荤段子,或请教景副部长对某些道听途说的相关时政的见解,或讲些我离开之后几年来盐场发生的变化。那晚,我从宴会热烈的气氛中充分感受着浓浓的乡情,这种心情只有那些长年漂泊在外的人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