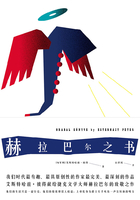在广州期间,恰逢母校校庆,因此与许多同学取得了联系。
校庆后几天,步新和老茧就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见到了近二十年没见的一些同学。其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夜深,躺在床上,一些词语和人物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涌现,这些词语和人物牵拉着我的心脏,渐渐地,漫满了我整个胸腹。在这些词语和人物的影像里,我看到那些逝去的青葱岁月正如水流一般缓缓浸透了我的回忆的心,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女性所独有的特质。在写作《相亲》时,她们的这些特质悄无声息地钻到了小说的人物里去了。
在广州期间,我写完了《相亲》。写完,先给步新看。
步新看完,过来拉了我的手,说:"我喜欢你的叙述方式。也喜欢你给我安排的那些个千奇百态的相亲人物,寡淡的生活都变得趣味死了。你常来广州和我住好不好?保证让你不断获得新的写作的灵感。我实在是太寂寞了。哎,对了,简,你也和我一起去相亲吧。你虽然比我小点儿,可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
我看着美丽优雅的步新,笑着点了头:"成,常来,和你相亲去。"
朱珠读后乐不可支,说将来如果还接着相亲,一定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给我,让《相亲》成为一个别人不忍释手的连续剧。
三个好姐妹笑抱成一团。
我在本篇小说的前言里还要特别感谢步新的父亲,离休的某军区司令员。正是他在闲暇时常常与我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不拘官仪敢喜敢怒地聊大天,才使我得以将《延安笔记》里的韩建业这个人物描写得更为血肉丰满,个性鲜明。老将军和我讲述的故事,讲述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和成长轨迹,讲述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一些杰出的人的命运怎样被无情地改变,那些横遭变故的人又怎样沉默地面对和抗争……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在写作《延安笔记》的时候胸腔里注满了感动奔溢着永不枯竭的激情。
在《相亲》里已提到过老茧是我和步新朱珠的大学同学。他是众多大学女生们信赖而没想过要爱恋的那样一种男人。校庆见过他以后,我们便有了联络方式,节假日就间或有了些短信往来。
老茧读了我给步新和朱珠写的《相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原来在搞写作呀,太好了,正巧我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发泄到社会上,肯定会引起动荡不安,给你提供素材,让你写篇精彩的小说不正是两全其美的事?"
我就笑了:"老茧你不是开我玩笑吧,你个大文豪,谁不知道你在大学就写小说?我只是个半吊子,现在离职在家,没事干,玩票而已,哪能浪费了你那一肚皮珍贵的素材?"
"我原是预备自己写的,可我现在打算走一条男人的路,去考公务员!经世济民、定国安邦,那才是我老茧该走的路!你的才能,就不用我来吹捧了吧,我们班的同学们早把赞美的言辞都搞到了极致,我要跟风,都无处下嘴了。哈哈。"
我们在电话里大笑。
"好吧,既然如此,我再客气也太那什么了。我的三脚猫功夫能够叫你老茧入得眼,也就勉为其难吧,将来写出来若有不尽意处,尽可以打骂丢石头啊,不要怕伤着我。哈哈。"
老茧有点儿怕步老爷子,就把我从步新家里约出来,去广州的茶楼喝早茶。断断续续地,我们谈了三四次,对他的故事他的思想他的郁闷他的雄心略有了些了解。因他实在太忙,要复习要找实践经验,再有,他考的是湖南的公务员,所以便相约了如果有问题再电话联系或者回湖南后再面谈。
因为写老茧的故事,我与老茧的往来比从前多了些。有时候要在细节上略作些沟通,以不伤了老茧故事里的人物们在现实里的和气。
但总体上,我们的友谊仍然清淡而不浓密。正如故事写完后,与老茧举酒为庆时引用的杨简的语录一般:仕宦以孤寒为安身,读书以饥饿为进道,骨肉以不得信为平安,朋友以相见疏为久要。
老茧终于考上公务员了,因为表现出色,被某主要领导选为自己的秘书。后来他为我引见过一位气质忧郁的女子叶子,是他在政府里的同事。奇特的是他们同时也是早年在最初参加工作时的同事,都换了好些单位,最终却又遇到了一起。
因为与叶子的相识,我写成了这部不是长篇的长篇小说中的最后一章《爱情是个病》,藉以劝慰那些义无反顾地扑向虚幻光亮的迷狂的飞蛾们:生命脆弱珍贵,活着为最紧要。
这是后话了。现在我在这一章里要写的是关于费诚、小茜和阿瑞的故事。
从广州回到长沙,爱晚亭的枫叶已经红了。
叶脉湿润叶色嫣红。这湿润嫣红每年都会如期而至,经了风霜歌咏以守望者的姿态在秋天岩岸般伫立。在这种伫立中,我的心悄然回胸。
老单位湖南电视台又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游荡了几个月的我忽然也萌生了重新归纳自己的念头,于是一拍即合,准备又从自由散漫回到秩序规束里去。
于是在写完《左脸的微笑》后,我就将小说交给了老茧,由他替我去处理或发表或修改或保存的事。
《左脸的微笑》也是有原型的。费诚、小茜、阿瑞的原型都是我的朋友。但所有具体的细节信件往来的文字全是我的虚构,只是大体的故事脉络取自他们。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给费诚(权且称他为费诚吧)去了一封信,征询他的意见。
费诚兄好。
与君交谈,是兴味盎然的事。
真写起小说来,发现它的好处是,可以任意抒发自己的想象,不比新闻或纪实的拘宥。
"简以宁"是我虚构的作家名字。
生活有所赐予,而小说越过生活又使生活更多姿态,这也许是写作的一种趣味和幸福了吧。:)
那天与你在线上聊到关注底层,整个社会的底层,农民里最穷困者,市民里最窘迫者,无产无业者的困境造致的种种思想言行,和他们人性里本初的诚善……在这些方面,虽可感,但确实没有真真切切地深入思考和入心入肺地体察过。其实幼年我也在乡下长大,但困苦的记忆不复深刻,父亲虽在远方工作,但身边一直有母亲呵护。母亲一度曾是语文老师,使我们兄姊三人从小略有文艺气。故此使我对乡村的记忆甚至有些唯美。这是遗憾和汗颜之处。聊可辩解的是,生活万千形态,各有困顿,各有亮色,随意撷取都可算得一种呈现?
另有思虑的是,写农民的作品,或者是学商士……者在读;写男人的,女人在读;写商人的,文人在读……诸此等等,读者与作品人物的不太重合,这虽有不完美处,但或许也是好事。生活互为补充,也能形成认知上的互动。
当然更谐和的情形,常常是每个阶层的人对自己所属的生活最能共鸣,最有心灵相通之感。比如看《马大帅》,东北人最起老劲,我到东北,发现那里的人无不对《马大帅》喜爱莫名,而本土的辽宁教育社的《万象》却知之者寥寥。而在北京,校园林立,学生学者们《万象》《读书》《随笔》等常在案头者不少。……
凡喜好者各有不同,就特别感慨包罗万象的写法之难。
对二月河先生的关于几个王朝的作品,很有敬畏感:庞大,纷繁,充满合理的想象,主要部分还不能离史料太远,即使那么长,读起来仍然流畅而愉快。那天你谈到获奖的《张居正》,非常惭愧,我尚未开读,但我想,作为万历年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它的写作难度不会太小。之前我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世间已无张居正,印象很深。他生前逝后的命运,那个时代官场的机体,上至古怪的皇帝,旁及形形色色的官员,以及他力行的改革政策,各阶层在这种政策下的纠结……所以那天你一提,我就觉得一种浩瀚扑面而来,似是被网住了,言语无从伸展。
当然,小说写作是一个漫长的修习过程,想慢慢来,从一些细部开始,写好了细节的个人的,渐渐而再扩充开了去。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个人的也是大众的嘛。呵呵。
现在我正拟写几个中篇,其中一个约略算得一个情感类或者情绪类故事,想以你与小茜的某些故事为原型,未知你同意与否?当然只取些脉络,细节全部由我来虚构,不会触及太多你的隐私,呵呵。
描述的文字不那么刚直利落,而取温和柔软式,不晓得能达到情意的效果不?
某天在读佩索阿时,得到一些些启示,于是在人物的预备上设置了双重作者,好像就形成两个并轨发展的故事,且在外围的故事中,还可以以作者和读者的姿态观望小说里的人物,以破解生活的困局。
我读某期杂志里何立伟先生的散文数章,对他写事的角度从小不从大,小中又见大,文字的韵味取轻不取重,轻亦不失重,挺喜欢。当然,已是名家了。
我自己也写些随想类,开了两个博客,一般是想哪写哪,以前还算勤劳,但坚持不常,今年以来写得也少了。
更从前还写诗,年轻人共有过的经历。现在诗的灵感却渐渐地渺微了,读到肖先生的诗,就不由长生感慨。诗是文字的梦想,如梁实秋先生所言,一个人如果达到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经风吹雨打,方寸间还能诗意盎然,他是得天独厚,他是诗人。
在信里面瞎谈些胡乱的认识,以补聊天之不及。即时说话有时候常会犯些拘谨,从容些的文字似乎就自由些。你也许常作讲座或者演讲或者电台电视台直播等等,修炼得敏快的思维和口才,常令我应之不及唯有拜望。
有时候读先贤们的简牍往来,很有一种阅读上的欢欣。是故不揣观点的浅陋,贸然抛砖,望得老兄的玉言锦句呢。
今日又有雨,风也悠然入窗,似是一个可人的凉爽秋天。:)
祝好。
简以宁
10.27
费诚很快给我回了信。
以宁好。
得知你写小说,很高兴。我早就惊叹过你的文才,那时候我就说过你是台里的文化领袖。
你尽管写吧,不必顾忌我。生活如戏,戏如生活。无论你把我写成什么样子,那都不是我,是你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我只会欣赏,不会挑剔。
近段时间略有些忙乱,所以不及与你讨论文化艺术。待我闲了,总是要好好炫耀一下我的所思所读的。哈哈。
主持大局,总有些意想不到的艰难,当然也有意想不到的快乐。幸得安安在我身边,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使得生活不至于跌宕得太厉害。上回在线上我与你提到过她吧?大致的情形就是我说过的那些。
北京的枫叶开始红了。如果你来京的话,正是赏枫红品果脆的好时节。顺便也带安安与你见面,让你过目。呵呵。
祝你快乐如意,文思如飞。
费诚
10.28
引子
老茧收到简发来的邮件时,已是数天之后了。邮件里发来了她最近写的一篇小说,她说交给他全权处理,她要出去旅游了,到世界各地去转悠。对于小说的源起和写作经过,她略略地作了一些说明。
她说:我早年的一位朋友供职于画院,她先生在企业界。然他们的内心却常常焦虑苦闷不堪。因皆忙于事业,无暇生儿育女,所以年近不惑,内心就成了一个隐痛。女友时时想脱离现在的工作,去办一个幼儿园,以慰自己一颗热爱孩子的心。而她先生也常想以大学教师作为职业,在商场的险恶环境中神经绷得疲惫了,于是特向往那一片宁静和缭绕的学术气息。两人为此被折磨得憔悴不堪,身心分裂,双双患上了抑郁症。在一次聚谈中,得悉我目前赋闲在家,看书写字,便开始向我倾吐内心的苦闷,既为我补充写作的素材,亦经过交谈疏散了他们的闷苦。无形中我倒是成了一个心理按摩师了。
从前写稿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肩着高于生活的"意义"。为意义而意义的挖掘难免不陷入疲惫,如今就想放下意义的重压,真正体会生活里原本存在着而被忽视了的种种微波,一点点酸一点点甜一点点苦一点点……生活是广阔的,而广阔的原始是细节,就如一望无际的海亦是由点点滴滴的海水汇聚而成。放下端着的肩膀了,下得笔来便随感而至,比之踌躇再三的掂量,更有自然的流畅。而交给你,也更有一点意义以外的意义了吧。
她在此处还发了一个吐舌眯眼的扮怪脸谱。老茧忍不住笑出了声,一贯素面严谨的她居然也学会了调用这些新式武器,看来心态上真的是放松了。
她还说:光只是听,仅能触及到人和事物的外围,难以身临其境、心临其境,写出来的也定然只是皮毛,而难触及底里。怎样才激发出自己潜意识里的共鸣,将朋友的苦痛化为自己的苦痛,将他们的焦虑变成自己的忧惧?抑郁症,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今天,早已非一两个人的专享,而是已经蔓延开来,在大片大片的人群中扩散着。以前还不大觉得,这次为了接近我小说里人物的内心而扮作实习者走进一个朋友的诊所,才发现各类稀奇古怪的心理症状之人是如此之多,发病的原因是如此之广。
看到那么多的奇情怪状,为使自己感同身受,写起来就有些煎熬辛苦。本想将情节设置得离奇些,以获得阅读的冲击力,可生活很笨,其实盛容不下多么磅礴的曲折惊险,即使是虚构,我的文字也只好尽力沿着费诚、阿瑞们可能的原生态的生活情节走下去。
当然毕竟总是小说,朋友夫妇的经历真的只是一个提示的影子,人物费诚或者阿瑞并没有遵照他们生活的事实来写,大部分是糅合了一些真实的社会现象的。比如看电视里的某些女性节目,里面很多情感的故事和婚姻的纠结就让我深为感慨,也给了我一些写作的提示。
写出来现在这样与朋友的生活面目全非的小说,怕遭他们误会,怕他们一一地将情节往自己身上套,烧焦了我。所以交给你,说明缘由,你周转得开的才能或可让我解脱些臭骂吧?
我旅行去了,你多珍重。
读了简的信,老茧更觉她是一个率性的女子。与她从认识到今,她一直飘忽不定,无论是性情还是行踪。但她仍然给了他一个可信任的感觉。
小说取了一个奇怪的题名叫《左脸的微笑》。老茧按捺住好奇的心思开始了小说的阅读。
一 阿瑞:遇
这天她乘火车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一个出版社组织的作品讨论会。她不是非去不可,因为不是讨论她的作品。但她已经有好些年被囚禁似的困在单位,上班,回家。她是杂志社仅有的两个美编之一,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春节没有一个连贯的假期,于是哪儿也不曾去。在这个世上她似乎成了一个隐身人,虽是任谁也囚禁不了的她的心依然可以在远方飘游。另外,这次讨论的作品是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向来羡服她对文章的欣赏力,认为她常能挖掘出作者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作品的魅力。她以她的品读才能让朋友赞羡,常说自己每有新书,断不能少了她的评点和批判。所以力邀她来参加这次作品研讨会。面对如此盛意,若不来,就显得矫情而不道义了。
然就是这最平常的却是她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出行,让她发现了一个被蒙蔽经年的自己,似是有了一种全新的初始的诞生。虽然出行的因由是讨论作品,而她并未从讨论会中有多少深入的收获,但她在去往京城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奇异的偶遇。
这偶遇便如在虚空黑暗的理由中神制造的初始的光,光的闪亮刺破了她生活的苍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