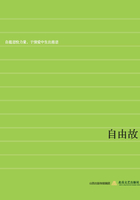虽然吴凤梧那么断言成都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而只是军政府的人有点升沉,但是端方在资州被杀的消息传来,大家到底为之骇了一跳。
在这两个月中,做知州知县的,诚然着同志军和变乱的官军戕杀了好几个人,然而官是那么小,势是那么孤,仅仅官场中人听见,有点为之寒心外,在一般人说起来,并不感到什么。并且自独立以来,许多独立地方的官吏,还身任了都督,或是其他事情;而重庆是革命党独立的,川东道和重庆府两个较大的地方官,还好好的被保护着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说杀了一员更大的官,先是一般退任的官僚就不能不惶恐起来,奔走骇汗的,你跑来告诉我,我跑去告诉他了。
端方之被杀,是成都独立后几天的事。他之那条联络绅士,运动独立,想把赵尔丰弄倒,自己在独立自治的狂澜中来求得一条生路的妙计失败之后,他便坐困资州,真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刘师培朱山一般人,全是讲经数典,吟诗作赋的文人,其余也只是一些讲究伺候上司的官,更说不上什么经纶。他于无法之中,只好终日摩挲着随身所带的古董,以遣愁怀,希望独立的绅士们感激他曾经奏参赵周田王等,而保全诸人性命的大功,容许他长在资州吃着燕菜席,等世界清平了,再平安的回家去享福。
其实,独立的绅士们未尝不这么在想,而人民和同志军也并不怎么恨恶他,赵尔丰周善培等虽恨之次骨,但现在自己已是无权无势的人,又能够把他如何?假设不是他自身所带的鄂军三十一标几营人,因为听见湖北独立成功,急于要回去,并想顺便建立一点功勋时,他断乎不会着杀的。
据说,鄂军情形不稳,他在头一天也就知道了。一到次日天明,就连忙把几个管带请去,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极力欢笑着向他们说:“兄弟并非满人,我的祖宗原是汉人。因打败了,着满人抢去,估逼投降的。我原姓姓陶,所以兄弟自出来做官,别号就叫陶斋,以志不忘本来。如今话说明了,我们都是同胞,若是容许兄弟革命,这是兄弟求之不得的,如其不容许,兄弟也知道诸位跋涉数千里,委实太辛苦了,现在四川乱成这样儿,各处衙门都如水洗一样,没有钱,兄弟身边尚有私蓄四万元,敬以奉赠诸位,作为出川盘费,料想诸位一定可以答应的罢?”
据说,几个管带果然被他哀告动了,都默默的退了出去。他正自大为欣喜他的手段,同着他的兄弟正自商量,等军队走了,他们就上省来找徐炯,找邵从恩,这两个曾经求过他恩典的绅士时,忽然厅堂之上,人声喧哗,约有四五十人,携着枪刃拥了进来,大声吆喝:“把他捉来砍了罢!满洲官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不受他的骗!他做两湖总督时,杀过我们多少人啦!”这等声势,自然不是口舌金钱所能退得了的,凭他再怎么哀告,终于一身衣服被撕了,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他的兄弟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说道:“求你们把我哥放了,光杀我罢!”结果,连他一并捆起来。
据说,仅仅把他两弟兄砍了,其余随员共二十一人全逃跑了,没有波及一人。而端方的头,尚被几斤食盐腌着,随着这几营人一直走向湖北去了。
这件事影响所及,因才有杨嘉绅的卷款潜逃。
杨嘉绅自从独立那天,改穿着军服,并挂着指挥刀,偕同周善培、王棪、路广锺、几个极力要和绅士们亲近,以释前嫌的退任官,在军政府观礼帮忙之后,一连几天,他都打早就进了皇城。一肚皮的四川财政纲要,滔滔不绝的,把个蒲都督听得来目昏脑胀,只是点着头说:“彦如兄高明之极!不过目前四川,尚言不及此。今之所急,只在制度如何改订,人民的自由如何保障,彦如兄如其能在这上面帮点大忙,那更好了!”
大概他就因此把蒲都督看明白了,也因此把军政府的人看明白了,便本着他向来的智慧,思索了一条道路。然而不是端方被杀,或许他也不会那样快的就实行。
他的计画,在那时节真是巧妙极了。黄澜生吴凤梧等人,初听见时,真是说不尽的佩服。黄太太也说:“这简直像《天雨花》那些大传书上说的了。”传到傅隆盛诸人口里,更其小说化起来,并说他把盐库全搬空了。大家都气势汹汹的,要告着奋勇去追他。一会儿又传说已经被军政府派去的追兵,在江口追上了,杨嘉绅全家都着杀在江口。而别一般人则否认是官兵追杀的,说是在黄龙溪就遇着了大帮土匪,他带去的盐务营也变了,伙同把他卷去的款子抢光后,才把他杀了的。
其实,并不如此,他是安安稳稳的出川了,比之田徵葵、周善培、王棪等之走,还威风,还安稳。
他是这么样走的:那时府河虽然还不顶通,江口等处虽然还有一些变像的同志军把守在那里,阻扰行商,但是也只能阻扰行商而已,如其是多有几支枪的队伍,他们仍只好不出头。这情形,杨嘉绅一定知道,所以他才放心大胆的先在东门外使人悄悄的包了三四十只,可以一直驰行到嘉定叙府去的大半头船,然后把盐务营三百人分调上船,下的手谕,是说奉军政府札子,派到叙府去办公事。因而把家眷和从盐库中提取的白银三十万两,一并送到船上。船头立着崭新的汉字旗,舱门上贴着军政府的新封条。
一切布置好了,他才从从容容先坐着大轿,到军政府来议事。脸上是那样的和气,谈风是那样的健,规画是那样的周详。议事完后,又到几家当事的公馆中去闲谈。因此就把轿夫遣了回去,出门是另自叫了一乘小轿,一直坐到东门外大码头。一上船,就叫船夫子连夜开行,说是公事很急迫,如其赶于次日晌午得到江口,每人重赏牙祭肉半斤。所以到次日晌午,军政府的人发觉他卷款潜逃,立刻点兵一营,分成水陆两路赶去时,已相差一百二十余里,并且一过彭山地界,便不是成都军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而是罗八千岁周鸿勋等同志军的势力范围,纵然把电报打去,也未必有效。并且他有三百支快枪,顺流而下,谁也挡不住他。
杨嘉绅一走,而各衙门各局所更其不安宁了。加以都是同胞,都是共同办事的同胞,谁管得着谁?新官们又都是读书明理的维新派,很知道平等自由,当然是独立自治的真谛,否则便成为黑暗的专制了。何况今日的官并不是官,以前那种派头更是该扩而清之的。所以在上的越是实行平等,而小至于一个司书,也便获得了拍着上司的桌子,大声谩骂,勒逼着要预支三个月薪水的自由了。
他们也有理由。他们说:“即如盐务公所,放着许多余利,而把我们的薪水拖到一月不发。我们只管枵腹从公,但杨嘉绅却席卷而逃,军政府把他无计奈何,所苦的只是一般小员司。劝业公所却好,所有存款,先就拿来平均分了,每个人足足预领到四个月薪,那怕你们新任旧任再逃了,也没相干的了。”
不但一般小官和员司们骂着吵着,要欠薪,要预支,并且军界中也着传染了。
军政府的执事人员,大概也想到了巡防兵陆军等,那么军纪废弛的在城里游荡招摇,实在不是妙事,顶好还是按照陈法,无论陆军巡防,一律开出城去,分驻在扼要的地方,一则不在都市上,使他们不至为繁华所诱,好专心一致的去操练,免得生事,再则军政府的势力范围太窄了,把兵分驻出去,也可把这范围扩大一些,安排的是军队开出了,再把有力的同志军招编两镇人,派两个心腹军官来当统制,专驻在城里,一以拱卫军政府,一以安慰出过力的一些同志,料想都是同志,自然比什么还可靠了。再把警察切实整顿起来,而后成都的治安便可恢复,军政府的基础也更稳固了。
可惜他们直迟到第九天,一切都已纷解,而别有用心的人,机构业已成熟之后,方来着手。所以军政部的议案方一提出,军界的代表便应声而至,他们所陈诉的,简直像预定了似的,他们说;“自从变乱以来,弟兄们大小百余战,出生入死,辛苦是辛苦够了,牺牲是牺牲够了,虽然报不出劳绩,得不到都督的奖赏,但是弟兄们有欠饷二月的,有欠饷三月的,在开拔之前,总得请求都督发清,弟兄们把家室安了,也才能够安心出去为都督效劳。”
都督为之一惊道:“怎么说,你们军饷竟会欠到两三个月?赵制台办移交时,却没有提说过,难道他忘了吗?断不会的!”
代表们又诚诚恳恳的说了一番,欠饷是实,营务处是有案可稽的,而后都督才说:“既这样,本都督接事也才九天,你们归入军政府也才是九天的事,所欠两三个月,全然算是赵制台任内欠你们的。凡事须问经手,你们的欠饷,得去问前任赵制台要,与我军政府无干。而叫你们开拔,这才是我军政府的命令,你们须得奉行的。”
事问经手,这的确是一种理由。代表们自然只好跑到旧院去要求赵尔丰补发,而得到的答复,则是移交时,藩库存银二百五十万,盐库存银一百余万,即是各县解来上兑的银款,未及入库,暂时缴存在各银号内的,也都一并移交军政府去了。“你们的欠饷,自然有案可稽,但制台绝不能以自己的私囊,来代补发。所有银款,既都移交出去,你们便不能再问旧任,就是以前的事,也得去问军政府,因为军政府既接受了旧政府的移交,那吗?旧任的事,军政府不能推诿的。”
新旧蝉联,这也是一种正当的理由,代表们便又转到皇城来。
那一天,代表们就这么在此推彼让之间,东西奔走了五六趟。大家都生了气,便坐在皇城里面,不再走了,口里吵闹着:“既然藩库里尚有那么多钱,为啥要扼在手上,不把我们的欠饷补发跟我们?难道也要学杨嘉绅吗?各自把款子卷逃了吗?那却不行,我们拼命来的钱,不能这们白白的就丢了!如其存款几百万赵制台没有移交跟你们,我们自然该问他要,钱又在你们手上,你们却把我们朝外面推,又要我们开拔出去,现在三曹对案,你们尚这们东推西推的,如其开拔了,你们还承认吗?我们拼命的钱,不是就肥了你们一般人了?天地间那有这样不公道的事!大家要这样蛮横不讲理,那吗,我们也会蛮横的。到那时,却不要怪我们弟兄伙目无王法了!人不要命,何事做不出哩!”
这些言动,似乎都有点像预定的。朱副都督到底是外省人,到底是统过兵的,知道这些不好听的话,大有来头。便来商量于蒲都督和军政部长,欠饷似可答应补发,即使目前百废俱举,需用孔殷,不能全数发给,到底得发一半,方可把军心安得了,也才能够指挥调遣。然而军政部长则疑心他别有用意,“此人该不是以此来要结军心罢?他正感着在受排挤,而又是个心怀叵测的下江人!”蒲都督虽不如此着想,仍旧很信赖他的,但觉得他这办法太把军政府的面子损失了。军人既是以服从为天职,那就不比别的人,把命令置诸脑后,而来要挟补发欠饷,并且出词不逊,如其因为他们胡说八道,而就害怕了,答应他们,这不但失了军政府的威信,还开了个恶例,使他们相信,凡他们有所求的,都可以要挟出之,从兹以后,太阿倒持,军政府岂能再指挥他们?“所以,依我说,此事是万万不能允可的。就是要发饷,也只能这样说,本都督们念尔等辛苦效顺,姑准各赏恩饷一个月。以往欠饷作罢,不准再事要挟,否则按照军律惩办,决不姑宽。似乎必如此,而后我们才有权威。前几天就是听老兄的话,对他们太宽纵了。所以他们才得尺进步,啥子都逾越轨范起来。”
军政部长也力赞此说,并主张:“作战以来,每队都有缺额未补,若只根据旧日名册,按营头拨发,一定有不实不尽之处。并且两都督就任以来,尚未观过兵,也是一件缺憾。不如借此机会,叫他们从新实造名册,全体集合东校场,两位都督亲自点名发饷,一则得使他们亲睹威仪,心怀敬畏,二则也不致使国家有用之钱,归于中饱,倒是一举两得的事。”
朱副都督只管不以为然,而蒲都督却颇颇听得入耳。于是再同腹心的谋士一商量,都认为这办法较善,政府与都督的威信,这一下便撑起了。但是代表们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都督准发恩饷一个月,三日内集合东校场,静候点名,点名三日内支发,支发三日内照指定地方开去驻扎操练。大家很为怨忿,因而别有用心的人便更得到了机会来布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