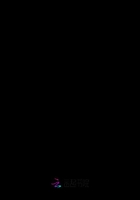寒冷的武汉并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参政而暖和多少。周恩来朝长方形的窗子外面眺望了一阵,若有所思地看着珍珠似的雨点在玻璃窗外面飘着。国民党的CC派、复兴社,正在外面大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冷风,今天——2月10日,贺衷寒控制的《扫荡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还说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这篇社论搅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周恩来取出一把伞,搭车去见蒋介石。这一阶段,虽然两党关系仍在原地踏步,但蒋介石还是做出了姿态:只要有事需要协商,周恩来可以随时约见他。
周恩来经过前室,登上二楼。
蒋介石已经在办公室里等他了。周恩来才跨进门,蒋介石放下正在打着的电话,抓住靠墙放的一把椅子的椅背,把它拉过来,请周恩来坐近点。周恩来巡视了一遍房屋,没有发现报纸,便指了一下窗外:“《扫荡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让人们相信中国只应有一个党的宣传,必然引起严重后果。”
“这并不足虑。”蒋介石置之一笑,“既然开放言论,对主义的信仰就不准备限制。
先总理不是说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嘛。”
“照此说来,别的党派都要取消喽?”
“没有那个意思。我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存在的意思,只是希望它们融成一体。”
恼人的沉默。
“既然两党都不能取消,”周恩来抓住对方的思路,尽量把谈话朝自己有利的方面拉,“只有从联合中才能找到出路,否则又是空忙一场。”
“可以研究。”蒋介石的视线越过了一动不动坐着的周恩来,凝视着别处,放慢了说话的节奏,“《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我本人的意见。”
坐在沙发上始终没有说话的陈立夫,弄清了蒋介石的意图,这才补上一句:
“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周恩来走后,蒋介石又与陈立夫商量:“共产党并没有退让的意思,看来这类文章是要少登,免得共党纠缠不清。”
陈立夫微微动了动肩膀。原来这是一场试探性的攻势。以后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报刊上这类宣传内容倒是少多了,尽管摩擦还在酝酿。
周恩来给延安中央报告:今日见蒋,对边区借口是国共两党县长并存制,有拖延意……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加发了临时犒赏费五万元……前晚见蒋,要他发枪。他答:连坏枪也发出了。宋美龄氏答:(来了)新枪可发。
郭沫若担任厅长,也不顺心。
一厅厅长贺衷寒总跟三厅作对,一会说三厅走私,一会又说三厅是中共的运输机关,没有抓到把柄,贺衷寒却升为政治部秘书长。去部里办事的郭沫若只好称贺衷寒的“职”了。自尊心极强、又曾是北伐军堂堂副主任的他,自然咽不下这口冤气,三天没上办公厅。
周恩来知道了,在第三天晚上请郭沫若和三厅的负责人到他寓所去吃饭。检讨过工作之后,周恩来说:“三厅的工作仍有意义。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而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郭沫若知道周恩来的话是针对他说的,但没有吭声。当谈到部内的人事变动时,郭沫若忍不住了,放下吃到一半的饭碗,说:“三厅的工作我自己的贡献很少,取下我这顶乌纱帽,三厅的同志们依然可以干下去。再要在贺衷寒下边受气,实在有点吃不消。”
周恩来已经就此说了不少话,此时有些不悦,把筷子往桌上一放,问了一句:
“那么怎么办呢?”
郭沫若一向敬重周恩来,认为他和蔼可亲。可现在透过镜片,看见的是一双快要着火的眼睛!他闷下头去,重新拿起碗。
周恩来没有发作,但口气还是很严厉:“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忍受!我们受的委屈,难道比这小吗?”不知郭沫若是否听出此话的弦外之音:周恩来到武汉后,与蒋介石打交道,本来就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而又要受制于国际派来的王明。王明狂妄,常常不听别人的劝告,连延安的毛泽东也不在他眼里。王明和毛泽东的意见常常不一致,是听王明的,还是听毛泽东的?周恩来经常处在烦恼与疑虑的气氛中,处在国共两个圈子里的人暗中互相竞争的气氛中,处在远方的莫斯科和延安的两种指示下……难呐。这也是他对亲近的人发火的缘由。发完了,他会主动道一声:“我也是迁怒于你啊,不要介意……”
郭沫若明白了周恩来的心思。在多少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说:“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
张国焘投入蒋介石怀抱
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多少进展,张国焘逃离延安的事又闹得满城风雨。
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借去黄帝陵奠祭之际,一头钻进了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的小卧车,到了西安。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张国焘决定到武汉去见蒋介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接到张的警卫员张海的电话,立即赶到车站,在车内和张见了面。林伯渠问他此行经过中央批准了没有。张国焘说:“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通知延安好了。”林伯渠告诫他:“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批准自己行动呢?你有意见可以到办事处或者回延安去提。”张国焘不听,执意要去武汉,说要与蒋介石当面谈统一战线问题。林伯渠知道劝不住他,就叮嘱张海路上多加小心,回办事处就给中央报告。中央估计张国焘可能叛变,电告周恩来等在武汉找到张国焘,做最后挽留的努力。周恩来对张国焘的出走很吃惊,马上派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机要科长童小鹏、交际科长邱南章、周的副官吴志坚四人去火车站。周恩来交代他们:“找到张国焘,把他带到办事处来,如果他不肯来,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听候中央的指示。”
4月9日,他们四人来到大智门车站,火车上的旅客都走光了,还是不见张国焘的踪影。他们估计,张可能还留在车厢里,于是便留童小鹏守住出站口,李克农等三人进入车厢内寻找。果然,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只见他和警卫员被国民党两名武装特务左右“保护”着,张海的枪已被缴下。邱南章过去见过张国焘,上前说道:“张副主席,周副主席派李秘书长带我们来接你去办事处。”张国焘坐着不动:“我到武汉有事,有地方住,不用他请。”他本来是在等候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派人来接他,李克农一上车,他马上意识到很难脱身,提起箱子就走。李克农等在后面紧紧跟上,并让张海从特务手中要回武器。两名特务见他们几个都身着军装,军衔也不低,摸不清来头,不敢阻拦,只得让他们走出车站。
几个人在街上转悠了几圈,张国焘死活不肯去办事处。只好在去江汉关的一条街上找了几间僻静的房子住下,由邱南章和吴志坚陪住,李克农和张海回办事处汇报。几天后,又让张国焘搬到比较热闹的中山路的太平洋饭店去住,那里生活条件也好些。
为了说服张国焘,武汉的中共领导周恩来、王明、博古差不多天天找他谈话,有时个别谈,有时一起谈,一谈就是半夜,有一次几乎谈了一个通宵,可都无济于事。
张国焘一有机会就钻出去,与复兴社书记兼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厅长康泽会面。
康泽早就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通知,要他接待并联络张国焘。见面后,康问张离陕经过,张略述是假借祭黄帝陵离开(多年后,康泽供称,实际上是国民党西北行营的高级参谋涂思宗将张国焘“拉出来”的)。康泽又问他离开的原因。张国焘含糊地说:“是为抗战军事的问题和毛泽东决裂了,这是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谈它。”表现出一副不愿深谈的样子。而后,康泽又与他谈到来武汉的居住和露不露面的问题。
张说他有住的地方,暂时不露面的好。张还说他的家眷也一同来了。康问他每月需要多少开支。张说:“200元就可以了。”康泽当即同意每月送他200元。
康泽和张国焘这次见面后,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召集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人的汇报会,出席的有:陈立夫、陈诚、朱家骅、张厉生、陈布雷、周佛海、张道藩和康泽等。汇报结束后,康泽向蒋介石报告:“张国焘已住到汉口,我已经和他见了面,是否可以约见他?”
在蒋介石尚未答复之际,张厉生抢先说:“我主张现在不要约见张国焘,免得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感。”
蒋介石同意,决定看看再说:“如果他还以共产党的身份见我,我倒不妨一见。”
11日晚上,周恩来又来到太平洋饭店,找张国焘谈。张国焘捶着太阳穴,重复自己的观点:“合则留,不合则去,我跳出中共这个圈子,或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周恩来瞪着他:“你这是叛党行为!”
“那种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让我当边区副主席太不公道!”张国焘喃喃辩解。
“你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至今还没有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处理有什么不对?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为什么背着中央自由行动?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性?”
张国焘无言以对,看看手表,说明天再谈吧。第二天,张又提出要看看市容,周恩来就陪他出去转。他们上街的当口儿,警卫员按周恩来的吩咐,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日本租界大石洋行89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回来后不见了行李,只好到办事处去住。晚上,张国焘来到楼上周恩来住处,又提出:“蒋介石既然是抗战之领袖,我应该去和他见一次面。”
周恩来不同意:“以你这样的身份去见他自然不妥,等一等吧。”
“不要等,我可视他的态度决定去留。”
“你要去,也要等我与他联系后,由我陪你去。”
蒋介石同意见张。一见面,十分热情,离座握手,上茶。
张国焘陪着笑脸:“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一听这话就来气,讽刺道:“你糊涂我不糊涂!共产党人成千上万,不是从哪个角落里跑出三个两个人的事!”
蒋介石仍然兴致勃勃:“于归则好,于归则喜。一个人对一个党派的领导者如在政策上不能一致,当然可以挂冠而去,拂袖而去,或飘然而去……你不是任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吗?我欢迎你再度与我合作。”
张国焘被周恩来几句话一刺,脸上也有些发烧,听不进蒋介石聒噪什么,自己的谈兴也索然无味,没坐几分钟就告辞出来。
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周恩来仍很不高兴,两人默默地乘船返回江汉关码头。上岸时,周恩来碰到个朋友,站在那里谈了几句,一回头,发现张国焘已不知去向。
周恩来只好让办事处的同志四处去找,直至深夜,才在武昌一家旅馆找到张国焘。
周恩来气极了,声音有些颤抖:“国焘同志!你这是搞什么!你不能这样三番五次地搞嘛!”
张国焘似乎精神上出了毛病,莫名其妙地讲述了一大堆趣闻轶事,把悲哀和狂放搅在一起,也不知他是遗憾,还是抱怨,还是装傻,连连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的。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吧。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你们让我走吧。”
周恩来和王明、博古商量后,向他提出三点解决办法:一是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是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是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摇着胖胖的身躯,开始考虑:“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三条中选择。”
“那你就考虑两天吧。”
张国焘并不好好考虑,于谈话的当夜,即4月17日夜间突然逃到太平洋饭店,在国民党特务多人的保护下坐车而去,逃到了胡宗南的司令部。当时在场的只有邱南章一个人,而国民党特务人多势众,拦也拦不住。张逃后在房间里留下一张纸条,上写: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去找,至要。”当邱南章满头大汗赶回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反而不惊了:“我想他大概就走这条路。”
周恩来把“建议”带给李宗仁日军的炮火继续猛烈地朝着中国大地倾泻,到了3月份,铁蹄已经踏上津浦铁路,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白是国民党战将中的主战派。军委会改组后,出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同周恩来常常见面。出发前,他特地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他的寓所,请教作战方针。
周恩来呷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回茶碟,很随便地谈起来:“请教不敢当,你是军事家嘛。但我有一个建议,仅供你参考。”他的建议是: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目不转睛地听着。周恩来戛然而止。白崇禧催促道:“接着说,接着说!”
周恩来手一摊:“没有啦!”
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咧嘴摇头赞叹道:“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向李长官转告,至于新四军方面……”
“这你放心,我会亲自关照的。打日本嘛,责无旁贷。”
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