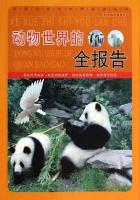郝治平对卓琳说,她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她打开随身带的大本的《毛主席语录》,翻到关于要做老实人那一段话,让卓琳看。毛主席说,陈独秀、张国焘等等不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没有好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老实人。郝治平说:“我这几天就靠这一段过日子,要是没有这句话,我这日子过不了。”
卓琳说:“不要想那么多,还是照顾好罗总长的生活。”
说着,两人都掉了泪。
17日,他们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一同回北京。在飞机上,郝治平碰到陈毅夫人张茜,问道:“你怎么一个人回来?”
张茜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先因为老房子维修,他们暂住钓鱼台。罗瑞卿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有关上海会议的情况,在《康克清回忆录》中也有述及:
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经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倔强的罗瑞卿选择了“毁灭”
上海会议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罗瑞卿“反对你(指林彪),还没有反对我……”所以上海会议没有给罗瑞卿扣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是上海会议以后,再不给罗瑞卿扣上这两顶大帽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林彪要置罗瑞卿于死地而后快的要求了。所以三月会议要开出和上海会议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来才行。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罗瑞卿,对他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罗瑞卿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罗瑞卿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的确比罗瑞卿有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罗瑞卿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历史,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罗瑞卿渡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罗瑞卿没有想得太多,也没有预料到现实是如此残酷。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是罗瑞卿最亲密的同志,有他爱戴、尊重的上级,也有爱戴、尊重他的下级,一时间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了一副面孔,就像是随着环境改变体色的变色龙。他们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要和罗瑞卿划清界限。他们都以十分敌对的目光望着他,好像从来不曾亲近过。
也许这就是罗瑞卿最不能忍受的。
“文革”中走上自杀之路的无辜者,大多囿于此因。
从上海回到北京以后,罗瑞卿就写了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调离他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报告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此报告及批件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还给了罗瑞卿一份电报抄件。
接下来,军委办公厅来人拆了电话机。罗瑞卿是个自觉又细致的人,他要秘书将自己的手枪、猎枪,以及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没觉得那么严重,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罗瑞卿朝秘书摇摇头:“不要留,全部上交。”
罗瑞卿不想外出。当他的头发太长时,提出去理个发。上面的人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这以后,他除了去解放军总医院拨了一颗牙,哪里也没有去过。
罗瑞卿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个刚烈而好动的人,被一下子困在楼里,犹如狮子关进了铁笼。看到孩子们,他们一无所知,特别是3个仍然年幼的孩子,罗瑞卿心里更是火烧一般。当时他想:“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正是这种想法,促使罗瑞卿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毁灭。
至于罗瑞卿究竟是怎样从楼顶跳下来的,无人看见。连他的家人当时也不知道。作为妻子和儿女,记得罗瑞卿情绪中的变化,但没有丝毫的预感。
在这段时间里,罗瑞卿精神上感到最痛苦的是被诬陷反毛主席。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前沉思到深夜。一天晚上,妻子走进他的房间劝他早点休息。罗瑞卿神情沉重地说,他睡不着。突然,两颗泪珠从他眼角滚落下来。他用低沉的语调对妻子说:“他们说我反毛主席,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长征时,我在一方面军当保卫局长;解放后,我当公安部长,我长期做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的老警卫员,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啊!”
罗瑞卿百思不得其解。
3月18日,孩子们照例一大早都上学去了。家里只有罗瑞卿和郝治平。吃过早饭,突然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罗瑞卿,说会不开了。这使罗瑞卿又受到深深的刺激。对于那些旨在折磨人、毫无道理可说的批斗会,罗瑞卿怕开,可更怕不开。因为开会仍是老一套,并无新的东西,不过是对着他狂轰滥炸一通。而不开会,说明会议的主持者可能又在研究新方案,搞出什么新花样,那就意味着诬陷又要升级。
罗瑞卿也就在这一刻产生了一个“死”的念头,因为他已经绝望,接下来的更沉重的打击变得更加可怕和无法接受。因为他解释的一切无人相信,而能够作证的那些关键人物不愿意或不可能出面澄清事实。他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他灵魂的支柱瞬间坍塌了。他眼前只剩下唯一一条能够自主的路,就是让自己从这个世界消失。当他最后竟没有死成,才说出当时的心境:“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郝治平回忆当时的情况:“平时我们一起吃早饭,吃过早饭他就去开会。这天忽然通知说不开会了,他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我走进去跟他说,怎么搞的,看东西也看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住,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他说,他也是那个样子。我想让他松一松心,就对他说,现在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其实,我反而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瑞卿就对我说,你觉得那个书好,你就去看那个书吧,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我拿着书到隔壁去了。”
郝治平离开房间后,罗瑞卿就伏在桌子上写了一封绝命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
永远革命!
写完这张纸条,他把它放在抽屉里。他来到隔壁房间,推开门,看到郝治平仍然拿着那本小说,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
如果郝治平敏感一些,抬起头看看罗瑞卿那异样的眼神,或许能发现什么,化解一些什么,可惜郝治平毫无觉察,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罗瑞卿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改变。他回到自己的卧室,轻轻地掩上门,脱下日常穿的衣服,换上了一套洁净的睡衣,然后轻手轻脚地踏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
这整幢房子是过去一个海外的官僚资本家留下的,三楼是一个储藏室,里面放着几个长年不见阳光的大箱子,从这里,有一扇狭小的窗子通往楼顶的平台,罗瑞卿低下高大的身躯,从这里走向平台。
死的结果是一样的,而死的方式有不同。在这里无须去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发生的一切。我们这一代人——开国将士们的后代,到现在的年龄,多数已经尝到或目睹了送走上一代人的情景,而他们多数是因病或年岁关系的正常离世。即使是这样,看着亲人慢慢闭上眼睛的一刻,是那样撕肝裂肺,只要自己闭上眼睛就会历历在目。而何况像罗瑞卿这样被迫害的人。所以,我在反复阅读罗点点记述父亲自戮的那一部分文字时,常常被打动得落泪。
不啻是为罗大将一人,还有整个民族在那个非常时期所遭受的一切。
所以我在此照直录下罗点点所感悟的、震撼人心的那段文字:
只有一扇窗子通往楼顶的平台。我猜父亲一定是很费力地跨过了这扇狭小的窗户。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这样一幅情景。父亲高大的身躯正艰难而又固执地通过这扇小窗。噢,父亲,你的决心一旦下定何以竟这样顽强?!难道人世间就再没有你可留恋的事情?!多少人在天伦之乐中颐养天年,多少人在浑浑噩噩中尽尝自然硕果,疲倦的政治家还可闲云野鹤,东篱种菊,被放逐的将军也还可挂甲拴马,终老田园,而你竟这般毅然决然!是什么样的绝望吞没了你的理智,是多么狂暴的风雨熄灭了你的生命之火,是什么样无法克服的矛盾使你给妻子儿女留下了那么专一而又那么凄然的企望,而你本人却不肯在这世上再多活一分钟。噢,父亲!21年前的这一幕,至今使我想起来就热泪盈盈。21年前重压在你心头的惨烈的痛苦,至今使我不堪回顾。这是我心灵中一个永远不堪触抚的伤痛。死亡本身就是阴冷的。这种追求死亡的特殊方式更是阴冷可怕和不自然的。自戮,就是骨肉迸裂,就是心灵破碎,就是生命毁灭,就是万念俱灰!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自欺,更不能欺人。在短短的几年里,有那么多中国人民中的杰出人物都先后走上了这条可悲的道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那个毛骨悚然的时代。可悲之处恰恰在于,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民族都缺乏准备。如果他们(父亲和老舍先生)当年果真有那么冷静的分析的话,他们就绝不会去死。以他们对生的热爱来说,死亡,尤其是自戮,是最残酷的苦刑……
一浪高过一浪的批斗高潮,将罗瑞卿送进了监狱;罗瑞卿不曾料到的是,不仅自己没有死成,反而加重了“罪孽”。
当时罗瑞卿跳下去时,郝治平还不知道。听到外面有人喊,她的心紧缩起来,知道大事不好。当她跑到楼下院子里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开进了大门。人们七手八脚将罗瑞卿瘫软的身躯抬上了车,他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到了北京医院,六神无主的郝治平跟着担架往楼上跑,迎面碰上汪东兴。他叫住郝治平,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还说,这几条对罗总长也适用,要郝治平转告。他要她早点回家,说他还有事要找她谈。郝治平五内俱焚,哪有心思听汪东兴说这些,答应了一声就赶紧往上走。
等到罗瑞卿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郝治平把刚才汪东兴说的那套话说给他听。但罗瑞卿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对妻子说,他的抽屉里放着他给她的东西。当时旁边还有别人,听到这个话就赶快先走了。
下午3点多钟,郝治平看罗瑞卿情况平稳了一些,记挂着抽屉里的东西,就先回家了。
她没有想到,一进家门,就看到汪东兴在那里等候。看到郝治平,他又把那三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叫郝治平去吃饭。郝治平哪里吃得下。汪东兴就说要到楼上去看,郝治平记起罗瑞卿说的放在抽屉里的东西,就说:“我和你一起去看。”汪东兴起先不让,可在郝治平的一再坚持下,只好答应。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向上走,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汪东兴就拦着郝治平,说什么也不让上。郝治平只好作罢,站在楼梯口等着。汪东兴等几个人上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就坐上汽车走了。
这些人一走,郝治平就三步并作两步朝上跑,想找罗瑞卿说的东西。可是抽屉翻了好几遍,却怎么也找不到。她去问秘书,秘书支支吾吾地说已经上交了。郝治平这才想起,她和罗瑞卿说那东西时确实有秘书在场。郝治平急了,冲着秘书发问:“那是给我的东西呀,为什么要交上去?”她坚持一定要看一看。那些人没有办法,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把罗瑞卿写的东西拿来了。不过,他们不让郝治平碰。由他们拿着,让郝治平伸头来看。这就是罗瑞卿写的那封绝命书。
“彭罗陆杨”案一出,“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
在上海会议之后成立的“中央工作小组”,于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第一阶段,3月4日至16日,42人参加,对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罗瑞卿跳楼跌断一条腿后,因为罗瑞卿的所谓“自绝于人民”,以揭发批判为主的那个三月会议也随之升格,即性质变了,原来还带点人民内部矛盾的味道,一下子升级成“敌我矛盾”,罗瑞卿变成了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是叛党。于是从3月22日至4月8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人数也增至95人,对罗进行缺席批判斗争。
虽然外面在批判,但开始的时候,罗瑞卿还住在医院里,郝治平也可以经常去看他,这对两人都是极大的安慰。虽然门口和病房总有人监视,他们的谈话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不过是说些孩子们的情况。
以后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的事:当时负责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是彭真。不久,他们就成了国内头等大敌的“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的前两位。彭真当时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郝治平并不知道,还去找他,问道:“瑞卿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彭真说什么呢?只好安慰几句,让她不要着急。他对下面的人说:“你们收东西,把孩子们的东西收起来干什么?还给他们。”
4月里,郝治平还是隔一天到医院里去看罗瑞卿一次。4月3日是他们结婚的纪念日。郝治平没有按照隔一天去一次的常规,而是2日、3日连着去了两次。4月3日临去时,她从院子里采了两枝丁香花,又摘了两朵海棠花,悄悄装在口袋里,进了病房,她把花送到罗瑞卿手中,罗瑞卿看着怒放的花朵,嗅着它的清香,神色颇为激动:“你还记得啊……”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对罗瑞卿的审查结论。结论中,虽然仍是一口一个“同志”,紧接着又是一口一个“胡说”,谁都知道,一个一天到晚“胡说”的人,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反对“林彪同志”的人,早已不是同志而是敌人了。
他们罗列的罪名也证实了这一点,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