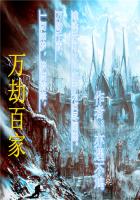总之,张学友便是香港流行音乐最金光熠熠的代表。他是公认的实力派,且动静皆宜,有一箩筐情深款款的慢板金曲,也定有《头发乱了》等绝无冷场的劲歌热舞时段,近年更逐渐以爵士、R&B拓宽歌路;90年代里,他的《吻别》唱遍了街头巷尾,“情人杀手”周海媚也因出演这首歌的MV而彻底摧毁了无数少男的心底防线;《吻别》同名专辑至今是华人音乐史上销量最高的唱片,在台湾,每二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拥有《吻别》;1995年,他的唱片年销量名列世界第二,仅位列如日中天的迈克尔·杰克逊之后,而远远地甩开第三位的麦当娜;同年,为庆祝入行十周年,他在世界各地举办了100场巡回演唱会,平均3天一场,总观众人数达200万人次,其中开唱的地点包括了麦迪逊广场花园,成为第一个在纽约演唱会圣殿开个唱的亚洲歌手;十二年后,他的“学友光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以105场再次刷新了自己的纪录;1997年,他参与策划、导演并主演的原创音乐剧《雪狼湖》在红馆公演,连续的42场至今依然是香港音乐剧场次的纪录保持者,他以一位流行巨星的身份推动音乐剧在香港的发展,为保证《雪狼湖》的尽善尽美,不惜花费数月在百老汇学习舞蹈、参与音乐剧理论课程培训;他获奖无数,巨蟹座的恋家好男人形象随着奶粉广告更加深入人心,他的成熟、稳重、勤勉、谦逊的奶爸形象充满了说服力。记得在某次颁奖礼上,他担任颁奖嘉宾,在串词时说:“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忽然听到电台里面传来了一首歌,很好听。我想,这是谁的歌呢?听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哦,原来这首歌,是我唱的。”这些话若从陈冠希口中说出来,一定会遭到媒体乐迷的口诛笔伐,但他是张学友,他略带腼腆的样子不会给你带来不适,而是让你感慨:是啊,我们的香港乐坛是怎么了呢?歌曲制作越来越精良的同时,为什么却无力重现黄金时代的辉煌呢?这不是倚老卖老的显摆,而是对后辈的诚挚勉励。可以说,德艺双馨的张学友是完美的化身,是每个人的偶像。
学友却摆了摆手。不,我并不完美。
1986年,张学友的第二张唱片《遥远的她》狂销40万张,比他的首张唱片《Smile》风头更猛,专辑中的《月半弯》《遥远的她》等歌曲更是获得了万般赞誉。他丝毫没有被“新秀墙”影响,也没有所谓的“第二张困难症”,一路顺风顺水。正当大家以为这颗冉冉升起的超新星将顺利接过谭咏麟、张国荣的枪时,没想到张学友却在此时遭遇了没有任何预兆的低潮,1988年的专辑《昨夜梦魂中》销量只有几千张,电台打榜成绩黯淡无光,在年末的几大颁奖礼上颗粒无收。和歌唱事业的低谷形成反差的是他日益增长的酒量,“我几乎每天都会喝得大醉,几乎没有人敢跟我喝酒。因为你喝一口,我一定喝两口;你喝一杯,我一定喝半瓶。不把对方放倒绝不算完。”他开始不断出现在兰桂坊——位于中环半山Soho区里,那个汇聚了夜蒲族、外籍人士、中产阶级,在《朝九晚五》《喜爱夜蒲》等电影帷幕中出现的纸醉金迷之处。对于我等内地游客来说,兰桂坊只是一个闻名遐迩的香港旅游景点,到此一游,拍几张相片,便已足够。那些半开半掩的店门,是我们绝不会去碰的,可那时的学友却每每在里头喝到天昏地暗,喝到酒吧凌晨三四点打烊。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酒鬼,他的丑闻不断出现于各大小报,什么张学友兰桂坊醉拳打歌迷啦,女友罗美薇宣布和其分手啦,在朋友婚礼上喝得酩酊大醉并将蛋糕扣在了新郎脸上啦,以及臭名昭著的梅艳芳生日会大闹天宫事件,这些都让他的公共形象跌入谷底。这时的张学友才不是什么谦谦君子,他不过就是一个走了狗屎运的毛头小子,运气用光之后,马上就被打回原形,还落得一副自以为是、傲慢无礼的样子。
多年后,张学友回忆自己的这一段荒唐岁月,总是有心有余悸的感觉。在一夜成名之后,被忽如其来的名利冲昏头脑之时,许多人都会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么是骄傲自满,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要么是惧怕挑战,老想着自己是否能够延续这个发展势头呢,患得患失的心理成为前进的桎梏。每一个伤仲永的故事,其实都大同小异。反正,听歌的人就是那般无情,今天能把你捧到天上,明天就能把你摔到谷底。“我那段时间是很冷清的,心里很慌。我什么都不会做,除了唱歌之外,自己也没有任何专长。我甚至觉得歌手是一份非常危险的工作,是一份很没有安全感的工作。”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没品尝过从云端猛地跌下来的滋味,那你就没法子用更坚韧的毅力去探索宇宙更深处的星球。台湾乐团Tizzy Bac有一首歌叫作《如果看见地狱,我就不怕魔鬼》,把生命中的挫折极端化,当我知道地狱是怎么样一副光景的时候,那我怎么还会对身边发生的其他事情感到畏惧呢?
张学友低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接连两张《给我亲爱的》《只愿一生爱一人》推出后,他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此后他不但戒掉了酒瘾,甚至还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在日后反复地强调自己的被救赎,感谢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的人,感谢他们给予的宽容。其实,他最应该感谢的是挫折本身。没有那茫然失措的两年,不会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宠辱不惊的张学友。他也不用老说自己是如何不完美,人生本来就因不完美而完美。
想起海明威,这个以溺于酗酒的形象闻名世界文坛的硬汉老爹。二战结束后,海明威在意大利一个名为阿西亚罗利(Acciaroli)的小村庄里生活,开始创作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之后的新作品——《伊甸园》。但他一直没能够完成这本书,村民们说,海明威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拎着酒瓶子到处乱走。后来他回到了古巴,在1950年发表了小说《渡河入林》,迎接他的是纷至沓来的如潮恶评。许多人讥讽海明威已江郎才尽。面对质疑,海明威喝得更厉害了,据曾前往古巴为他拍摄照片的著名摄影师阿尔弗莱德·艾森塔斯特(Al-fred Eisenstaedt)说,“这个人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喝酒,喝杜松子酒和琴酒。他还有一个每时每刻都能提供酒给他喝的司机。”当大家都以为海明威就此在酒精里沉沦的时候,1952年9月,整个美国的书报刊都在为“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个名字而沸腾。在9月1日上架的《生活》杂志专刊里,海明威发表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当年,他获得了普利策奖;两年后又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老人与海》发表之前,他曾扬言要把那些指责他的评论家揍成一摊烂泥,誓要写一部“让那些狗娘养的闭上臭嘴的作品”,他并没有食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年以后,在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老城区的小佛罗里达酒吧里,在海明威当年几乎每个夜里都会来狂饮一番的地方,全世界的仰慕者们在此点上一杯代基里酒——这种在朗姆酒中加入酸橙汁或柠檬汁和糖混合的鸡尾酒饮品是海明威生前的最爱。海明威也一样,一个见过地狱的人,鲨鱼算得了什么。
当然,张学友和海明威的区别在于,后者的酒瘾一直伴随着他的终生。
因为他有孩童般的天真,这是他清澈见底的湖水;同时他也有少年维特式的敏感,所以即使是最轻柔的微风拂过,也会拨动他的心。
“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
一眨眼,二十年过去了。在大家为“沙士10年”“Beyond成立30周年”“张国荣逝世10周年”举行各种缅怀活动时,关于陈百强的声音却要微小许多。现在谈这个兴许还早,4月是属于张国荣的,6月是属于Beyond的,对于媒体的版面来说,一切都要按部就班。等到10月份,大家应该就会猛然想起,噢,原来丹尼仔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
如同胎记一般,关于陈百强的记忆当然是从《一生何求》开始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每晚都守在电视机旁,为《义不容情》兄弟间的爱恨情仇揪心不已。黄日华愤怒而绝望的咆哮,还有背负了一生的生母临终托付;温兆伦打造的TVB史上最著名的反派角色,连怀了他骨肉的加敏和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云姨也不放过。关乎这一辑80年代末内地和港澳台收视率最高的时装剧,或许在今天看来,剧情和人物设置也未免太狗血太老套了,但你永远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去评价昔日之景。而正当全家人对温sir咬牙切齿、百般期待他最后落得怎样的下场时,这首歌出现了:
一生何求 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耗尽我这一生 触不到已跑开
一生何求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陈百强《一生何求》
《义不容情》捧红了黄日华和温兆伦,同样也把陈百强及王杰的歌声送入了千家万户。和王杰的插曲《几分伤心几分痴》相比,《一生何求》更符合剧中主题和人物宿命。全曲段落起伏分明,感情上一唱三叠,陈百强呢呢喃喃地唱出人生的得与失、追和逃,结合他一贯的忧郁王子形象,更相得益彰。儿时的世界只有两种颜色,要么是黑色,要么是白色。长大后才渐渐发现,每个人都有各自需要追寻和守护的东西,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裁夺正义的天平,所以在回答“一生何求”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会有千种不同答案。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如莎翁剧本里所说:“世界本无善恶之分,是想法让它变成了好或坏(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尽管这首歌本是翻唱自王杰两年前热卖国语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中的冷门歌曲《惦记这一些》,但经过潘伟源重新填词后,完全抛离了原作的大路情歌印象,而成了一首有着悠远意境的、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进行深刻反思的雅俗共赏流行曲。
除了《一生何求》外,丹尼仔还有许多表述大爱、致敬生命的作品。《画出彩虹》和《摘星》均是顾嘉辉的代表作,歌曲的年龄和我同岁。前者是TVB当年的同名剧集主题曲,郑国江的词不仅和剧中自学成才的画家主人公身世贴合得天衣无缝,更暗合了顾嘉辉本人从九龙木屋村开始的“香港梦”。“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陈百强的声线好似画笔一般,轻轻柔柔地就在你的心头描绘出一道充满希望的彩虹。黄耀明极其喜爱这首歌,把它放到了2004年时的顾嘉辉致敬专辑《明日之歌》第一首的位置,用微醺的电音脚步、摇曳的木吉他、飘飘然的小号声绘出了属于明哥自己的画卷。而《摘星》搭配的词人是林振强,这是1984年度的香港反吸毒活动主题曲,在翌年5月的《辞汇》里,林振强特地撰文讲述了这首歌的创作始末,他在抓破头皮后猛地想到“一间没有窗的屋”,然后再把“后悔”“明天”等添进去,这才有了后来的“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和小品级《画出彩虹》相比,《摘星》是作曲大师顾嘉辉的另一面,歌中充满了旭日之屋式的万丈豪情,陈百强也能将这喷薄的热情完全铺洒开来。还有那首功能性的《念亲恩》,每天都会在点歌台里听到好几遍。“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惜取孝道。惟独我离别,无法慰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MV里陈百强一边唱着,底下的字幕也在一路滚动,轮番显示着点播者对今天生日的妈妈的祝福。这是比Beyond《真的爱你》使用频率更高的歌。
陈百强被大家所铭记,很大部分还是源于他冠绝一代的情歌王子形象。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和张国荣、梅艳芳平起平坐的香港乐坛流行巨星,当他们皆陨殁后,陈百强之成就及影响力和其他两位相比,都要矮一个头。你可以把原因归结为Danny的生命太过短暂,他“一生不能自决”的性格,还有终究未发行过国语专辑的事实。但对于许多省港澳的80后来说,陈百强的位置却是无可取代的。在谈“早恋”而色变的时代,在把“早恋”视为洪水猛兽的时代,父母们成日里播放的陈百强便是我们最早触摸到的情书。
在他寄给大家的一封又一封的情书里,信签纸大多是淡淡的紫色——这也是陈百强“一生紫爱”的专用色,象征着尊贵、圣洁、纯爱。当20岁的丹尼登上乐坛时,他像一个白马王子一样,唱着自己作曲的《眼泪为你流》《不再流泪》《初恋》。他的歌声里掺杂着阳光和苦闷,偶尔有片刻的欢愉,但转眼间又被一扫而空。像《眼泪为你流》《不再流泪》开头的电话应答声,你能一下子就把自己代入陈百强在歌中扮演的角色,仿佛他面对爱情怯生生的举止就在眼前,敏感脆弱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本来就是一个孩子。钟镇涛是陈百强在圈中的“契大佬”,在谈起自己的弟弟时,总是会特别指出他的孩子气:“陈百强喜欢给人意外惊喜。有时候我忽然见到舞池有个年轻人跳得很起劲,没准一看就是他;有时候我去停车场拿车,挡风玻璃会夹着他留下的字条;有时候刚下车,他会跳出来吓我一跳。同时他也很情绪化,是圈中的受保护动物,从不会伤害人。”身为一个偏执的浪漫主义者、唯美主义者,陈百强对爱情又有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可这对于置身于放大镜下的娱乐圈来说,又是注定会落得遍体鳞伤的下场。就像他的《不再问究竟》,弟弟看到哥哥又红又肿的双眼,关切地问哥哥你是怎么啦?哥哥轻轻抹了一下眼角淡淡的泪痕,“乃因风砂吹入了眼睛”。多年后另一个“苦情弟弟”梁汉文则唱了一首《一再问究竟》致敬Danny:“那夜孩童前来问候你,骗他的说风砂吹入眼睛,这夜孩童随年月大了,呆站街角忘怀年少气盛。”梁汉文说:“陈百强是我最爱的歌手。每次有机会演绎他的歌曲,我总会有一种异常兴奋的感觉。这一次能够演绎《不再问究竟》里面长大后的小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为《一再问究竟》填词的新一代词人小克同样也感到荣幸,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和老一辈词人林振强隔空对话证明香港乐坛的薪火相传,于我旁人亦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