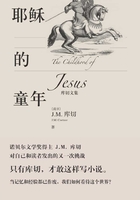杨柳云还活着的事,让军分区领导既感意外又高兴万分。听了她和护送的战士陈述后,杨政委当即叫人去接欧阳剑。
得知帮助柳云的团长叫程小平,欧阳剑激动了:“程小平,会不会是当年大突围时和我一起的副排长?”他紧抓着柳云的胳膊:“你有没有提起过我的名字?”
柳云摇着头:“你那时的处境,我能提,敢提吗?”
“但愿,有机会能再见到他。”
为了政治组长全面管理、协调和工场的关系,欧阳文宇和周洪波对换驻地,到二工段验收点负责。
二工段离场部十多里山路,驻地在一个大山的低洼之处,除了连排干部大多为军人,有一百多养路段和森工局正式职工和二十多名家属工。
临行前,老彭对欧阳文宇说,副营职的二工段长兼书记老何较耿直;成天脸上挂着笑,好事坏事都不当面表态的地方干部卢副书记,人称“笑面虎”,和场部周副书记关系很好,须小心提防。
欧阳文宇知道周副书记仗着年轻,指挥部有后台,不仅觊觎一把手的宝座,而且痴心妄想穿上军装,一直暗中培植势力,半公开和魏书记唱对台戏,而魏书记凭着资历和一帮老战友、老首长的铁硬关系,打心眼里瞧不起坐直升机上来的周副书记,仅让他分管后勤和工青妇,其他工作根本不让插手。
检验组在二工段的点只有欧阳文宇和小罗两个人。不多言语的小罗来自农村,娶的老婆也在农村,因为父亲是基建部队的后勤部长,所以得到关照当了兵、进了检验队。
这里的工作仍然轻松,每天检验运进防空洞的原木,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只需很短时间即可完成。
两座大山之间有一条宽不过十米的河,为通行便利,二工段在河上架了座桥,这架通向河对面的桥,是一座仅容两个人同时通过的索桥,那索桥因为窄,也因为跨度长,人走在上面,摇晃得很厉害。女性走在索桥上,都会扶着半人高的钢丝护绳,哆嗦着双腿慢慢挪动,成天在桥上过往的老工人,走在上面也会相当小心。
桥下的流水太急,浪花击打在石头上发出的声音,震得人的耳朵听不到声音。
欧阳文宇自到这里来的第二天早上,就在桥上练开了拳。说来也怪,不管那桥如何晃动,他练拳的身姿总是那样矫健,步伐也恰到好处,无论腾跳起伏或平步行拳步履都极为稳健。
后来,他在桥上练拳时,竟做到了从桥头到桥尾行云流水般运动过去而桥面不摇不晃。就连前后空翻、飞腿起跳,那桥都纹丝不动。
瘦得如竹竿、两颊深陷,如瘦猴子般的二工段工人刘有德同样练拳,只不过他练的是简易太极拳,和欧阳文宇以进攻为主的杂家拳大相径庭。
这天清晨,天上飘着毛毛细雨,刘有德在河边练太极时,发现桥上有动静,抬眼望去,一个身高约一米七六,着一身蓝色运动衫,下穿白色网球鞋,腰间束黑色练武带,手上戴着护腕,国字脸上五官端正,醒目的剑眉下双眼目光如炬的年轻人正在桥上打拳,腾挪起跃间挥拳生风,起腿快如闪电,身形和桥融为一体。
刘有德大吃一惊,使劲揉着双眼,再仔细观看,心想:没想到,二工段竟有了这样的人才。
仔细看清练拳人是欧阳文宇,他心里盘算开了:难怪这新来的检验员虽清瘦,但双眼有神走路虎虎生威,早该看出他是个练家子。
刘有德父亲解放初期被镇压,可他坚持说有证据证明老爷子是地下党,奉党的指示开展工作筹措经费。相当一段时间,只要有机会就会诉说老子的不幸和辛酸,却没得到同情和理解。历次运动中吃了太多苦头以后学乖了,不再说父亲的事,也不再埋怨不公待遇,下班后就和一帮出身不好被打入另册的人喝酒聊天,暗地里大发牢骚。偶尔,也会酸气大发和几个“牛鬼蛇神、坏分子”摇头晃脑吟诗填词,自娱自乐。
想学拳术练武功,却苦于没有人教的刘有德,和掘进三班班长赵明,连续几天端了炒好的菜,提着瓶装白酒,溜进欧阳文宇宿舍非要和他交朋友。
欧阳文宇刚到二工段和段上领导见面时卢副书记就告诫过他,刘有德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分子,只能远离不可近交,可欧阳文宇却不忍拒绝他诚挚的请求。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既不是领导干部,也非中共党员,普通军人一个。既无被人拉拢腐蚀的可能,也没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价值,只要酒里菜里没有毒,凭啥不吃?至于练武,毛主席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个人是锻炼,多几个人就是积极响应领袖号召,开展体育运动的好事。
外号“金刚钻”的赵明,身高不过一米六出头,在家乡当知青时却是个打架斗狠的角色,曾手提一根扁担,在大街上和十多个山城知青血战,虽最终遍体鳞伤倒在了地上,却也让县城人就此刮目相看。
掘进一班班长魏庆松,是魏书记的亲侄子。长得虎背熊腰五官端正,浑身上下透露出真正的男人味,原本相当积极向组织靠拢,也曾是森工企业采伐能手和先进分子,却不知什么原因,总不能得到提拔。到人防工地后,自感进步无望,也就当天和尚撞天钟,得过且过了。
掘进二班班长杨牛儿来自养路道班,一身蛮力,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就是太喜杯中之物和吞云吐雾,每月工资一大半换了烟酒。
这几个不被领导看好却也离不了的生产骨干,成天跟在欧阳文宇身后练拳习武,评朝议政,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胡写一些既不是诗也没词味的玩意。
工段领导不能管,也没有权力干涉欧阳文宇,就连跟在欧阳文宇身后混的一帮人,也不便过多干预。因为他们是聪明人,只要完成挖掘任务,不出人命和重大安全事故;只要按照上级指令,把批判“四人帮”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其他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过了小桥,一座平坦的小山坡上,两间石头为墙、牛毛毡为顶的房子为单身大工棚,一间比工棚小了一半的房子是伙食团,大工棚上面有简易球场,球场上不远处是正在挖掘的人防工程。宽敞的洞外一幢近三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住着连队领导和检验员以及部队武装班。每晚,武装战士由干部带领轮流值班、巡逻,防止阶级敌人进入洞内搞破坏。
欧阳文宇和小罗各分了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屋里有床,办公桌,火炉,热水瓶,洗脸架和两张简易木椅。
刘有德等人在屋外砌了一个灶台,搬了张折叠式圆桌,弄来了半新的锑锅、铁锅和十来副碗筷,用木板做了简易碗柜和几个木凳,俨然一像模像样的小伙食团。
除了早晚练拳,这帮卢副书记痛恨的角色,每天下班后就会凑到欧阳文宇的小屋前,弄出香喷喷的饭菜,就在巷道里大快朵颐,全然不顾及走道那头段长、副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异样的目光。
魏庆松的老婆邓桂芳,鸭蛋形脸上五官搭配得恰到好处,皮肤白得透亮,眼睛不大但却很清亮、灵巧,头发随便用一根筷子挽成圆圆的髻,平时身上的衣物虽都是低廉面料却极为得体,给人清雅大方之感。
有人说,魏庆松虽身高体壮,但却“不行”,邓桂芳嫁给他实属无奈,至于为什么无奈,却没有人能说清缘由。也有人说,邓桂芳和魏庆松现在的儿子,根本就不是魏庆松的种,因为他没有男人的功能,属先天残疾。
邓桂芳活跃,心地善良,不管什么人都能友好相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没人看到她板过脸,没听到她和人发生过争吵。
魏庆松在森工企业时,不但拼命工作超额完成任务,对手下工人要求也相当严,任何人想请病假都难;学习时逼着每个人发言,时时强调必须跟上革命形势,稍微不对就大声苛责,比领导还严厉,弄得好多人都不愿在他的班里工作,几年下来,不少人对他印象都很差,背后骂他为“屁巴虫”。可看在邓桂芳的面上,也没有人和他过分计较。到了人防工地,虽改了急功近利的毛病,却仍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
好几次听刘有德喝了酒,摇头晃脑发泄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被敲了脑袋的老子鸣冤,欧阳文宇感到烦了,不以为然地说:“刘大哥,我劝你还是多看点中国近代史,多了解建国以后党的历次运动吧。你老爷子不过一名普通人,错杀了算什么?冤死的大人物多着呢!死了就死了吧,活着的人想开点,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