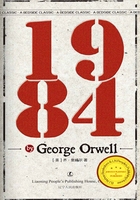无论如何,我是这局棋里坚持到最后—个的棋子虽然我的对手和同伴都已经放弃一
第一眼看见林沉。追求他。众人皆知,轰轰烈烈。
不是没有人跌破眼镜。如常生。将我从头到脚扫射:微白。我的名字在他嘴边滴溜溜打个转,最终是一颗枣,囫囵吞下去。
我知他欲言又止。多年来我是纹丝不动的女子。抱书辗转在教室和图书馆。夏天穿一件白衬衣、卡其裤子。冬天便是烟灰毛衣。戴黑框眼镜,面容沉静。春心不见,只一潭古井。脑门上写三个字,奖学金。是谁呵气如兰在我耳边笑,白白,你周身是雷达气息,这世上男人多如蚊蝇,谁敢靠近。
大三这个夏天,我却似突然变成虬髯豪放客,坐镇赌局,拿出全身积蓄荷尔蒙,只一谋面,统统梭哈在林沉的身上。
这样鲁莽轻率,大失水准。将我多年来纯良素白形象一脚踩黑。常生会瞪大眼睛,无可厚非。但是他终于没有开口询问或责备。他看我眼神开始百折千回。最后终于只剩下一声叹息,微微而怅然。
死者已不可追,活下来的突然醒转要开始享受人生,未免不是好事。纵然那个叫沉的男人,声名如此恶劣。这是我自常生日记簿上看到的一句话。一本墨蓝封面的本子,自他七岁时候一直记到22岁。常生的一生也便是这样一本薄薄履历。翻开,合上。
二
在九月的黄昏看见林沉。赤裸上身,带球过人,神采飞扬。
我侧身去问常生,他就是林沉?
他的球风十分出挑,神情多睥睨。唇角有一带上扬弧线,但是毫无笑意。
接球,跑动,侧身,过人。站定。手臂做完美滑翔,气定神闲。咣当一声。
我在中场间隙,走上去,递给他一支笔。然后摊开掌心。
当晚我即拨打手中的号码。我说,我是微白。我喜欢你。
他呵地一声,懒散沉郁。
就那样同他走起来。
看他每一场比赛。结识他身边同学。为他拿衣服送水。包揽所有作业。接吻。迎承他手指自我领口的每一次下滑。
偶尔校园里看见他揽着别的女子经过。会走上去,微笑,你何时有空,我等你吃饭。
林沉说他不爱长发女孩。我立刻起身去剪。林沉提到的若干书籍、电影,我尽力搜罗来看。林沉是我的天与地。
死心塌地毫无埋怨。
我的初次结束在校园外一家看片场所。8块钱一张单片。林沉连衣服都未曾褪去。直奔主题。事后我神情自若擦拭血迹。虽然双腿颤抖如棉絮。
林沉终于凝视我,伸手捞起我面前汗湿刘海,微白,你这样对我,真不值得。
他的声音有些许柔软,眸中开始有微微绞痛。
三
微白,你那样对他,真不值得。
常生终于不能按捺。他的语气那样绝望,因为不知如何拿捏愤慨,拳头握紧又松开。
他看到林沉在校园里公然同人接吻。
我轻轻地笑。常生,那是他的自由。我并不是他的任何人。
常生又开始头痛,微白,你说的什么话。你是他女朋友。
他和七岁时并未有太大变化。依然是直接简单的男人。还是曾经那一把笑语嫣然,俯在我耳边,白白,常生脑中脉络永远都是一条单行线。
我们自七岁相识。街坊小孩自成群体,我是被排斥的那一个。惟独常生待我亲厚每每有人指着我奚落,常生总面红耳赤站出来同他们理论。虽然理论从来不能收到效用。
我记得有一日他们应允我,倘使我能替他们每人做好功课,那么日后,他们便携我入团体。彼时我渴望混迹于大帮孩子中穿梭小巷,呼啸来往,做各种游戏,不用日日枯坐看天井蚂蚁。所以一直加紧不停写,直至手指握不住笔。待他们验收,看我眼巴巴的神情,却都哄笑如鸟兽散。有一人对我叶口水,他说,她爸爸是酒鬼,她是笨蛋。
然后常生不知从哪里冲出来。
可惜常生到如今也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并非付出就该有回报。你的信任、付出、爱或不爱,其实都只是一个人的事情。能获得公平回报不是应该,而靠机缘。
他这一生都未能明白。只宁愿做十几年前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倔强地瞪着眼。
林沉没有拒绝我,不代表他已经接受我。
身体倘使不因灵魂支配,那么怎样亲密都毫无意义。
我是无数送货上门女子中的一个。不是他的女朋友。
他能怎样对我,自然可以如是对别人。
四
12月,身体不适。遇见凉秋。
我和常生在一起吃饭。这个女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她点烟的姿势相当熟练优雅,但是牙齿细致洁白。我叫凉秋,席凉秋。认识一下,我很久没有看到林沉身边有这么够水准的女孩子。
她的笑声有一点点沙哑。身段面容都是经过磨砺的女人,但是她一边说一边对着常生笑,吐了一下舌头。相当天真。常生愣了一愣。
她给我们留下了手机号码,然后拿起筷子不客气地吃掉了一只鱼头,才起身离开。
走的时候她搂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对常生做了一个响亮的飞吻。这样率性。常生在回学校的路上喝醉了一般同我说,微白,我似乎在哪里见过她似的。虽然我可以肯定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轻轻地咳嗽,腹中隐约作痛。
林沉的孩子。两个月。
我在电话里一言不发听林沉不停地诅咒。最后他的声音冷静下来,他说,微白,你不要指望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笑,林沉,告诉你,因为你有知道的权利。除此,不代表任何意义。我一个人的事情,自己会处理。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凉秋。手术的那一天,打电话给她。
套上手术服躺到仪器上去的时候,凉秋再次拥抱我。她说,宝贝,我在外面等你。
五
麻醉散去七八分,睁开眼,看见的是凉秋喜悦的面孔。
我的眼睛开始不停地出汗。虚弱地喘气,看她使劲按住我的手,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
住到凉秋那里。出了一周的血。
第一个夜里,感觉自己沉浸在泥淖里,双脚踩进去,深陷。粘稠冰冷。双手绝望地四处伸张,只握住空气。牙齿发出战栗的声音。心脏是黑暗的深海。蜷缩,蜷缩起来。
有一具温暖的身躯贴上来。嘴唇自我的锁骨辗转往下,一吮就是一朵碎梅。
海水开始上涨,漫过入夜后沉睡的沙滩。呼吸细密交缠。终于伸出手去,拥抱她同样坦白细腻的身体。
常生隔三岔五来看我。
买我爱吃的翅膀和凉秋最喜欢的泡椒凤爪。
我依然还是安静的样子。穿黑色毛衣长裤,缩在沙发上看电视。凉秋和常生一起做饭或者下棋。也有的时候,因为困意而没有胃口,让他们两个一起去外面吃。
元旦。总算慢慢有起色。三个人一起去学校附近最大的酒吧庆祝。
凉秋去洗手间。常生坐到我身边来对我说,微白,我爱上凉秋。
我挑起眉毛。他的神情在昏暗灯光下依然兴奋烧灼,我开始扯开嘴角,却这般萧瑟,常生,她爱你吗。
那是当然,为什么不呢。常生孩子气的喉结动了一下。她怎么会不爱我呢,我这么爱她。
常生的公平和等价原则。可是常生,这个世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常生,或许真相不是你能够想象和愿意接受,但是总有一天你要尝试着接受。
常生总是迷糊的表情。然后他嘟囔,微白,不要因为林沉的恶劣,你就见不得这个世界上别的两情相悦。凉秋身边没有任何男人出现。我们相爱。
微白,你整个人变了很多。你要放开怀才对。微白,未央已经走了。我们活着的人,生活还要继续。
我的小腹又开始抽痛。我把自己轻轻地趴到桌子上去。
六
那一个晚上,我推开凉秋的身体。她的手指辗转向下,但是我把自己往墙角缩进去。
她支起身体来看我,气息紊乱有一点恼怒。
我倔强地看着她,我说,凉秋,我不想。
她把自己披散开来的头发拨到耳边去。她开始镇定下来,是今天不想,还是一直以后都不想。
这是一个错误。我听见自己清晰的陈述,然后听到清脆的巴掌的声音。
我再次闻到粘稠的血腥气味。面孔炸裂,寂静夜里脑袋中嗡嗡的回响。
她咬牙切齿地说,微白,我们必须相爱。我们只能相互陪伴。忘掉那个女人,她已经死了。
在搬来这里的第一个夜里,在身体的互相抚慰里,在情欲如潮水将我淹没的瞬间,我紧紧地拥抱着凉秋的身体,我嘶哑着喊出那个在心里尘封许久的名字,未央。我全身颤抖着喊着这两个字,像多年前的第一次。未央。血液的汹涌叫人迷醉。她鲜花一样芬芳的身体,她咬我的耳垂,她笑的时候能听到沙沙的雨点声,白白,你要发誓一直爱我。你们都要爱我。
未央已经死了整整五个月。
七
搬回宿舍。提着自己的衣服从学校的大门口走进来,一路是疏旷多日的篮球场、食堂、图书馆长廊。冬天那样寒冷,把面孔钻进男装外套的领子里面,眼神漠然。
身后轻轻地叹息。沉郁的嗓音有一点点哑,他喊微白。
喝一口咖啡。贪恋地用双手捂住,我知我面孔苍白如纸。
林沉的手指抚过我的眉眼,他的眼眶开始渐渐泛红。他终于说,对不起。
不知为何总剩下笑容。指面擦去他眼角的濡湿,傻小孩,都过去了。我现在很好呢。手术做的是全麻,并不痛呢。林沉,你知道吗,有些晚上,我会突然看到他的样子,他是个男孩子,长得很像你。眼睛很大很黑。我总是一遍遍对他说,不要怪妈妈。你来的不是时候。
林沉的眼泪大滴大滴地下来。
我还是没有回到宿舍。自凉秋那里出来,折返入林沉的房子。
正式开始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