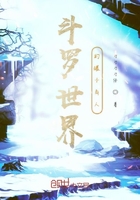罗城的城墙之上,一阵烟飘起,不像平常般洒脱灵动,反而来势汹汹有一股肃杀之意,昂然先动了,猛然的到鸢里的身后,手中刀片如大雨般倾洒而出,“叮叮叮”一阵急速的金属碰撞的声音过后,鸢里并没有动,眼都没眨一下,昂然与鸢里中间横着一条铁锁链,只一条锁链便挡住了所有的刀片,刀深插入城墙上,刀是毕缠的刀,锁链是刀上的锁链,。
鸢里转不急不慢的转过身,把扣在手心的里匕首转了一个圈向外握住,“哼哈。”毕缠阴冷的一笑,将刀用锁链拽了回来,刀身拖在地上发出刺啦的声音,有些令人烦躁,毕缠将刀重新握在手里,两把刀往肩上一抗,耸了耸肩。
毫无征兆,毕缠又是一耸肩,两把大刀带着铁链像一往无前的飓风一样奔向任平生,任平生也终于动了起来,掏出那柄铁匠铺的偷来的破锤子,砸开一把刀,用手抓住了另外一把刀末端的铁环,似乎他的锤子都是用偷的,任平生用力拽住铁环,浑身的肌肉都联动起来,毕缠顺着力道一跃而起扑向任平生,另一把被砸开的刀已经回到了毕缠的手中,左手用力抖动铁链,用手砍向任平生抓着铁环的手,瞬间在空中完成了这一连贯的动作,任平生只得放手举锤格挡,当的一声清音回荡在城墙之上,大刀与铁锤接触,毕缠仅退半步,任平生三步有余,虎口震得发麻,怒目圆睁盯着毕缠。
另一边,昂然依旧用着急如雨,一片接着一片的刀片射向鸢里,鸢里不紧不慢地挡着,似乎游刃有余,昂然用余光瞄了瞄毕缠,变换着步伐向任平生方向接近,鸢里似乎看出了昂然的想法不再被动的拆招,身体一拱,借力用城墙弹射出去,手中匕在手心飞速旋转形成两道炙眼的光芒,在远处看仿佛两道白玉盘比月亮还圆还亮,鸢里在空中一转身将两道盘甩了出去,盘的光亮映在了那张让女人都嫉妒的脸上,昂然皱了皱眉头抽身后退:“天南匕连环,双珠盘月圆,你竟然会这天南双匕,天南客是你什么人。”鸢里并不回话,手中双匕也没有因为昂然的问话停下,双匕再次飞向昂然,昂然化作一阵烟从双匕之间穿插而过来到任平生身边,抬手三片刀打退了正在纠缠任平生的毕缠。
昂然用手伏在任平生肩上,因为连夜的逃跑打斗有些气喘吁吁:“不能恋战让他们缠住,想办法甩开他们。”
毕缠又是哼哈的一阵冷笑:“你们走不出去,交出奥澜锤,一人一只手,我可以考虑放你们,来这里之前就应该想想这里是什么地方。”
昂然轻蔑的笑了下:“哦?是什么地方?”
毕缠三角眼眯成缝,捏了捏编成小辫的胡子:“是你们佣兵的噩梦。”
昂然支起了身子,继续拖延着时间:“是么,那真不好意思,我从不做梦。”又低声问了问任平生:“怎么不用奥澜锤?”
“他娘的有封印,非常强,这人来的话,吹口气就可以杀了我们四个。”任平生罕见的严肃,但今晚他已经好几次这样了。
似乎看穿了昂然这低级的伎俩,毕缠拖着双刀冲了过来,两把刀在地上带出两道火星,月亮不见了,一切都变得与刚才有些不同,整个地面像是被扎破的皮肤渗出红色的鲜血,以毕缠为中心慢慢散开,城墙,城门,远处的树荫,连墙上的青砖也染成红色,除了鸢里的双匕转成耀眼的光盘跟在其后,剩下的似乎都变成了红色,“红绵,恋双”很难想象毕缠这种形象居然会用出有这样四个字名字的招式,但他用了,而且还很强,双刀的锁链融入血红色中,化出无数的红色丝带将整个城楼都包裹了起来。
“至少点幽期。”昂然化身成烟躲避着如刀的红色丝带和双匕轮盘的纠缠,没有接到任平生的回应,昂然的目光找了找任平生,只看见任平生如雕像一样站在那里被丝带包裹住一动不动,目光呆滞。“灵魂秘法!”昂然惊呼出声。
“哼哈,终于被你发现了,同境之内还没人可以逃过我的红绵,所以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没受影响。”
昂然脸色阴沉,心有些发慌,又躲开了一条红丝带,扔出两片刀,刀片被红丝带弹开,并不能割断,抽身来到任平生旁边,半跪在地上,昂然已经闻到了死神的味道,昂然真的有些累了,但昂然不能累,累了会死,任平生也会,没人不怕死的,昂然也不例外,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样昂然又站起身,目光看着前方的毕缠和站在远处的鸢里从袖里拿出了四片刀:“这是我最后的刀片。”说着又低下了头。“哼哈,黔驴技穷了么,穷途末路了么。”毕缠说了一句肯定句。
“风灌其生,雨倾城。”四片刀片如蝴蝶般飞舞在血色的牢笼中,路过处丝带尽断,带起一阵浓烟淹没了这座城,淹没了昂然任平生。
“不好。”轻灵的声音响起,可比黄鹂,鸢里转起两把手中匕,“天南地北双飞客。”两道轮盘变成了无数道比刚才更耀眼,鸢里站在毕缠的肩上,双手交叉,无数的轮盘射向昂然所站之处,空气都变得扭曲,血红色的砖被刮出一道道裂痕,就连毕缠的丝带也都尽数斩断,然而城墙之上已没有昂然二人的身影。
罗城又安静了下来,月一如刚才的月,青砖也不再是血红,丝带也变回锈迹斑斑的锁链缠在毕缠的手腕上,两把大刀立起,立在这仿佛被刀风剑雨洗刷过的城墙上,鸢里站在昂然刚才站的地方,蹲下瘦弱的身体,用手蹭了蹭地砖:“大意了,这是遁招,但应该跑不了多远,追。”毕缠没有说话,拔刀跳下城墙,像城外丛林里追去,鸢里站起身,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肩膀上多了四只蝴蝶,美丽优雅,就像别人眼中的鸢里一样,美丽的事物从来都是被追捧的,鸢里轻声笑了出来像是一只被发现了秘密的小猫:“花俏的招式,华而不实,不学无术。”连着三句,都是贬义词,可从他藏在弯眉的笑意里却一点看不出不屑。
本来可以逃得更远的,但昂然实在没有力气了,从开始打便如此,此时又是背着任平生更是疲惫不堪,来本就是为了任平生而来,仿佛又看见了曾经在鄞州囚牢里,任平生拎着偷来的破锤子从郡里杀到郡外,从州内杀到州边救出被打断四肢的昂然,在连决观跪雨三天匍石五日只求一药可续肢,到普生寺做牛半年为马六月只为一榻可安神,如此情谊只因兄弟二字,任平生说过兄弟在侧,世间无处去不得,想着想着昂然挺起了腰让任平生可以更舒服些,“你说过我属猫有九条命,分八条给你,我们会活着,兄弟。”
“有些人九条命也不够死,有些人一条命可行天下。”
不知不觉二人已经逃到一悬崖边,昂然太累以至于辨不清方向,这是条死路,可这死路上有一个人,穿着黑色的皮大氅,手套在手捂子里,让人感觉已经到了冬天,他说了一句话,却让昂然提不起任何反抗的力量,闭上眼睛昂然都感觉不到有一个人在那里,比毕缠要强,比鸢里要强,比我们在一起都要强,就像是一座城压在心上。
“罗城城主。”昂然呼之欲出。
“在下,罗城,城主,姓罗,名孤城,罗孤城。”第二句话,语气温婉,如清风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