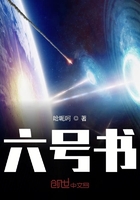阿雾几乎要拿到长矛,可是贺兰那一声呼唤令他分了神。阿雾的手与长矛擦过,他躲过雄鹿的冲撞,右腿一拐,单腿跪在地上。他立刻站起身来,仿佛看了一眼贺兰。然而贺兰从他的眼神里只看到一种模糊的疑惑,他不懂她,她明白。可是她又分明看到了他疑惑背后的那种动容,就像她也听见他手上那串手链格朗格朗的声响,清洌地,绕着圈,疑惑而犹豫地出卖他心底所剩的那些悲恸。
但是雄鹿似乎也受到惊吓,它失神而慌乱地奔跑起来,甚至撞上了长矛的末端,它坚硬的蹄子将矛柄踏碎,只剩下半截长矛仍旧插在土壤之中。
阿扎烈看准了这个时机,他身手敏捷地从鹿蹄下翻了过去,而后拔出了那半柄长矛。他正要得意洋洋去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不知怎的,那只失神的鹿已经掉转了头,向着他冲了过来。阿扎烈慌了神,人们也慌了,酋长手握长矛站了起来,可是他不能干涉这场斗争。雄鹿的刺尖犹如光针一般扎向阿扎烈的瞳孔,可是那道光晕却忽然向右一摆——是阿雾用自身从侧面向鹿身撞了过去,他与雄鹿都跌倒在地。
人们惊恐地呼出一口气,然而雄鹿却轻易地支起了身躯。自由啊,生命啊,万物那一点所剩的尊严啊,还有长风过境吹乱的沙沙树松啊,生命的组曲在这个节点激烈地相遇了。雄鹿恼羞成怒地看着阿雾,踏动了鹿蹄,人们的心再次悬到了鹿蹄之下,妇人们甚至不由自主闭上了双眼。
但贺兰没有闭眼。
她努力睁着眼,手紧紧握住围栏。她终于看到阿雾用最后一点力气,娴熟而精准地握住了雄鹿的犄角根部。她深呼吸了一口气,她知道这是阿雾最后的办法,用自己所有的力气与这只鹿角斗——可是这种厮磨,仍然是将性命放在天平之上摇摆着。杏杏的眼角落出大滴的泪,只有贺兰在人群中呼喊起来:“阿扎烈!”阿扎烈猛然醒悟,他爬起身来握紧那半柄长矛,几步上前,趁着这局面飞快地刺向雄鹿的肚子……在那一刻,再一次的,她感到天地混沌一色,万物归零,世界变得像雪原一样无垠无望。人们的心终于落地,平息,可是贺兰的声音却小了。杏杏发现贺兰的眼角挣扎出两道利落的泪痕,她口中念念有词只是一句:“贺兰是要你救它,救它啊……”然而云层蔽日,众神合眼,酋长也站起身来,他朗声宣布了最终成功猎鹿的,唯一的赢家:阿扎烈。
这个夜晚,大多数人都团聚在广场的篝火边分食那只雄鹿。四处结彩点灯,人们欢笑着享受“征服”的胜果。那只雄鹿头是阿扎烈的宝贝,他捧着这个慈眉善目却鲜血淋淋的战果四处寻找贺兰的身影。可是没有人看见贺兰,同样,也没有人看见阿雾,杏杏。年长的猎人们走过来拍拍阿扎烈的肩,他们称赞他的果断,称赞他最后那一下多么精准而漂亮。但是阿扎烈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他谦虚道:“阿雾救了我。”酋长在这时走了过来,他轻易地总结:“你也救了他。你们互相是兄弟,搭档,但是最终决定一切的,只有一个人,你懂了吗?”
阿扎烈点点头。
酋长端起一碗酒,一饮而尽,而后伸手拿起另一碗递给刚刚成年的阿扎烈:“喝吧,今天是属于你的节日。”阿扎烈抿了抿嘴唇,他像是要做好准备跨越到另一个世界来,而这碗酒就是开启这个世界的通道。他一闭眼,酒入喉肠,苦劲过后那种甘甜的火焰在他的胃中彻底绽放。也许他感到自己终于得到了某种全新的昭示,但酋长知道,一切只是开始。
酋长看着阿扎烈被烈酒冲红了脸,旁敲侧击道:“鹿头是想献给那个女孩吗?”
阿扎烈爽快地笑着:“可我不懂,是不是女孩都喜欢刁难人?”
“你是猎人,是战士,越名贵的头颅就是你最好的战利品,也是你身份的标识。女人,爱的就是你的勇猛、强壮,当然会要你最好的宝贝。”酋长假意在人群里寻了一遭,而后笑道,“她没来参加你的庆典吗?”
阿扎烈不好意思地端起酒,再次一饮而尽,他的表情就像是个搞砸了表演的巫师。但是他们都知道贺兰在哪儿,他们都知道,甚至彼此对视,目光穿越喧哗畅快地人群望向同一个方向——那顶棕灰色屋顶是阿雾和杏杏的家。阿扎烈行了个礼,酋长意会地挥手,阿扎烈便抱着鹿头走了。但是酋长的眼神仍然跟随着他,警惕得很,仿佛他是自己放出去的一只诱饵。可是猎物呢?他舔了舔舌头,仿佛黑暗之中那顶棕灰色的屋顶也在按兵不动地与他对视着。酒好辣,就像调皮的火焰,把胸口那一把灵魂鼓动吹赶起来。可是还不够,还要加把料才行,真相——这把冶炼万物的炉火呀——还烧得不够旺。酋长召唤来了猎人,吩咐着:“让索克玛去接替阿默里,好好盯着雪原的动静。”猎人走了,不一会儿,阿默里来了,酋长警觉地看着毫无征兆的远方,就好像狩猎已经开始了:“你记得清楚吗?风雪之神出现的日子……”阿默里点头。酋长给阿默里满上酒,道:“你辛苦了,好好休息吧。”他看向黑暗,他心知肚明这森林里只有一个人是风雪之神出现那天到来的,可是为什么她要来?为什么还要派人回到她当初抛弃的族人里?果然——那把炉火啊,还不够旺,他要加把劲让真相烧出原形来。
歌舞呀,火焰呀,人群交叠,彼此手手相环围着篝火起舞。但是光芒融不到小屋里,小屋之中静静的。杏杏看着阿雾非常执着地剖开一条鱼,她撇撇嘴,有点心疼地说道:“我不饿。”阿雾的嘴角扬起一抹模糊的笑容,但手下仍然耐心地表演,与火焰交相辉映,就像是种掩饰。贺兰想起老贺兰曾经说过,火焰是一种精魂,它们带有“覆灭”的灵魂。冰雪与火焰之所以互为反极,并非因为严寒与灼热,而是因为冰雪意味着生命的静、缓、永恒、休止,而火焰则是完全另一种姿态——释放自我完全的能量去盛放,发光发热哪怕最终只成一捧灰。那种妖娆令她的倔犟又膨胀起来,她走过去,夺过阿雾手里的刀,而后将鱼串在刀刃上,放在火上烤。“就这么吃。”贺兰说。
她以为阿雾会生气,她希望阿雾生气。
可是阿雾带着一种无奈地表情看着贺兰,好似他已经足够年长到需要用“宽容”来面对她。他道:“你们都怎么了?”
杏杏跪坐在阿雾面前,伸手去握阿雾的手:“哥哥,你怎么了?”
“我没事。”可他伸手蒙住自己的眼睛,“我失败了,可是我没事。”
“你没有失败,你救了他,我们都知道。”杏杏求救似的看向贺兰。
贺兰抿了抿嘴,她不擅长铺垫,也不擅长旁敲侧击,在所有的战斗里其实她唯一不懂的是:“当酋长,那么重要吗?”
想不到阿雾直截了当地回答:“重要。”
“当猎人,带领所有人杀掉那些动物,按照这种意愿活下去——这种事真的重要吗?”贺兰觉得自己的声音就像火焰一样,带着惊人的温度。
“你想错了——当猎人,杀动物,或者主持祭祀带领族人随季节迁徙,躲避马上民族的追猎——这种事对我根本不重要。”阿雾坐起身来。贺兰发现他用一种难以望穿的严寒回应她,他的瞳孔就像是两块冰,透而亮,但是一望无际,无法抵临。他就是这样,总将最深的东西像老贺兰那般自我封锁,禁锢在永恒的底部。可是,为什么呢?她不懂,她知道他也不会告诉她。
一旁的杏杏却哭了起来,声音里满是自责:“哥哥,那你是为了‘风雪之神’的秘密吗?”
阿雾伸手抚摸杏杏的脸:“不是。”
他撒谎。
“两百年前,大巫医离开之前,把‘风雪之神’的秘密留给了酋长。历代只有酋长知道‘风雪之神’的真相。”杏杏摇摇头,“可是哥哥有没有问过杏杏?杏杏并不想长生不老。”
杏杏闭上眼,她轻声朗诵起来:“‘人的灵魂纵然有高尚的一缕,却也有着致命的缺陷,若不能背负时间的枷锁,肉身一旦长久,灵魂便会因失控而腐坏’——妈妈最喜欢的这一句,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一句。大巫医不会背叛我们,她只是知道没有人可以接受‘长生不老’的试炼。长生不老不是成年仪式,不是可以征服的雄鹿之神,它是灵魂要和时间永远纠缠,理智要在每一次挑衅中战胜腐坏啊!”
“但她不是长生不老了吗?”
杏杏没有说话。
可是贺兰没想到,接下来阿雾那寒冷的眼神会毫不留情地望向她:“你是长生不老的,对吧?”
“哥哥!”杏杏尖叫起来。
“我开始只是猜,‘风雪之神’是为了你而来。”阿雾说道,“也许酋长也在猜,也许阿扎烈也在猜。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可是我的的确确找到了你不是一般人的证据——”阿雾拎起那条被他剖开的鱼,那条鱼几乎没有鳞,肉白色,眼睛发出幽蓝色的光晕,鱼骨修长妖冶呈半透明色,“森林里从来没有这种鱼。贺兰,你就叫贺兰,你就是大巫医,对不对?”
那堆火焰一瞬间像是膨胀开来,就像空间要裂开,有什么要从中走出来。
是真相吗?
可是并没有什么真相。
她只知道自己绝不能承认自己是贺兰,绝不能。然而她料不到阿雾忽而在她眼前单膝跪下,他的虔诚显然在精疲力竭之后:“大巫医,你知道我为了什么对不对?”
贺兰不知如何应答。
阿雾看向杏杏,杏杏惊恐地摇了摇头。她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敢相信吧。然而阿雾伸出手,邀请他弱小的妹妹一起参与到这祈愿的仪式里,他们一起看着贺兰,好似在等着她给予那么零星的希望。可是她没有感到任何无上的权力,却有一种柔软却腹背受敌的悲凉。她还想说“我不是”,可是她不知为何却对那种轻柔的重压产生了一种怜悯。她看着阿雾,阿雾也看着她。火光模糊的眼睛里他们共有一个荒芜的雪原。然而她的荒芜为无尽的生命,而他为了荒芜的尽头而饱受折磨。
她真傻。那种长久的对峙明明已经将真相泄露了。可是她仍然无法适度地去迎接这另一个极端。只是打破一切的却是卡加——它忽然大叫着冲出了房门,那一声吼叫将寂静的平衡打破了,撕碎了。阿雾跟了出去,贺兰也想走,可是她迈出一步自己的腿就不再放过她。她只能被杏杏搀扶着,而后看见阿雾领着卡加回到了屋子里。
她终于明白,在自己焦急地寻找屋外真相的那一刻,她的身份就已经向他们败露了。
阿雾非常冷静地圆谎:“……卡加大概饿疯了,根本没有人。”
也许这也不算谎言吧。阿雾确实没有在门外看见任何人,他只看见一小块血渍。新鲜的,鹿头所滴下的血。血滴向着人群的方向蔓延了一两滴,却又最终拐向了大森林的方向。
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他们不会达成新的墨守吧。他们无需言语,但是一切都变得不再相同了。阿雾替她和杏杏熄了灯,自己去了另一间屋。那种全新的黑暗与寂静像是一个在窥探她的妇人,躲得很远,那么多疑,但是正眼对视时却端庄得不留痕迹。贺兰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过了很久,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黑暗里拼命挣扎,可她也忘了自己沉沦下去的那个节点。所以她也不知道,当她睡着,阿雾就像影子一样悄然离开了小屋。
杏杏不知道阿雾要去哪儿,阿雾也自己也不知道去了又能怎样。他疑惑地挑了把趁手的匕首,踏着黑暗,牵着卡加就往大森林里去。卡加熟练地顺着那道血腥的气味追踪着,绕开陷阱,路障,在黑暗如迷宫一般的森林里从容地追随。幸好那滴血迹没有往酋长家的方向走,否则一切就完了。可是他找到阿扎烈又能怎样?他搞不明白自己那颗怦怦跳的心究竟想要把什么圈成他的牢。他最后捏着自己命悬一线的心,在卡加的带领下来到一处森林之中的湖水边。远远地,他看见阿扎烈坐在高处光滑的岩石上,鹿头放在一边。显然,阿扎烈并不吃惊,他像是早有准备的应战者,在月光下站起身来。见他如此积极的姿态,阿雾也微弓着身子放慢脚步围绕阿扎烈踱起步来。可是他们彼此打量,试探,周旋,却没有谁更靠近一步。若不是黑暗的森林里迅速蹿过什么动物,他们也许还能镇定地对峙下去。可是那一瞬,两人几乎同时动摇了,阿扎烈手握长矛迅速从高处跳下,阿雾也摸出匕首绕过阿扎烈进攻的方向,两人手持武器靠近了,却又在分秒钟共同维持那种冷静周旋。要怎样?他们也不知道要怎样。赢又怎样,输又怎样?他们全然不知。但是就在面对敌手伺机而动的那一瞬,他们朝彼此冲了过去,阿雾哼笑了一声,只要绕过阿扎烈笨拙的长矛就有机会。但是千钧一发之际,阿扎烈却忽然将长矛插入土中,而后奔向阿雾,弯身下蹲,对准阿雾的腹部给出猛烈的一拳。阿雾吃痛地倒在地上,想要起身还击,可是阿扎烈扭住了他的双手。
“你输了。”阿扎烈松开他的手,“虽然白天是你赢了。”
阿雾并不领情:“我不需要你给我公平。”
“那你需要什么?”阿扎烈质问道,声音有别以往的冷淡。
阿雾不在乎他的装腔作势,然而等到阿扎烈回过头,他才发现阿扎烈的眼神里都是混浊的提问,他才明白那些血滴为什么最终会没入森林。可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恨透了阿扎烈这个选择:“你那么喜欢她?”
“混账。”阿扎烈巴不得给阿雾再来一拳,“我不知道。”
说谎。阿扎烈知道,否则他带着秘密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他不是要找个足够清冷的地方,把秘密永远地扎成蝴蝶结,尘封得特别完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