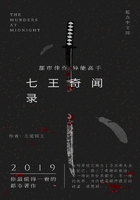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流逝的时间就像是亘古而来大江东去的滔滔洪流,永不休止,更没有尽头。人们有时就像是乘舟江流的游客,刚刚醉心于所见的静影沉璧皓月当空之美景,再一睁眼,满目或是另一番萧然,美景却已被自己远远地甩在身后,诚如美好的年华一去不返。
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当你在经历它时,它很漫长;但当你在经历过后回首它时,它却极为短暂。仿佛上个刹那,就是一个人最最难忘的瞬间,可就在闭眼,睁眼间,回忆就真的永远成为了回忆,而当它再次闪现的时候,心里或许唯余剪不断的淡淡哀愁,或许是温暖的打动心弦的小小感动,或是其他的只有自己才能诉说出的细腻情感...
人生就像一壶酒,时间好似壶底的那团火,越是烧,越是煮,壶里的酒越是甘醇,香气越是浓郁。
这是朱,岳,古三人见面的第四十二天。
是夜,岳子杨,古三通,朱无视,三人以天为盖,地为炉共同煮了壶人生佳酿,甘洌的酒香让他们一生难忘。
正是诗云:
湖光皓月九千里,拂面弄发杏花风。
狂歌对酒三豪杰,英雄谁无傲世时?
古三通:“对酒,当歌,人生几,几何。”
朱无视:“譬如,朝露,去,去日苦多。”
岳子杨:“慨,当,以康,忧思,忧思难,忘。”
“何以,解,解忧?唯有,唯有,唯有什么酒?”古三通怀抱着酒坛子四仰八叉地卧在地上,“咕咚咕咚”地再次灌下一大口酒,右手指着湖边的古柳树大叫道:“岳二哥,你,你告诉我。”
“哈,哈哈,老三,你醉了,你对着老子的师傅瞎嚷嚷个啥!对我师傅大喊大叫,老子,老子就是不告诉你,不告诉你,是唯有杜康!”岳子杨左手拄着剑右臂跨在朱无视的脖子上吐着满嘴的酒气万分得意地叫嚣着,耳朵边儿嗡嗡着朱无视毫无逻辑的琐碎话语,飘也似地迈着凌乱的步子,鬼使神差地绊在朱大哥的左腿上,两个大老爷们儿就在素心的眼前抱在一起狼狈地摔在了地上,懒驴打滚似地滚上几圈,沾了满身的泥土,勿自喋喋不休,骂骂咧咧的。
素心快步跑到表哥古三通面前,放下右手里装满三大碗醒酒汤的篮子,打开,小心翼翼地端出一碗,吹开碗上面蒸腾的水汽,亮晶晶的宝石双瞳里装满了古三通,柔声道:“表哥,素心给你带了更好的酒,听话,把它喝了。”她最是清楚,醉酒之人绝对不能说他喝醉了,不然必起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争执。
古三通笑嘻嘻地盯着面前的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未婚妻,嗅着自小便习惯闻到的淡淡香气,在酒精的作用下,或是说在内心深处的呼唤下,凑过脸去,满是忐忑地亲在了素心浸了层月光的脸蛋上,在嘴唇软软腻腻的触感里察觉到火热异常的香气吹在脖间,弄得他像掉进了火坑。
“表哥,你,你要听话,把这“酒”喝了!”素心紧绷着身子颤抖着软语小声嗫嚅道,脑子一片空白的她还是坚决地执行了“不能让表哥醉酒”的意志,轻飘飘的感觉像在云端。
“好,我马上就喝,别说是酒,就是毒药你让我喝我也喝!”古三通接过青花瓷碗,仰着脖子一口气儿酎了下去。温热的汤一下肚,内功深厚的他酒劲儿便被顶了过去,抱着碗温柔地看着素心,直欲仰天长啸一抒胸中柔情,他多想告诉这片天地此时自己心中的狂喜。
素心低着头不敢看表哥的眼睛,眼睛飘忽着低声道:“表哥,你去给朱大哥还有岳二哥他们喂汤!咱们不能叫他们醉在外面。”像是只受了惊的小兔子似地躲避着让她心跳加速,血液沸腾,难以呼吸的目光,转过身子把身后的竹编食篮递给表哥。
古三通目不转睛地看着素心,听到她那句羞怯“咱们”心底涌上祥和暗道:“只要扛过这次跟八大门派的恩怨,我古三通一定封剑归隐,和素心好好地过完下半辈子,天下第一,和素心比又能算得了什么?”接过由灵巧女儿心编织的竹篮,左右手抢着端起剩余的两碗汤,一边喝上一大口嘟嚷道:“我家娘子做的汤,不给他们喝!”冒着肚皮破掉的危险强灌下后,把碗一扔,用洁白的袖口擦擦嘴,拽起素心的柔软小手得意地跑开了。
把两个结拜的好兄弟扔在太湖边吹了一夜的凉风。
“这古三通也挺不地道啊!哎,我说,老头儿,你们俩真傻,人家主场作战还有后勤保障,你没个脑子啊你!你把华山派的脸都丢到月亮上去了!”江小龙听后忍不住伸着手指头指着岳子杨鼻子跳脚骂道,他和岳子杨向来是没大没小的惯了。
岳子杨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江小龙重复往日的对骂,撇着嘴“哼”了声,道:“你小子知道个屁,朱无视和老子摔那一跤就醒了,你啥时候见过我给华山派丢过人!”岳子杨本是豁达的豪杰,虽说后来经受大难,性情大变,但也还没到和一个小孩子斤斤计较的地步,江小龙骂他蠢,骂他笨,他都不在乎,皆能一笑了之,可是一旦涉及到华山派名誉的事情上,岳子杨绝对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便是没理也得绞尽脑汁地讲出个三分道理来。他深受上代华山派掌门的大恩,恩师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门派清誉,折辱自己倒无所谓,辱及先师最看重的东西却是不行!岳子杨对没能报答师傅的恩情半生耿耿于怀,如今依旧用朽朽残躯守望者般地守护着在江小龙眼里半毛钱也不值名声,可叹,亦可敬!
“废话,你丢人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上哪儿见着去?”江小龙抻着椅子拖到门边儿不屑地“呸”了一口,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却苦涩地发现,刚刚还斜照的夕阳现在已经被视野尽头的连山吃下去大半儿,远处山峰横接的缝隙,像是一张又一张丑陋的嘴巴,撕扯着挣扎的残阳,令人生厌。他不由得心里一软,双手又重新抱起凳子坐到了岳子杨的对面,柔声道:“师傅,那后来呢?”
这,恐怕是江小龙头一次叫岳子杨师傅。
老头儿长,老头儿短个听习惯的岳子杨被这一句“师傅”叫得一愣,浑浊又发黄,涣散而失神的眼睛里闪现动人的神采,那种光,像是久候闺中的妻子等到征边丈夫平安返家时流下晶莹泪珠中的七色光华;像是苦候春雨而不得乍闻惊雷声的老农民淌在褶皱遍布皮肤上汗水折射出的油亮希望。
“呵呵,你且听为师细细道来…”岳子杨伸出手去摸着江小龙的漆黑头发万分平静地说道。
那天晚上,古三通是在素心的房里睡的;
那天晚上,朱无视真得喝醉了,醉得人事不醒;
那天晚上,只有岳子杨睡得最为安详。
事情,事情就是在那天晚上开始走向了自私的深渊,罪恶的地狱。
素心挽起了妇人髻,悉心架起的双刀发髻在第二日太阳洒下的金辉里散发着柔顺的光泽,万千青丝,万千情思,万千柔情,密密地紧紧地扎在一起;典雅大气的朱钗像是爱之神丘比特的圣箭,那碧玉的簪子把两颗心连成串,在她们心里孕育出微疼的甜蜜。
然而贴在一起的心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伤口,或许,丘比特先生应该考虑换一种更加温柔的把心连在一起的方式,我想,胶水会是更好的选择。
双刀发髻,发髻如刀,它狠狠地重重地残忍无情地割着朱无视只有在面对素心时才会表现的柔软之心,绵绵无绝期的伤痛,真让他恨不得掏出怦怦跳的心脏,砍下那深入骨髓般刺痛的地方;可是他又好舍不得,舍不得那种为素心而喜,为素心而忧,为素心而伤痛的感觉,舍不得在刻骨铭心的疼痛中隐含着的那股难以名状的莫名快意,当心被紧紧攥住时的那种仿佛停止跳动的窒息感竟是让他如此迷恋。
“我一定是着魔了。”朱无视心底道。
逃难也似地不辞而别,向来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的朱无视头一次如此羡慕一个人,或是说用嫉妒形容更为贴切。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生出了不可抑制的情感,爱上了一个绝对,绝对不应该爱上的人,可是,可是他控制不住如火山般喷发的情感,奔涌的热血像滚烫的岩浆毁天灭地似地摧毁他的理智,飞蛾扑火一样傻地在黑暗里追求那触之即死的禁忌之光,素心就是挣扎在冰天雪地里的他毕生所追求的太阳。一个从生下来就缺少温暖,成长途中渴望温暖,成才之后苦寻温暖的高贵的可怜人,没有谁能体会到那种瑟缩在阴暗角落里流着血泪奢望温暖的无助与绝望,背在人后默默舔舐伤口时的那种对光明的企盼和希冀。
朱无视终究不过是个可怜人,一个高贵的可怜人,一个宁愿用生命换取温暖的可怜人。他没有娘亲疼,父皇也不喜爱,兄弟姐妹更是想着办法地算计自己,巴不得他犯下大错被严厉地惩罚。亲情,血脉在皇族里除了带来身份外没有半分价值,所谓的帝族贵胄,天家荣光不过是权力之下冷漠绝情,灭绝人性的遮羞布罢了。
素心并没有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绝世容颜,却有着世上最善良的心灵;她的性子柔得像水,又烈得似火;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如此得自然,柔美,像是盛开在空谷的幽兰,淡雅,绝尘,没有一丝肮脏的世故,静静地绽放着她特有的美丽,不求人观,不求人赏,一切都是在用发自内心深处的天性来表达,一个干净的让人忍不住捧在手心里悉心呵护的女人,任何对她的伤害都是世界上最为残忍的事情,不容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