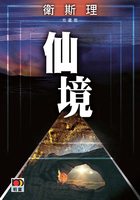胡雪岩上船下船,一向在介乎元宝街与清河坊之间的望仙桥,螺蛳太太怕惹人注目,所以有此劝告。但胡雪岩的想法不同。
“既然一切照常,我当然还是在望仙桥上岸。”胡雪岩又问,“罗四姐原来要我在啥地方上岸?”
“万安桥。轿子等在那里。”乌先生答说,“这样子,我在万安桥上岸,关照轿子仍旧到望仙桥去接。”
胡雪岩的一乘绿呢大轿,华丽是出了名的,抬到望仙桥,虽然已经暮色四合,但一停下来,自有人注目。加以乌先生了解胡雪岩的用意,关照来接轿的家人,照旧摆出排场,身穿簇新棉“号挂子”的护勇,码头上一站,点起官衔灯笼,顿时吸引了一大批看热闹的行人。
见此光景,胡雪岩改了主意。
往时一回杭州,都是先回家看娘,这一次怕老娘万一得知沪杭两处钱庄挤兑,急出病来,更加不放心。但看到这么多人在注视他的行踪,心里不免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是阜康的客户,又会作何想法?
只要一抛开自己,胡雪岩第一个念头便是:不能先回家!多少人的血汗钱托付给阜康,如今有不保之势,而阜康的老板居然好整以暇地光顾自己家里,不顾别人死活,这口气是咽不下的。
因此船一靠岸,他先就询问:“云青来了没有?”谢云青何能不来?不过他是故意躲在暗处,此时闪出来疾趋上前,口中叫一声:“大先生!”
“好、好!云青,你来了!不要紧,不要紧,阜康仍旧是金字招牌。”他特意提高了声音说,“我先到店里。”
店里便是阜康。轿子一到,正好店里开饭,胡雪岩特为去看一看饭桌,这种情形平时亦曾有过,但在这种时候,他竟有这种闲情逸致,就不能不令人惊异了。
“天气冷了!”胡雪岩问谢云青说,“该用火锅了。”
“年常旧规,要冬至才用火锅。”谢云青说,“今年冬至迟。”
“以后规矩改一改。照外国人的办法,冬天到寒暑表多少度,吃火锅,夏天,则多少度吃西瓜。云青,你记牢。”
这是稳定“军心”的办法,表示阜康倒不下来,还会一年一年开下去。谢云青当然懂得这个奥妙,一迭连声地答应着,交代“饭司务”从第二天起多领一份预备火锅的菜钱。
“阜康的饭碗敲不破的!”有人这样在说。
在听谢云青细说经过时,胡雪岩一阵阵胃冷,越觉得侥幸,越感到惭愧。
事业不是他一个能创得起来的,所以出现这天这种局面,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过失,但胡雪岩虽一想起宓本常,就恨不得一口唾沫当面吐在他脸上,但是,这种念头一起即消,他告诉自己,不必怨任何人,连自己都不必怨,最好忘记掉自己是阜康的东家,当自己是胡雪岩的“总管”,胡雪岩已经“不能问事”,委托他全权来处理这一场灾难。
他只有尽力将得失之心丢开,心思才能比较集中,当时紧皱双眉,闭上眼睛,通前彻后细想了以后说:“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这是一句总诀。云青,你记牢!”
“是,我懂。”
“你跟螺蛳太太商量定规,今天早晨不开门,这一点对不对,我们不必再谈。不过,你要晓得,拆烂污的事情做不得。”
“我不是想拆烂污--”
“我晓得。”胡雪岩摇摇手阻止他说,“你不必分辩,因为我不是说你。不过,你同螺蛳太太有个想法大错特错,你刚才同我说,万一撑不住,手里还有几十万款子,做将来翻身的本钱,不对,抱了这种想法,就输定了,永远翻不得身。云青,你要晓得,我好像推牌九,一直推得是‘长庄’,注码不管多少都要,你输得起,我赢得进,现在手风不顺,忽然说是改推‘铲庄’,尽多少铜钱赌,自己留起多少,当下次的赌本。云青,没有下次了,赌场里从此进不去了!”
谢云青吸了口冷气,然后紧闭着嘴,无从赞一词。
“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起来。”
“大先生这样气慨,从古到今也没有几个人有。不过,”谢云青迟疑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做生意到底不是推牌九。”
“做生意虽不是推牌九,道理是一样的,‘赌奸赌诈不赌赖’,不卸排门做生意,不讲信用就是赖!”
“大先生这么说,明天照常。”
“当然照常!”胡雪岩说,“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拿存户的账,好好看一看,有几个户头要连夜去打招呼。”
“好。我马上动手。”
“对。不过招呼有个打法,第一,一向初五结息,现在提早先把利息结出来,送银票上门。第二,你要告诉人家年关到了,如果要提款,要多少,请人家交代下来好预备。”
“嗯、嗯、嗯。”谢云青心领神会地答应着。
能将大户稳定下来,零星散户,力能应付,无足为忧。胡雪岩交代清楚了,方始转回元宝街,虽已入夜,一条街上依旧停满轿马,门灯高悬,家人排班,雁行而立,仿佛一切如常,但平时那种喧哗热闹的气氛,却突然消失了。
轿子直接抬到花园门口,下轿一看,胡太太与螺蛳太太在那里迎接,相见黯然,但只转瞬之间,螺蛳太太便浮起了笑容,“想来还没有吃饭?”她问,“饭开在哪里?”
这是没话找话,胡雪岩根本没有听进去,只说:“到你楼上谈谈。”他又问,“老太太晓得不晓得我回来了?”
“还没有禀告她老人家。”
“好!关照中门上,先不要说。”
“我晓得。不会的。”胡家的中门,仿佛大内的乾清门一般,禁制特严,真个外言不入,螺蛳太太早已关照过了,大可放心。
到得螺蛳太太那里,阿云捧来一碗燕窝汤,一笼现蒸的鸡蛋糕,另外是现沏的龙井茶,预备齐全,随即下楼,这是螺蛳太太早就关照好了的,阿云就守在楼梯口,不准任何人上楼。
“事情要紧不要紧?”胡太太首先开口。
“说要紧就要紧,说不要紧就不要紧。”胡雪岩说,“如今是顶石臼做戏,能把戏做完,大不了落个吃力不讨好,没有啥要紧,这出做不下去,石臼砸下来,非死即伤。”
“那么这出戏要怎样做呢?”螺蛳太太问说。
“要做得台底下看不出我们头上顶了一个石臼,那就不要紧了。”
“我也是这样关照大家,一切照常,喜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场面是可以拿铜钱摆出来的,只怕笑脸摆不出来。”
“难就难在这里。不过,”胡雪岩加重了语气说,“再难也要做到,场面无论如何要好好儿把它吊绷起来,不管你们用啥法子。”
胡太太与螺蛳太太相互看了一眼,都将这句话好好地想了一下,各有会心,不断点头。
“外头的事情有我。”胡雪岩问说,“德晓峰怎么样?”
“总算不错。”螺蛳太太说,“莲珠一下午都在我这里,她说,你最好今天晚上就去看看德藩台。”
“晚上,恐怕不方便。”
“晚上才好细谈。”
“好,我等一下就去。”
胡雪岩有些踌躇,因为这时候最要紧的事,并不是去看德馨,第一件是要发电报到各处,第二件是要召集几个重要的助手,商量应变之计。这两件事非但耽误不得,而且颇费功夫,实在抽不出空去看德馨。
“有应春在这里就好了。”胡雪岩叹口气,颓然倒在一张安乐椅,头软软地垂了下来。
螺蛳太太吃一惊,“老爷、老爷!”她走上前去,半跪着摇撼着他双肩说,“你要撑起来!不管怎么样要撑牢!”
胡雪岩没有做声,一把抱住她,将头埋在她肩项之间,“罗四姐,”他说,“怕要害你受苦了,你肯不肯同我共患难?”
“怎么不肯?我同你共过富贵,当然要同你共患难。”说着,螺蛳太太眼泪掉了下来,落在胡雪岩手背上。
“你不要哭!你刚才劝我,现在我也要劝你。外面我撑,里面你撑。”
“好!”螺蛳太太抹抹眼泪,很快地答应。
“你比我难。”胡雪岩说,“第一,老太太那里要瞒住;第二,亲亲眷眷,还有底下人,都要照应到;第三,这桩喜事仍旧要办得风风光光。”
螺蛳太太心想第一桩还好办,到底只有一个人,第二桩就很吃力了,第三桩更难,不管怎么风光,贺客要谈煞风景的事,莫非去掩住他们的嘴?
正这样转着念头,胡雪岩又开口了,“罗四姐,”他说,“你答应得落,答应不落?如果答应不落,我--”
等了一会不听他说下去,螺蛳太太不由得要问:“你怎么样?”
“你撑不落,我就撑牢了,也没有意思。”
“那么,怎么样呢?”
“索性倒下来算了。”
“瞎说八道!”螺蛳太太跳了起来,大声说道,“胡大先生,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
胡雪岩原是激励她的意思,想不到同时也受了她的激励,顿时精神百倍地站起身来说:“好!我马上去看德晓峰。”
“这才是。”螺蛳太太关照,“千万不要忘记谢谢莲珠。”
“我晓得。”
“还有,你每一趟外路回来去看德藩台,从来没有空手的,这回最好也不要破例。”
这下提醒胡雪岩,“我的行李在哪里?”他说,“其中有一只外国货的皮箱,里头新鲜花样很多。”
“等我来问阿云。”
原来胡雪岩每次远行,都是螺蛳太太为他收拾行李,同样地,胡雪岩一回来,行李箱亦照例卸在她这里,所以要问阿云。
“有的。等我去提了来。”
那只皮箱甚重,是两个丫头抬上来的,箱子上装了暗锁,要对准号码,才能打开,急切间,胡雪岩想不起什么号码,怎么转也转不开,又烦又急,弄得满头大汗。
“等我来!”螺蛳太太顺手捡起一把大剪刀,朝锁具的缝隙中插了下去,然后交代阿云,“你用力往后扳。”
阿云是大脚,用脚抵住了皮箱,双手用足了劲往后一扳,锁是被撬开了,却以用力过度,仰天摔了一跤。
“对!”胡雪岩若有所悟地自语,“快刀斩乱麻!”
一面说,一面将皮纸包着的大包小包取了出来,堆在桌上,皮箱下面铺平了的,是舶来品的衣料。
“这个是预备送德晓峰的。”胡雪岩将一个小纸包递给螺蛳太太,又加了一句,“小心打碎。”
打开来一看,是个乾隆年间烧料的鼻烟壶,配上祖母绿的盖子,螺蛳太太这几年见识得多,知道名贵,“不过,”她说,“一样好像太少了。”
“那就再配一只表。”
这只表用极讲究的皮箱子盛着,打开来一看,上面是一张写着洋文的羊皮纸,揭开来,是块毫不起眼的银表。
“这只表--”
“这只表,你不要看不起它,来头很大,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用过的,我是当古董买回来的。这张羊皮纸是‘保单’,只要还得出‘报门’,不是拿破仑用过,包退还洋,另加罚金。”
“好!送莲珠的呢?”
“只有一个金黄蔻盒子。如果嫌轻,再加两件衣料。”
从箱子下面取出几块平铺着的衣料出来,螺蛳太太忽生感慨,从嫁到胡家,什么绫罗绸缎,在她跟毛蓝布等量齐观,但一摸到西洋的衣料,感觉大不相同。
这种感觉形容不出。她见过的最好的衣料是“贡缎”,这种缎子又分“御用”与“上用”两种,“御用”的贡缎,后妃所用,亦用来赏赐王公大臣,皇帝所用,才专称为“上用”。但民间讲究的人,当然亦是世家巨族,用的亦是“上用”的缎子,只是颜色避免用“明黄”以及较“明黄”为暗的“香色”,“明黄”只有皇帝、太上皇帝能用,“香色”则是皇子专用的颜色,除此以外,百无禁忌,但争奇斗妍,可以比“上用”的缎子更讲究,譬如上午所着与晚间所着,看似同样花样的缎袍,而暗花已有区分,上午的花含苞待放,下午的花已盛开。这些讲究,已是“不是三世做官,不知道穿衣吃饭”的人家所矜重,但是,比起舶来品的好衣料来,不免令人兴起绚烂不如平淡之感。
螺蛳太太所捡出来的两件衣料,都是单色,一件藏青、一件玄色,这种衣料名叫“哔叽”,刚刚行销到中国,名贵异常,但她就有四套哔叽袄,穿过了才知道它的好处。
这种在洋行发售,内地官宦人家少见,就是上海商场中,也只有讲时髦的阔客才用来作袍料的“哔叽”,在胡家无足为奇,胡雪岩爱纤足,姬妾在平时不着裙子,春秋佳日用“哔叽”裁制夹袄夹裤,稳重挺括,颜色素雅,自然高贵。她常说:“做人就要像哔叽一样,禁得起折磨,到哪里都显得有分量。”此时此地此人,想到自己常说的话,不由得凄然泪下。
幸好胡雪岩没有注意,她背着灯取手绢擤鼻子,顺便擦一擦眼睛,将捡齐了的礼物,关照阿云用锦袱包了起来,然后亲自送胡雪岩到花园的西侧门。
这道门平时关闭,只有胡雪岩入夜“微行”时才开。坐的当然也不是绿呢大轿,更没有前呼后拥的“亲兵”,只由两个贴身小跟班,前后各擎一盏灯笼,照着小轿直到藩司衙门,由于预先已有通知,德馨派了人在那里等候,胡雪岩下了轿,一直就到签押房。
“深夜过来打搅晓翁,实在不安。”胡雪岩话是这么说,态度还是跟平时一样,潇洒自如,毫不显得窘迫。
“来!来!躺下来。”刚起身来迎的德馨,自己先躺了下去,接过丫头递过来的烟枪,一口气抽完,但却用手势指挥,如何招待客人。
他指挥丫头,先替胡雪岩卸去马褂,等他侧身躺下来,丫头便将他的双腿抬到拦脚凳上,脱去双梁鞋,然后取一床俄国毯子盖在腿上,掖得严严的,温暖无比。
“雪岩,”德馨说道,“我到今天才真佩服你!”
没头没脑的这一句话,说得胡雪岩唯有苦笑,“晓翁,”他说,“你不要挖苦我了。”
“不是我挖苦你。”德馨说道,“从前听人说,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鸡鸣狗盗,到了紧要关头,都会大显神通。你手下有个周少棠,你就跟孟尝君一样了。”
周少棠大出风头这件事,他只听谢云青略为提到,不知其详,如今听德馨如此夸奖,不由得大感兴趣,便问一句:“何以见得?”好让德馨讲下去。
“我当时在场,亲眼目睹,实在佩服。”德馨说道,“京里有个丑儿叫刘赶三,随机应变、临时抓哏是有名的,可是以我看来,不及周少棠。”
接着德馨眉飞色舞地将周少棠玩弄黄八麻子于股掌之上的情形,细细形容了一遍,胡雪岩默默地听着,心里在想,这周少棠以后有什么地方用得着他。
“雪岩,”德馨又说,“周少棠给你帮的忙,实在不小。把挤兑的那班人哄得各自回家,犹在其次,要紧的是,把你帮了乡下养蚕人家的大忙,大大吹嘘了一番。这一点很有用,而且功效已显出来了,今儿下午刘仲帅约我去谈你的事,他就提到你为了跟英国人斗法,以至于被挤,说应该想法子维持。”
刘仲帅是指浙江巡抚刘秉璋,他跟李鸿章虽非如何融洽,但总是淮军一系,能有此表示,自然值得珍视,所以胡雪岩不免有兴奋的语气。
“刘仲帅亦能体谅,盛情实在可感。”
“你先别高兴,他还有话:能维持才维持,不能维持趁早处置,总以确保官款为第一要义。雪岩,”德馨在枕上转脸看着胡雪岩说,“雪岩,你得给我一句话。”
这句话自然是要胡雪岩提供保证,决不至于让他无法交代,胡雪岩想了一下说:“晓翁,我们相交不是一天,你看我是对不起人的人吗?”
“这一层,你用不着表白。不过,雪岩,你的事业太大了,或许有些地方你自己都不甚了了。譬如,你如果对你自己的虚实一清二楚的话,上海的阜康何至于等你一走,马上就撑不住了?”
这番话说得胡雪岩哑口无言,以他的口才,可以辩解,但他不想那样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就是不诚。
“雪岩,你亦不必难过。事已如此,只有挺直腰杆来对付。”德馨紧接着说,“我此刻只要你一句话。”
“请吩咐。”
“你心里的想法,先要告诉我。不必多,只要一句话好了。”
这话别具意味,胡雪岩揣摩了半天,方始敢于确定,“晓翁,”他说,“如果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一定先同晓翁讨主意。”这话的意思是一定会维护德馨的利益,不管是公是私。
“好!咱们一言为定。现在,雪岩,你说吧,我能替你帮什么忙?”
“不止于帮忙,”胡雪岩说,“我现在要请晓翁拿我的事,当自己的事办。”
这话分量也很重,德馨想了一下说:“这不在话下。不过,自己的事,不能不知道吧?”
“是。我跟晓翁说一句:只要不出意外,一定可以过关。”
“雪岩,你的所谓意外是什么?”
“凡是我抓不住的,都会出意外。”胡雪岩说,“第一个是李合肥。”说到这里,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唉!原以为左大人到了两江是件好事,哪晓得反而坏了。”
“喔,这一层,你倒不妨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