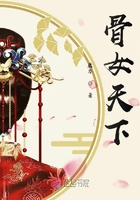犹大走后就再也没来过牢房,期间都是那两个技术员,轮着班,不情愿的,苦哀哀的,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大气不敢喘,小气不敢吸,磨叽推搡的进来给王仲禾吊上几瓶营养液后,就撞门逃了出去,怕身上染上晦气。
这一个月来,他们两个着实被吓怕了,对这个发生过地狱景象的房间有着浓烈的惧怕,对那个经历过地狱所有酷刑的人也是百味杂陈,有敬佩,有唾弃。
王仲禾这几天吃不上腐肉,喝不上血尿,咽不上蠕虫,小命就全赖这几瓶营养液给撑着。
他如今的觉很少,不敢多睡,为了一条命他丢了廉耻,丢了气节,丢了发肤。丢了这么多东西,哪个人能不痛?哪个人能不珍惜当下?
睡着了,这些被他丢弃的东西全是孤鬼亡魂,痛哭狼嚎的折磨他,拷炼他,让那怖人的过往一次次重新浮现,历历在目,让人心凉。
脑袋里浮想联翩,不敢停下来,可伤势总会把人的念头给勾回地狱来,王仲禾只能跟自己较着劲,硬往死胡同撞,狠钻牛角尖。
执拗的偏执,绝不回头。
暗无天日的地方,感受不到时间流转,分不出一天还是一年,反正都一样,是一天我就珍惜,是一年我就赚本。
活着做有意义的事,远不如活着有意义。
生来的大志抱负,在生死面前,浮云过往。
刺啦!
那道该死的门依旧没人上机油,声音难听的要死。
两个技术员掩着口鼻推搡进来,脸上作严肃,可又掩盖不了恐慌,表情很是怪异。
“真主大人请先生赴宴,支派小的来移送先生过去。”
话说的很快,跟机关枪似的,说完后就再也不敢张嘴。
王仲禾没说话,没说不答应。他不过一个阶下囚而已,就算对方说的再客气,摆在他面前的答案也只有个恭敬不如从命。
略带惊讶的看那两个技术员解开他身上的锁铐束带,从外面推进来一辆轮椅,两个人撮着牙花子,把不着片缕,浑身脓疮烂肉的王仲禾给抬到了轮椅上。
这是王仲禾第一次看清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左腿少了半截,露着一指长没磨完的白骨,腿上的肉片翻着,肉丝连着。右手没了手指,只剩了个掌心,光秃秃的,瞧久了,也能觉得它可爱。
被推着来到了外面的观察室,王仲禾口齿漏风,言语不清的道:“你们不给我上枷戴铐,也不怕我跑了?”
推着王仲禾的那个技术员紧了紧握把的手,手心湿漉漉的,咽了口吐沫,佯作淡定的道:“大人说了,若是先生能以这副身子杀进杀出,也是个英豪。丢上百来条性命,也是对先生的敬仰,甚值。”
王仲禾勉笑:“你们大人看的透彻。”
上到宫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王仲禾欣赏着沿途的艺术油画。
脚步不停的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了一座浴仙池,雾气昭昭,水汽缭缭,周围高挑幔帐,透过纱雾,隐约窥得里面跪侍着几个娇弱玉女。
两个技术员把王仲禾停在近处,道了声告退,就低着头,快步离去复命。
二人刚走,就见云雾中袅袅婷婷走出两排薄纱漫玉体,三点私处隐隐现的绝代娇人。
行礼弯身,道了万福,一众女子就款移莲步来到王仲禾跟前,这个托腿,那个架腰,看见王仲禾一身烂肉,断肢残体也不惊讶,轻手轻脚的将王仲禾放入水漂花舟的兰汤中。
水汽氤氲酥玉胸,纱帐香飘兰麝。雪莹玉体透房帏,柔荑捏拿轻搓。玉腕揽水荡花漾,勾魂惹火嘲人。
浴汤内良药百味,浸泡三时,王仲禾伤好结痂,出了池子来,众女飘飘给他穿了一身舒适贵服,重推来一辆金制轮椅。
到了外门,被两个春色惊艳,明媚动人的侍女接过,弯弯绕绕,穿厅过殿,直到了膳厅。
雕梁画栋,极尽奢华。香焚宝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帘开合浦之明珠。
见水晶盘内,高堆火枣交梨;碧玉杯中,满泛琼浆玉液。烹龙肝,炮凤腑,果然下箸了万钱;黑熊掌,紫驼蹄,酒后献来香满座。碾破凤团,白玉瓯中分白浪;斟来琼液,紫金壶内喷清香。
竭力从案桌上移开目光,王仲禾抬首举目就看见到一个锦衣华服,面润如玉的青年,正一脸温煦笑意的望着他。
“近来事忙,怠慢了先生,望先生勿要见怪。”青年唇红齿白,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作揖问礼进退有度。
王仲禾听言辞,看举止,不禁面露惊容。这青年居然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作揖自然得体,不生疏,一看就是精通之人。
青年很谦逊,对王仲禾的表情恍若未见,伸手示意请王仲禾用餐:“先生来到三千界也有十余年的光景,想来对家乡菜甚是想念。不才,我这里有人会些乡味烹饪,就宴请先生陪个不是。”
王仲禾冷冷一笑,开口仍说三千界语言:“你费劲心思,动用那么大的阵仗把我抓到这里来,现在轻描淡写一个请字,未免太有些冠冕堂皇了吧?”
青年伸手夹了一块肥肉,油腻腻的吃着:“我这人面子薄,平生就怕人驳了面子。寻思先生大驾,甚是难请,于是动了点手段,手下人没个分寸,粗鲁了些。”
王仲禾只是含笑看着他。
许是被王仲禾盯的不自在,青年放下筷子,也呆呆的看着王仲禾,目光清澈如湖水,像个邻家小弟弟,对视良久,青年猛的一拍脑门:“哎呀呀,你看看我这记性,家里废物奴才不知先生是贵客,莽撞了先生,多有得罪,望多包涵。先生如今身子不适,自是吃些稀汤最好,养养身子,胃口好了,大鱼大肉有甚吃不得。”
说着,亲自动手给王仲禾舀了一碗碧粳米粥,可能是青年也没给人舀过粥,握汤匙的手没稳住,瓷碗里满满登登,都快溢出来了。
看这青年,吐了吐舌头,尴尬的挠挠头,深吸口气,半蹲下小心的扣出碗檐,脑袋不敢晃,肩膀不敢动,慢慢起身,生怕羹汤撒出一点,烫了手。
大气不敢出,挪步似蜗牛,两只眼睛紧盯汤碗,偶尔偷瞄瞧路,短短的几米路,走了五分钟,待青年一脸兴奋的把碗放到王仲禾跟前后,长出口气,欣喜满面,甚是自得。
实不知在他靠近王仲禾的时候,外面有人已经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恐怕王仲禾暴起伤人。
要说王仲禾在青年靠近他的时候,有没有杀人的意念?那肯定是有的。但王仲禾不会出手,若是杀了这青年,他是必死无疑。王仲禾是不会干这种白痴事的。
至于劫持人质,王仲禾更是懒得做,他不清楚这青年的底细身手,以他这半残身子,就算劫持了,也跑不远。
青年回到座位,也不再和王仲禾说话,左一筷子,右一筷子的自顾吃了起来。
王仲禾喝了汤,左手捉着筷子,尽自己所能,把胳膊能够到的食物都往嘴里放,也不管下咽的时候食管疼痛。
菜过五味,王仲禾解了馋,肚子鼓涨,摸了摸嘴,打着嗝看向了早就吃毕的青年。
青年道:“先生可还满意?”
王仲禾点点头。
“满意就好。”青年起身走到王仲禾身后,推着轮椅就走出了膳厅。
“吃饭前不爱谈事,坏人胃口。此时饭饱,我就不绕圈子,和先生畅谈一番。”
走到长廊上,能看见廊外的翠竹秀立,景色宜人。王仲禾坐轮椅在廊中,青年随意的坐在柱子墩上率先开口:“说起来,咱们之间也有缘分。”
“哦?什么缘分?”王仲禾奇怪。
青年嘻嘻一笑:“怕先生已经忘记。那是前些年的事,网上出了一款新游戏,你我曾在一起玩耍过几局,后来还加了好友。你叫‘骑猪打老虎’,我叫‘狮子不怕狗’,还记得吗?”
王仲禾眉尖微挑:“这个谁能记得清。”
青年惆怅道:“谁说不是,若不是调查了先生的身份芯片,谁能想到你我有过这等渊源。”
“查我身份芯片?”王仲禾皱眉,不明白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