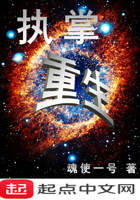“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我问道。“我叫阿伯特·霍金斯。”他说。“我回来时还能在这儿找到您吗?”我问。“能够的,”他说,“我就在这个车站工作,您只要提到我的名字就行。”“您若是找到了那只戒指,”我说,“那就麻烦您保管好,等我回来取,别忘了告诉我一声。”乘客们都在急匆匆地上车,我也回到车上,车门关上了,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您记住电话号码了吗?”我问他。
“记住了。”阿伯特·霍金斯说,火车开动了。“非常感谢您,霍金斯先生。”我冲他大声叫唤。
火车开出站台,我坐下来想自己的心事。把戒指丢落在那个大车站的什么地方使我伤心透了。
“我不会再看到自己的戒指了,”我暗自寻思,“假设霍金斯找到了它,他会拿去卖个好价钱,或者就在此刻,另外一个人已经捡到它了,他将据为己有。反正我不可能再听到任何关于戒指的音信了。”
我越想越伤心,真想立刻下车回到那个车站找我的戒指,但是火车越开越快——远离了我的戒指。
大约一个钟头之后,火车到站了,我的朋友用小汽车把我接走,在路上我把这个伤心事讲给她听,她深感惋惜。
到了朋友家,她停放小汽车去了,我脱掉外套,放好提包,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对方说:“我是利物浦大街火车站的阿伯特·霍金斯。”
“啊!霍金斯先生,”我说道,“您找到我的戒指啦?”“是的,”他说,“事情很顺利,我已经找到它啦,您是在车站商店里把它弄丢的。一个人捡到了它,交给了商店的女售货员,当我问到她时,她拿给我看,我肯定是您的戒指。”
“啊,我太高兴了!多谢您了,回头我到您那儿去拿。”
“干吗要等那么长时间?”霍金斯先生说,“我可以把它寄给您,不过我不知您的地址。”
“但那样的话又会给您添麻烦。”我说。“一点也不麻烦,”霍金斯先生说,“我很高兴这样做。”
我便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了他。“我这就给您寄去。”他说完挂上了电话。两天后,我接到一封信,里面用纸包着我的戒指,纸上写有一句话:“非常高兴能帮助您!”后来我送给阿伯特·霍金斯一点钱和一封感谢信,但我无法向第一个捡到戒指的那个人致谢,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他们没有财富,但他们有助人为乐的美德,这比财富好得多,他们是善良的人。
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里奥家是纽约城里唯一没有汽车的人家。
他们每天上街买东西,总是坐一辆简陋的两轮柳条车,拉车的是一匹老马。马里奥的父亲是个职员,整天在证券交易所那如同“囚笼”般的办公室里工作。假如父亲不把一半工资用于医药费以及给比他们还穷的亲戚,那么,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事实上,他们是很穷的。
他母亲常安慰家里人说:“一个人有骨气,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在生活中怀着一线希望,也就等于有了一大笔精神财富。”
马里奥挖苦地反驳说:“反正你买不起一辆汽车。”而母亲在生活中处处力求简朴,在母亲悉心料理下,家里的生活还是有趣的。
一件意外的事情把马里奥那实实在在的羞愧之情一扫而光,激动人心的时刻突然来到了。
几星期后,一辆崭新的别克牌汽车在大街上那家最大的百货商店橱窗里展出了。这辆车将在市集节日之夜以抽彩的方式馈赠得奖者。马里奥呆在人群外面的黑影里,观看开奖前放的焰火,等候着这一高潮的到来。用旗帜装饰一新的别克牌汽车停放在一个专门的台子上,在十几只聚光灯的照耀下,光彩夺目。人们鸦雀无声地等待市长揭开装有获奖彩票的玻璃瓶。
不管马里奥有多么想入非非,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幸运女神会厚待他们这个在城里唯一没有汽车的人家。但是,扩音器里确实在大声叫着他父亲的名字!那时,马里奥从人群中慢慢地往里挤。市长把汽车的钥匙交给他父亲,他父亲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把汽车缓缓地开了出来。
回到家里,马里奥正想向父亲道贺。不料,父亲的态度使他大为吃惊,他咆哮道:“走开,不要呆在这儿!让我清静清静!”马里奥在起居室里见到母亲,她看到他悲伤的样子说:“不要烦恼,你父亲正在思考一个道德问题。我们等待他找到适当的答案。”
“难道我们中彩得到汽车是不道德的吗?”马里奥迷惑不解地问。
“汽车根本不属于我们,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母亲说。
母亲把事情一五一十跟马里奥讲了,当初父亲对吉米说,他买彩券的时候可以给吉米代买一张,吉米同意了。过后可能再也没有想到过这事。父亲就用自己的钱以自己的名义买了两张彩票,并在一张上——正是中奖的那一张——做了一个轻轻的记号,表示那是吉米的。对马里奥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吉米是一个富翁,拥有几部汽车,还有两个雇用的司机。对他来说,增加一辆汽车简直等于普通人的马具里多一个马嚼子。马里奥激动地说:“汽车应该归我爸爸。”
母亲平静地说:“你爸爸知道该怎么做是正当的。”第二天下午,吉米的一个司机来到他们这儿,把别克牌汽车开走了。
蓝色的连衣裙
1909年的春天来到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城,可是,它没能给盖特街带来新面貌。临近的那些漂亮街道上的住户们都已忙开了:拾掇闲了一冬的小园子,粉刷、油漆房屋,为夏天准备好剪草机……盖特街却仍是老样子——又脏又乱。
盖特街是条短街,但走过这条街的人都嫌它太长了。当然,住在这儿的人都没多少钱,穷人的要求是不高的。他们有时能找到点儿活干,有时为找工作而奔波,他们的屋子多年没有油漆粉刷了,院子里连自来水也没有,盖特街的住户只好到街角的水栓那儿去提水。
街上的景象当然好不了——没有人行道,没有路灯,街道一端的铁路线给这儿增添了更多的嘈杂声和尘土。
春天来了,别的街上去学校读书的小姑娘们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裳。但是,这个盖特街来的小姑娘还是穿着那件她已穿了一冬的脏罩衫,也许,她只有这一身衣服。
她的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多好的小姑娘呵!她学习起来可真用功,她懂礼貌,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可惜,她的脸从来也不洗,还有一头蓬乱的头发。
一天,老师对这个小姑娘说:“明天你来上学以前,请你为我洗洗你自己的脸,好吗?”老师看得出,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第二天,漂亮的小姑娘洗干净了脸,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放学时,老师又对她说:“好孩子,让妈妈帮你洗洗衣服吧!”
可是,小姑娘还是每天穿着那身脏衣服来上学。“她的妈妈可能不喜欢她?”老师想。于是老师去买了一件美丽的蓝色连衣裙,送给了小姑娘,孩子接过这礼物,又惊又喜,她飞快地向家里跑去。
第二天,小姑娘穿着那件美丽的裙子来上学了,她又干净又整齐,兴高采烈地对老师说:“我妈妈看我穿上这身新衣服,嘴巴都张大了。爸爸出门去找工作了,可是没关系,吃晚饭时他会看到我的。”
爸爸看到穿着新衣服的女儿时,他不禁暗暗地说:“真没想到,我的女儿竟这么漂亮!”当全家人坐下吃饭时,他又吃了一惊:桌子上铺了桌布!家里的饭桌上从来没用过桌布。他不禁问:“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整洁起来了,”他的妻子说,“又脏又乱的屋子对我们这个干净漂亮的小宝贝来说,可不是个好事。”
晚饭后,妈妈就开始擦洗地板,爸爸站在一旁看了会儿,就不声不响地拿起工具,到后院去修理院子的栅栏去了。第二天晚上,全家人开始在院子里开辟一个小花园。
第二个星期,邻居开始关心地看着小姑娘家的活动,接着,他也开始油漆自己那个多年未曾动过的房屋了。这两家人的活动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于是,有人向政府、教会和学校呼吁:应该帮助这条没有人行道、没有自来水的街上的居民,他们的境况这样糟,可是他们仍然在尽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
几个月后,盖特街简直变得让人认不出了。修了人行道,安上了路灯,院里接上了自来水。小姑娘穿上她的新衣服的六个月后,盖特街已经是住着友好的、可敬的人们的整洁街道了。
得知盖特街变化的人们管这叫“盖特街的整洁化”,这个奇迹愈传愈远。
其他城市的人们听到这个故事,也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整洁化”运动,到1913年,有上千个美国城镇组织了修理、油漆房屋的活动。
当一个老师送给一个小女孩一件蓝色的新衣裳时,谁能料到会引起什么奇迹呢!
非同寻常的出租车
我刚坐进这辆出租车,就感觉到了它的非同寻常:车厢地板上铺着山羊毛地毯,地毯边上撒着鲜艳的深秋红叶,玻璃隔板上镶着梵高和高更名画的小幅复制品,车窗晶亮透明,一尘不染。
我对司机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漂亮的出租车。”
“我喜欢听到乘客这样赞美我的车。”司机笑着说。“装饰得这么漂亮,这是你自己的车吗?”我问。“不,这不是我的车,这是公司的。”他说,“多年以前,我还在出租车公司当清洁工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主意了。那时候,每天晚上车子回到公司停车场时,都龌龊得像个垃圾桶,地板上到处都是烟屁股和火柴梗,座位上或车门把手上总粘有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像花生酱啦、口香糖渣啦什么的,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一辆值得乘客们去自觉保持清洁的出租车,他们或许就会更多地为别人着想了。我相信,人人都懂得珍惜美的事物。”
“后来,我领到了出租车营业执照,便马上用上了这个主意。我把公司给我驾驶的出租车收拾得干干净净,又自己掏钱去买来了一张漂亮的薄地毯和一些鲜花。每个乘客下车后,我都要仔细地察看一下车子的卫生状况,因为我一定要让后来的每一个乘客都感觉到它的整洁。所以,我的车每天回到停车场后,都依然十分干净。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我的老板就把这辆车交给了我承包,于是我又买来了那些名画复制品。”
“我从15年前就开始驾驶出租车了,我的乘客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没有人在我的车厢地板上乱扔烟头,也没有谁会在我的车上乱抹花生酱或口香糖渣。先生,正像我听说的那样,每一个人都懂得珍惜美,也懂得欣赏美。假如我们的城市多种一些花草树木,将所有的楼房屋宇都打扮得干干净净,我敢和你打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不会在大街上乱扔垃圾的。”
我心想,这位司机正在述说着一条平凡的真理,但它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真理。人天生就爱美,大部分人不必接受任何教诲就懂得美是来之不易的。因此,当他们见到美好的事物时,他们的心灵就会立即作出相应的感应;而如果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本身就是美的一部分,那么,他们不仅不会去糟蹋美,而且会想方设法去爱护美,进而还会为美锦上添花。
弯腰的哲学
孟买佛学院是印度最著名的佛学院之一。这所佛学院之所以著名,除了它建筑历史的久远和它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佛学院所没有的。
这是极其微小的细节,但是,所有到过这里的人再出来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正是这个细节让他们受益无穷。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细节:孟买佛学院在它的正门一侧又开了个小门,这个小门只有一米五高,四十厘米宽,一个成年人要想过去必须弯腰侧身,不然就只能碰壁了。
所有刚刚进入佛学院的人,都十分纳闷:那么大的佛学院,有着壮观巍峨的大门可以堂皇地出入,还开这个小门干什么?
其实,这正是孟买佛学院给它的学生上的人生第一堂课。所有新来的人,教师都会引导他到这个小门旁,让他进出一次。
很显然,所有的人都是弯腰侧身进出的,尽管暂时有失礼仪和风度,却达到了目的。教师说,大门当然出入方便,而且能够让一个人很体面很有风度地出入。但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出入的地方并不都是有着壮观的大门的,或者,有大门也不是可以随便出入的。这时只有学会了弯腰和侧身的人,只有暂时放下身价和体面的人才能够出入。否则,你就只能被挡在院墙之外了。
佛学院的教师告诉他们的学生,佛家的哲学就在这个小门里,人生的哲学也在这个小门里。人生的路上,尤其是通向成功的门上,所有的门都是需要弯腰侧身才可以进去的。
罗丹的启示
我那时大约25岁,在巴黎研究与写作。许多人都称赞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些我自己也喜欢。但是,我心里深深感到我还能写得更好,虽然我不能断定那症结的所在。
这时,一个伟大的人给了我一个伟大的启示。那件仿佛微乎其微的事,竟成为我一生的关键。
有一晚,在比利时名作家魏尔哈伦家里,一位年长的画家慨叹着雕塑美术的衰落。我年轻而好饶舌,热烈地反对他的意见。“就在这城里,”我说,“不是住着一个与米开朗基罗媲美的雕刻家吗?罗丹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同他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永垂不朽吗?”
当我倾吐完了的时候,魏尔哈伦高兴地指指我的背。“我明天要去看罗丹,”他说,“来,一块儿去吧。凡像你这样赞美他的人都该去会他。”
我充满了喜悦,但第二天魏尔哈伦把我带到雕刻家那里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老朋友畅谈之际,我觉得我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