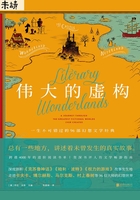点亮自己的“心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多云黯然的午后。英国小说家米切尔·罗伯特照例来到郊外的一个墓地,拜祭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友。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去时,竟意外地看到文友的墓碑旁有一块新立的墓碑,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支小蜡烛失去光辉!炭火般的语言,立刻温暖了罗伯特阴郁的心,令他既激动又振奋。罗伯特迅速地从衣兜里掏出钢笔,记下了这句话。他以为这句话一定是引用了哪位名家的“名言”。
为了尽早查到这句话的出处,他匆匆地赶回公寓,认真地逐册逐页翻阅书籍。可是,找了很久,也未找到这句“名言”的来源。
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又重回到墓地。从墓地管理员那里得知:长眠于那个墓碑之下的是一名年仅10岁的少年,前几天,德军空袭伦敦时,不幸被炸弹炸死,少年的母亲怀着悲痛,为自己的儿子做了一个墓,并立下了那块墓碑。
这个感人的故事令罗伯特久久不能释怀,一股澎湃的激情促使罗伯特提笔疾书。很快,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从他的笔尖流淌出来。
几天后,文章发表了。故事转瞬便流传开来,如希望的火种,鼓舞着人们为胜利而执著前行的脚步。
许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还在读大学的布莱克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并从中读出了那句话的隽永与深刻。布莱克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几家企业的高薪聘请,毅然决定随一个科技普及小组去非洲扶贫。
“到那里,万一你觉得天气炎热受不了,怎么办?”“非洲那里闹传染病,怎么办?”“那里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面对亲人们那异口同声的劝说,布莱克很坚定地回答:“如果黑暗笼罩了我,我决不害怕,我会点亮自己的蜡烛!”
一周后,布莱克怀揣着希望去了非洲。在那里,经过布莱克和同伴们的不懈努力,用他们那点点烛光,终于照亮了一片天空,并因此被联合国授予“扶贫大使”的称号。
蜡烛虽纤弱,却有熠熠的光芒围绕着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这样的蜡烛。当一个人在气馁、失败,甚至感到有些绝望时,不妨激活自己,点亮心烛。黑暗消失了,留下来的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以笑声面对残酷的命运
1954年,当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上台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却谦虚地说道:“得此奖项的人应该是那位美丽的丹麦女作家——盖伦·璧森。”
海明威所说的这位丹麦著名女作家,就是那位奥斯卡金像奖电影《走出非洲》里的女主人公。《走出非洲》这部电影的结尾,打上一行小小的英文字:盖伦·璧森返回丹麦后成了一位女作家。
盖伦·璧森(1885—1962)从非洲返回丹麦后,不但成为一位享誉欧美文坛的女作家,而且在她去世40多年后的今天,她和比她早出世80年的安徒生并列为丹麦的“文学国宝”。她的作品是国际学者专研的科目之一,几乎每一两年便有英文及丹麦文的版本出现。她的故居也成了“盖伦·璧森博物馆”,前来瞻仰她故居的游客大部分是她的文学崇拜者。
盖伦·璧森离开非洲的那一年,她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女人,有的只是一连串的厄运:她苦心经营了18年的咖啡园因长年亏本被拍卖了;她深爱的英国情人因飞机失事而毙命;她的婚姻早已破裂,前夫再婚;最后,连健康也被剥夺了,多年前从丈夫那里感染到的梅毒发作,医生告诉她,病情已经到了药物不能控制的阶段。
回到丹麦时,她可说是身无分文,除了少女时代在艺术学院学过画画以外,无一技之长。她只好回到母亲那里,仰赖母亲,她的心情简直是陷落到绝望的谷底。在痛苦与低落的状况下,她鼓足了勇气,开始在老家伏案笔耕。一个黑暗的冬天过去了,她的第一本作品终于脱稿,是七篇诡异小说。
她的天分并没有立刻受到丹麦文学界的欣赏和认可。她的第一本作品在丹麦饱尝闭门羹,有的人甚至认为,她故事中所描写的鬼魂,简直是颓废至极。
盖伦·璧森在丹麦找不到出版商,便亲自把作品带到英国去,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英国出版商很礼貌地回绝她:“男爵夫人(盖伦·璧森的前夫是瑞典男爵,离婚后她仍然有男爵夫人的头衔),我们英国现在有那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何要出版你的作品呢?”
盖伦·璧森颓丧地回到丹麦。她的哥哥蓦然想起,曾经在一次旅途中认识了一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美国女作家,毅然把妹妹的作品寄给那位美国女作家。事有凑巧,那位女作家的邻居正好是个出版商,出版商读完了盖伦·璧森的作品后,大为赞赏地说,这么好的作品不出版实在是太可惜了。她愿意为文学冒险。1943年,盖伦·璧森的第一本作品《七个哥德式的故事》终于在纽约出版,一鸣惊人,不但好评如潮,还被《这月书俱乐部》选为该月之书。当消息传到丹麦时,丹麦记者才四处打听,这位在美国名噪一时的丹麦作家到底是谁?
盖伦·璧森在她行将50岁那年,从绝望的黑暗深渊,一跃而成为文学天际一颗闪亮的星星。此后,盖伦·璧森的每一部新作都成为名著,原文都是用英文书写,先在纽约出版,然后再重渡北大西洋回到丹麦,以丹麦文出版。盖伦·璧森在成名后说:“在命运最低潮的时刻,她和魔鬼做了个交易。”她效仿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把灵魂交给了魔鬼,作为承诺,让她把一生的经历都变成了故事。
盖伦·璧森把她一生各种经历先经过一番过滤、浓缩,最后才把精华部分放进她的故事里。她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因为她认为,唯有这样她才能得到最大的文学创作自由。熟悉盖伦·璧森的读者,不难在其作品中看到她的影子。
盖伦·璧森写作初期以Isak Dinesen 为笔名,成名后才用回本名。Isak,犹太文是“大笑者”的意思。她之所以采用这个笔名,也许是在暗示世人,以笑声面对残酷的命运。
盖伦·璧森成为北大西洋两岸的文学界宠儿后,丹麦时下的年轻作家皆拜倒在她的文学裙下,把她当女王般看待。74岁那年,她第一次出访纽约,纽约文艺界知名人士,包括赛珍珠和阿瑟·米勒皆慕名而来。但盖伦·璧森对她的文学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的梅毒给她带来极大的肉体痛苦,当梅毒侵入她的脊柱时,她常痛得在地上打滚。晚年时,她变得极其消瘦、衰弱,坐立行皆痛苦不堪。
盖伦·璧森死时77岁,死亡证书上写的死因是:消瘦。正如她晚年所说的两句话:“当我的肉体变得轻如鸿毛时,命运可以把我当做最轻微的东西抛弃掉。”
一个女孩和一棵树
悲剧中也能发现希望,每一个生命都生机盎然一一无论她多么短暂。
大约20年前,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隆冬。那会儿我们全家正沉浸在幸福之中。
在我们的三个女儿中,就数幼女莱莎·玛丽灵秀调皮,无拘无束。她一天到晚蹦来跳去,一刻也不安宁,宛如远方潺潺奔流的小溪。
1973年,一个料峭的春日,莱莎从幼儿园拖回家来一棵小树苗。“每个人发了一棵小树苗。”她说,“它将来一定会长得很茁壮。”
我仔细一看,那棵小树苗其实只不过是根两英尺长的毫无生机的枝条而已。根部的土疙瘩已被拖拉掉,根须看上去都快干枯了。可莱莎硬是央求父亲把它栽到了后院。“我给它起名叫安琪拉。”莱莎郑重其事地宣布说,“因为所有的安琪儿都会来帮助它成长的。”
此后,莱莎每天都要给安琪拉浇水。同时,还要拍拍它,虔诚地说上几句悄悄话,然后低下头默默在祈祷。莱莎坚信,终有一天,她会让这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夏日的一个清晨,莱莎风风火火地跑进厨房:“妈妈,小树长出了两片叶子!”她大喊大叫。“两片叶子!”果然,那棵叫安琪拉的小树已经长出了嫩嫩的绿芽。冬日来临,风雪肆虐。莱莎经常跑出去,抚慰安琪拉好好睡觉,等待春天时醒来。转年夏天,安琪拉伸枝吐叶,生机盎然。我们全家特意为安琪拉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大家一起分享了莱莎的快乐——她站在安琪拉身旁,一只手抚着它,笑嘻嘻地对我们做了个鬼脸儿……幼女的这一娇态,是我心海上的一束阳光,灿烂、明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1974年8月,莱莎七岁生日前两天。将近中午,一个外科医生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我和丈夫正在那儿等着。从凌晨起,那位医生就在为莱莎做手术。“不必用显微镜检查,就可以告诉你们,这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恶性肿瘤。”他沉郁地说。我们一下子变得呆若木鸡。
虽然我们从未给她任何口头暗示——她快要死了,但我相信莱莎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她的天真活泼仍一如既往,她从未流露出一丝恐惧。
两周以后,8月17日一个炙热的下午,玩具狗诺曼伴着她,我们的小女儿陷入了一片宁静安详的昏迷之中。她的呼吸渐缓渐歇,最后好像完全停止了。过了好一会儿,哈登医生又听了一次心跳。最后,我打破了沉默:“都结束了?”
“是的,都结束了。”他轻轻地说。葬礼结束后,我们回了家,回到寂无声息的屋里。
楼上,诺曼孤零零地蹲在莱莎的床头,无所依傍;窗外,骄阳下的安琪拉孑然伫立,形影相吊;我们的内心,都充满了难以遏制的无尽的悲伤和失落……在那些黯然神伤的日子里,我们与莱莎的唯一联系就是那棵树——安琪拉,它已是七尺高了。家中的一切,无形中也都让我们不时想到莱莎的离去。我们打定主意,马上搬家。全家郑重保证,来年春天一定把安琪拉移过去。
第二年四月的一个清晨,我们返回旧居来移安琪拉。此时此刻,我们深切地感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责任和义务——要像莱莎也会做的那样,培育好安琪拉。我们把它栽在了新居的后院。
光阴如梭,一切如旧。安琪拉越来越枝繁叶茂,茁壮挺拔。
1990年底,莱莎要是活着,也该23岁了。丈夫以本应该用来让她受教育的钱,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专门用来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现在,我很幸福。经过长途跋涉,我终于走出了阴郁的谷底。善良的同情心贮满了我的心房。我悟出了一点儿道理:悲剧中也能发现希望,每一个生命都生机盎然,无论她多么短暂。
莱莎留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是安琪拉。现在,它足有30尺高了,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它挺立在那里,是对一个孩子的信念的雄辩有力的证明。莱莎从未怀疑,一根毫无生机的枝条会长成参天大树。本来,我们理应是她的老师,实际上正是她给了我们教益——关于信念、关于爱心和所有上帝的安琪儿们的巨大力量。
犹豫不决的命运之神
对于那些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事情,我们知之甚少。某些这类事情——如果可以回忆得起来的话——就在我们身边而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来去无踪,没有留下痕迹。假如预先知道我们的命运变化的各种可能性,那么生活就会充满过多的希望和恐惧,充满过多的惊异和沮丧,使我们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下面,请听关于克鲁斯·斯旺的一个故事。
我们发现克鲁斯,是他20岁那年在从他的故乡通往波士顿的大道上。在此之前我们和他并无关系。他的叔父在波士顿,是个商人,为他在自己的店里找了工作。这是夏季里的一天,他迈着双腿,从早晨起走到了正午。他又累又热,决定找个阴凉的地方坐下,等候驿车。没多久,他便来到一处,这地方泉水涌流,树丛成阴。他跪下去,贪婪地喝着沁人心脾的清泉,然后在柔软的土地上躺下来,头下枕着他的小包裹。
他在树阴下睡觉,行人们却在大路上匆匆走过,步行的,骑马的,或者乘坐各式各样的车辆的都有。有的既不朝左边看,也不朝右边看;有的在经过克鲁斯睡觉的地方时,朝这边匆匆一瞥。没有旁人时,一位中年寡妇停了下来,她仔细地瞧了瞧克鲁斯,自言自语地说,小伙子睡觉的模样真逗人。一位极力反对酗酒的牧师,看到克鲁斯后就认为他是喝多了酒,下个礼拜天在教堂里布道时,他将举出可怜的克鲁斯作为酗酒的可怕的一例。
克鲁斯睡着后不久,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停在了他睡觉的前方。有一匹马的脚伤了,车夫想让马歇会儿。车里走出一位富商和他的妻子,打算利用这个时间到树下去休息。他们看到了泉水和睡在旁边的克鲁斯。他们轻轻地走着,尽量不让弄出的响声把他吵醒。“睡得真香,”老绅士说,“他的呼吸多平静多轻松。我要是能像他这样睡觉的话,那就太有福气啦。不吃安眠药能睡得这么好,说明他身强体健而又无忧无虑。”“此外还意味着青春,”他的妻子说,“我们这些上了年岁的人再也不能像他这样睡得香甜。”
老夫妇对这位安静地睡着了的年轻人越来越感兴趣。“他似乎有点像我,”女人对她的丈夫说,“他很像我们自己亲爱的儿子。我们叫醒他好吗?”“为了什么呢?”丈夫说,“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善良的脸,”妻子语调文静地回答,“这样天真无邪的睡眠!”
谈话在继续,克鲁斯一动也没动,面部所有的表情都表明他不知道这两个人正以极大的兴致在观察着他。然而,幸运之神正站在他跟前。这老者和他的妻子都很富有,他们的儿子最近死去,对于他们的全部钱财,家里还没有人可以交付。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有时会做出比唤醒一位年轻人更奇特的事情来,认他做自己的儿子,然后让他成为他们财富的继承人。“我们叫醒他吧?”女士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