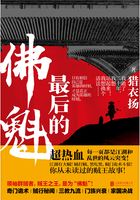这里所说的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只不过是一个短发的18岁女孩,她身穿新的茶色制服,细腰被皮带扎住了。她教给谢廖扎不少东西,她还打算与他一块开展小组工作。分手时,她给他一包书籍、宣传品,同时还特别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共青团的纲领和章程。
一直到了黄昏,他们才返回革委会。瓦利娅还在花园里等他。见到谢廖扎,她不由自主地就责怪起来:
“你看你也叫人,一点也不理睬家里的一切,为了你,母亲眼都快哭瞎了,父亲也气得了不得,你再这样下去,可怎么是好!”
“瓦利娅,不要这样说。我现在根本没时间回家,今天我也得走。我正好想和你谈谈,走,到我屋里去吧。”
瓦利娅简直不认识弟弟了,突然他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精神抖擞,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叫姐姐在椅子上坐下后,谢廖扎张口就说了主题:
“姐,我想要你加入共青团,这个你知不知道,就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我是团的书记。你如果不相信?呶,拿去看看!”
瓦利娅看了他的证件,露出羞愧不好意思的神情,她看看弟弟,说:
“在那里,我又能做什么事情呢?”谢廖扎把双手一摊:“你难道还怕无事可干,闲着吗?不会的,亲爱的姐姐,我都没时间休息、回家了。应当大力进行鼓动。伊格纳季耶娃说,我们现在应该把所有青年人全聚集到剧院,给他们讲一讲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她要我义不容辞地去讲话。我想,这可不行,你知道的,我不会说话的,我可能会讲得乱七八糟。呶,怎么样,你说说你究竟想不想参加?”
“我不知道。你要知道,如果母亲知道我也入了团,非气疯不可。”
“瓦利娅,你先不要说妈妈,”谢廖扎反驳道:“她根本弄不清这些事,她只想把孩子们放在自己眼前,她不会反对苏维埃政府的,而且我相信,她会同情苏维埃。不同的是,她希望别人在前线作战,而不想是她的子女。”
“难道说她做得合乎情理吗?你还记得朱赫来曾告诉过我们什么吗?你瞧保尔,他就不管他的母亲有什么样的看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在世上好好生活的权利。怎么样,瓦利娅,你难道会不愿意?如果你也入团那该多好!你做女同志的工作,我就做男同志的工作。克里姆卡,那个红毛鬼,今天我就要让他动起来。你到底想通了没有,瓦利娅,和我们是不是一块去工作?我这儿有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小册子交给了瓦利娅。瓦利娅不错眼珠地盯着兄弟,小声地问:
“假若彼得留拉的人重新又再回来了,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谢廖扎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我嘛,理所当然和大家一起撤退。不过你又该如何安排呢?母亲确实会非常伤心的。”他沉默了。“谢廖扎,不要让母亲知道这件事。别的人也不要知道我的名字在里面。但我可帮你干任何事情。还是这样办好一些。”
“瓦利娅,我很赞同。”伊格纳季耶娃来到房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让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的姐姐瓦利娅,刚才我俩说了入团的情况,姐是很好的人选,而且她也赞同,只是母亲那不好办,你看能否让她秘密入团?万一我们一定要撤走,我一定会拿起枪就跑,但她可以永远不能离开妈妈的。”
伊格纳季耶娃斜依着桌子仔细地听他说完这件事情。
“好,这样做也许会更好的,我赞同。”乱哄哄的年轻人挤满了剧院,他们都是看到四处张贴在城里的关于召开集会的告示而到这儿来的。糖厂工人管弦乐队演奏着乐曲,现在剧场里的人大多都是中小学生。
他们来到剧院其实并不是为了开会,更多人是为了看戏。
帷幕终于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拉津同志站在台上。拉津个头儿不高,瘦瘦的,长着尖尖的小鼻子。他的出现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抱着极大的兴趣听他演说。他分析到全国的斗争形势,号召青年人全聚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像一个真正的演讲者,在他的讲话中多次运用了诸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等陌生的文字,听众并不知道是什么。演讲结束时,全场人用极大的充满热情的掌声欢送。他让谢廖扎接着讲话,自己先行走了。
谢廖扎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应验了——他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说什么?该说哪些事情呢?他想东想西,就是不知如何开头,心里那个慌乱呀!”
伊格纳季耶娃及时帮助了他——她从讲台后面提示了他说:
“就先讲一讲组织支部的事情。”谢廖扎马上说起了实际工作。“同志们,你们刚才也都听了演讲内容,现在我们想要建立支部。有谁愿意参加、支持?”会场上一片寂静。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跑上前来为他更多地做群众工作,她开始向听众讲解一些莫斯科青年组织的情况。谢廖扎很是尴尬地站在一边。
看到到会者对组织支部的无动于衷极不热心的态度令谢廖扎感到很生气,他不时愤愤地瞪视着大厅里的听众,然而听众并没有仔细地听丽达讲话,扎利瓦诺夫以轻视的眼光看着丽达,对丽莎·苏哈里科交头接耳;高年级女生坐在前排,鼻子上扑着****,狡猾的眼睛东张西望,窃窃私语地议论着。几个红军战士坐在靠近前台入口的角落里,谢廖扎认识的年轻的机枪手当然也在其中。他坐在舞台前沿的栏杆上,着急地转着身子,憎恨地注视着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丽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这两人正旁若无人般地与那些无聊的男生打情骂俏。
丽达也觉得自己的讲话没有人听进心里去,所以匆忙结束了讲话,让伊格纳季耶娃讲话。伊格纳季耶娃说话语气平和、严肃而又低沉,很快地听众们终于安静下来。
“青年同志们,”她说:“刚才所讲的这种事情,我认为你们每个人会好好斟酌的。我也知道,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不少同志不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而是作为积极的参与支持者投身革命。革命的大门对你们敞开着,是否来加入,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希望你们讲一讲自己的观点、想法。有谁想到上面来说一说。”
大厅里没有一点声音。突然,后排中有人喊道:“我想去讲几句可好。”长得像头小熊,眼睛有点斜视的米沙·列夫丘科夫来到了台前:“如果说是这种事情,我们理所当然要给予支持,我赞成。谢廖扎了解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扎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很快跑到台前,说:“同志们!看,我就说吧。米沙是自己人,他的父亲是扳道工,不幸被火车压死了,为此米沙才失了学。别看他书读的不多,然而却很明事理的。”
大厅里热闹了起来,而且还间杂着起哄声。中学生奥库绍夫要求讲话,他是药铺老板的儿子,头上卷着蓬发。他整整中学生制服,说道:
“对不起,同志们,我不知道究竟要我们做什么。叫我们搞政治!那我们又如何上学呢?我们总得读完中学吧。如果说是搞一次什么体育协会啦、俱乐部啦,大家完全可以一起玩、看看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搞政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不起,我想,没有人愿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厅内爆发出一阵笑声。奥库绍夫跳下讲台,坐了下来。这时,年轻的机枪手不知何时站在讲台上了。他极为生气地把制帽往额头上推了推,愤怒的目光瞪视着,然后使劲喊道:
“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东西,这很可笑吗?”他的眼睛好像气得要冒火了。他深深吸了口气,气得浑身哆嗦,接着说道:“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是个孤儿,从小便四处流浪,靠讨饭过日子,晚上就团缩在人家的墙根边,整天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没有固定的住处,这是你们这群娇小姐、公子哥所不知道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红军收留了我,把我当作他们的儿子,给我饭让我吃饱,而且还教给了我很多文化知识,让我学会了怎样去做人,怎样的一生才是有意义的。他们把我培养成一名布尔什维克,我永远信仰它。现在我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为了我们自己,为了穷人,为工人政权而斗争。可你们呢?在这儿肆无忌惮地大笑,却不知道还有200个牺牲了的同志永远埋在了城郊,他们永远地走了……”扎尔基的嗓音就像那紧绷的琴弦,清脆悦耳极了。“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生活和事业,毫无顾忌地献出了生命……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有人流血牺牲,前线也是这样,就这般时候,你们却在此逍遥自在。”他猛然问又转过身来对主席团的成员说道:“同志们,你们难道不企盼他们,”他用手指指台下,“就是这样的一帮人,难道他们能够知道这些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嘛。现在就只有一个人愿做我们的同志,由于他是穷人,是个孤儿。”他突然激动不已无法控制地向大厅里的人喊道:“没有你们,我们同样的前进,我们不再哀求别人,你们这种人我们并不希望!你们只配挨机枪的子弹!”他怒气冲冲地喊出最后一句话,就从台上跳了下来,坚定不移地径直向出口处走去。
主席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参加晚会。就在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扎灰心地说:
“真是太让人生气了!扎尔基说得对!找这些中学生来开会,不仅不能起到丝毫作用,反而会让人感到更不舒服更怄气了。”
“这很平常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他们之中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几乎全都是小资产阶级,要不就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你要把锯木厂和糖厂作为依靠对象。但不管怎么说,会开得还是有必要的,学生之中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同志吧。”
丽达很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观点,她说:“我们的任务,谢廖扎,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给所有人的思想中去。党一定使劳动人民重视每一个新的事件,我们还要更多地召开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在车站,政治部已经准备举办夏天露天剧场,这两天宣传车就将过来了,到时我们要全力开展工作。您要记住,列宁说过:只有让千百万劳苦大众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战斗,我们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夜已太晚了,谢廖扎送丽达回车站去。分手时,谢廖扎紧紧握住她的手,好大一会儿才松开。丽达微微地笑了笑。
回城的路上,谢廖扎也顺便回家一次。面对母亲的责备,他接下来没有与母亲发生争执。
然而,当父亲开始责骂他时,他立即顶撞了去,顿时把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得理屈词穷了:
“爸爸,你说说,德国人在这儿时,你们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当时你也想过家庭吗?考虑过的,但你却不管不顾地做了,这是缘于你的良心。我明白,如果我们一定要离开,由于我的原因,你们会被搜捕;但只有我们胜利了,我们才会彻底翻身的。我不能只会留在家里。爸爸,这一点你要明白,那干吗还要阻三拦四呢?我做好事,你应当鼓励我,帮助我,可你还懈气。爹,我们不要再争执了,这样,我也不会被妈妈骂了。”他温和地微笑着,那对天真、聪慧的大眼睛自信地看着父亲。他相信他会成功的。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有点显得不安了。他笑了起来,在好久没有刮的杂乱的胡须间露出好久不见的笑容。
“你这小子,居然敢和老子讲人生的大道理?你以为你有手枪,小心点我也可以打你的。”
不过,他并没有真的要打的意思。他不好意思地想了片刻,后来,断然地把粗糙的手交给了儿子,而且还说道:
“好好去干吧,没有人会挡你,工作太忙了,就不要经常回家了,不会有人怪你。”
夜,一条亮光从稍开的门缝里露了出来,照在台阶上。在一间摆有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内,庞大的律师桌旁坐着五个人。正在举行革委会会议,里面的人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模样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其余的两名委员——傻大个儿、铁路工人舒季克和小扁平鼻的机务段人员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身子斜靠桌边,用坚定不可动摇的目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沙哑的嗓音一字一句地说:
“前线要供养,工人也是要吃饭。我们刚来,投机商和市场上的贩子就把物价全提上去了。他们不要苏维埃纸币,用沙皇尼古拉旧币或克伦斯基政府发行的纸币才能进行交易。今天我们就要制定合理的物价。我们心里都明白,任何一个投机商都不情愿按固定价格出售商品,他们必然要把东西隐藏起来。这样,我们就一定要搜索,征收这些吸血鬼囤积的商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工人挨饿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让我们仔细斟酌不可鲁莽行事,我看,这体现了她的软弱性。你也别不高兴,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只是就事论事,没别的。而且,问题的关键之处并不在那些小商小贩身上。今天我才知道的,在旅馆老板鲍里斯·索恩的家里还有一个不被人知的大地窖。还在彼得留拉匪徒占领本城之前,好多的大店主就把大量商品聚集在那里。”他笑了笑,充满了讽刺的气息,他在等待季莫申科的回答。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惊慌地问道。他很懊恼,因为本来由他来调查这些情报,但多林尼克却抢前了一步。
“嘿——嘿——”多林尼克也笑了,“兄弟,什么东西也不能瞒得住我的。告诉你吧,我不仅知道这事,同时我还知道你的驾驶员昨天饮了半瓶私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