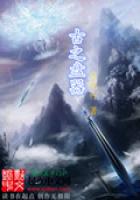说着,冉阿让不慌不忙,以简捷、稳健、准确的动作解开自己的领带,绕过孩子的腋下,系在她身上,不让她觉得太紧。随后,他把领带结在绳子的一端,打了一个海员们所谓的“燕子结”,咬住绳子的另一头,脱下鞋袜,并将鞋袜丢过墙头,跳上土堆,开始从两端相会的墙角上往高处升。他的动作稳健踏实,脚跟和弯肘都有一定的章法。这样,不到半分钟,他就已经在墙头之上了。
珂赛特一声不响,呆呆地望着他。冉阿让的叮嘱和唐纳德这名字早将她吓麻木了。
她忽然听到了冉阿让的轻轻喊声:“背靠着墙。”
她把背贴在墙上。“不要出声,不要害怕。”冉阿让又说。她觉得身子离开了地面升起来。到了墙头之后,她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冉阿让将她背起来,用左手握住她的两只小手,平伏在墙头上,一直爬到那斜壁上面。这里有一栋小屋,屋脊和那斜墙相连,屋顶角度平缓,屋檐离地面很近,那棵菩提树就在它的一边。
墙里的一面比临街的一面要高许多。冉阿让朝下望去,只见地面离他还很远。
他刚刚触摸到屋顶的斜面,手还没来得及从墙脊上抽走,便有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沙威领着巡逻队赶到了。
“搜查这死胡同!直壁街和比克布斯小街已经有人把守了。我保准他在这死胡同里。”沙威吼着。
士兵们一齐冲向让洛死胡同。冉阿让扶着珂赛特,顺着屋顶滑了下去。也许是因为恐怖,也许是因为胆大,珂赛特一声都没有吭。她只是手受了点轻伤——擦伤了一点皮。
六、谜
冉阿让发现自己落进了一个园子。那园子相当大,形状奇特,园子呈长方形,中间有一条小路,园子中央,有一棵极高的树孤零零地立在那片宽敞的空地上;此外还有几株果树,散乱的枝条蜷曲着;还有几方菜地;有一片瓜田,月光把玻璃瓜罩映得闪闪发亮;另外还有一个蓄水坑;几条石凳分布于各处,若干纵横的小道,两旁栽有颜色暗淡的、挺拔的小树;道上,杂草和苔藓混杂在一起。
冉阿让身处一栋破屋旁边,他正是从那破屋顶上滑下来的。屋旁有一堆木柴,木柴后面靠墙的地方有一个石刻人像,人像的头部已经损坏,在黑暗中,那脸部更不成样子了。
屋子破得不能再破,几间房的前脸儿已经坍塌,其中的一间里面堆满了东西,可能是个堆废料的棚子。
园子的尽头隐没在迷雾和夜色之中。迷蒙之中还可以望见一些纵横交错、重重叠叠的墙头,像是这园子外面也还有一些园子。再往外,便是波隆梭街的一些矮屋顶。
再也想象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园子更幽僻、更荒凉了。
冉阿让首先要做的便是找回鞋子和袜子,穿上后,领着珂赛特到那棚子里去。逃匿的人总是觉得自己躲藏的地方不够安全。孩子则一直在想着唐纳德夫人,本能地蜷伏着。
珂赛特紧靠在他的身边,抖个不停。他们听到了巡逻队搜索那死胡同的喊声,街道上的一片嘈杂声,沙威对那些分头把守的密探们发出的叫声。
大约一刻钟后,那种风暴似的怒吼声渐渐远去了。冉阿让屏住呼吸,直到那些声音的消失。
他的一只手一直轻轻放在珂赛特的嘴上。他所处的环境异乎寻常,左右的墙壁好像是用圣书中所说的那种哑石砌成的。任凭外面如何喧嚣,如何吓人,这里却不受丝毫惊扰。
忽然,一种新的声音打破这种寂静。这是一种美妙的、难以形容的仙乐。这颂主歌从万籁俱寂的黑夜中传来,这天乐由合声和祈祷交织而成,由女人们演唱,既有贞女们纯洁的嗓音,也有女孩儿们稚气的童声。这歌声从园中最高的楼中传来,掩盖了魔鬼的咆哮声。
珂赛特和冉阿让一同跪倒在地。他们这样做是身不由己的,他们觉得,忏悔者、无罪者都应跪倒在主的面前。那里虽然传出了声音,但人们还是感到那大楼是空的。那声音似乎是一种从空楼里发出来的天外歌声。冉阿让耳朵里听着歌声,脑子里出现了一片晴空。
他望见的已经不是黑夜,而是一片晴天。歌声停了下来。它也许曾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不过,冉阿让说不清。人在出神的时候,时间就会过得飞快。四周又归于沉寂。墙外墙里均不再有声息。令人心悸的声音和令人心安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只有墙头上的几根枯草在风中瑟瑟作响。
七、猜不透
到了凌晨一两点钟,可怜的珂赛特一声不吭,倚在他的身旁,头靠着冉阿让低下去。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好像在担心什么。她还一直在发抖。冉阿让不禁一阵心酸。
“你想睡吗?”冉阿让问她。“我冷。”过了一会儿,她又问:“她还没有走吗?”“谁?”冉阿让问。“唐纳德太太。”
冉阿让原先用来吓唬珂赛特的话,早已被他忘掉了。“啊!”他说,“不怕,她早走了。”听了这话,孩子叹了一口气,压在她胸口的那块石头被拿掉了。
地上很潮,风越来越冷,老人脱下大衣披在珂赛特的身上。
“这是不是暖和些了?”他说。“好多了,爸!”“那,你等等。我去去就来。”
他走出棚子,向大楼走去,想找一处比较安稳的藏身之地。他看见好几扇关着的门,楼下的窗子全都装上了铁条。
他走过建筑物靠里一端的墙角发现面前有几扇拱形窗,窗子里亮着灯。他停在一个窗子前,踮起脚尖向里面看。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厅,有许多窗子,地上铺着宽石板,中央有几个石柱,顶上有穹窿,墙角有一盏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厅里寂静无声。仔细望去,地板上似乎横着一件东西,像个人体,上面盖着一条裹尸布。那东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脸朝地板,两臂左右平伸,与身子形成一个十字形,一动不动。那吓人的物体,脖子上还有一条绳子拖在石板上,像一条蛇。
厅堂的一切在昏暗的灯影中若隐若现,恐怖异常。在这阴森的地方,在这凄冷的黑夜里,看到这种僵卧的人形,那东西可能是死的,那也已够使人胆寒的了,假如它还活着,那就更令人心惊了。
他大着胆子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想看清楚那东西究竟是死是活。越看越怕。那僵卧的人形竟一丝不动。他忽然感到一种难以说明的恐惧,迅速逃离。他朝棚子奔跑,不敢往后看,觉得一回头准会看到那人形迈着大步、张牙舞爪地在后面追着他。
他心惊气喘地跑到了破屋边,跪在地上,被吓出一身冷汗。
这是什么地方?谁能想到在这巴黎城中竟会有这等鬼蜮之地?一座多么阴森神秘的建筑物!刚才,这里的天使们在黑暗中用歌声招引灵魂,当灵魂招来后,却又陡然示以这种骇人的景象;而那确确实实是一座建筑物,是一座临街的有门牌号的房屋!不是梦境!但冉阿让得摸摸墙上的石条才能信以为真。
寒冷,焦急,忧虑,一夜的惊恐,他发起烧来。他回到了珂赛特身旁。她睡着了。
八、另一个谜
孩子枕在一块石头上,早就睡着了。冉阿让坐下来,看着她睡。看着看着,他渐渐安定下来,思维也渐渐恢复。他开始知道,今后,他活着的意义在于与这孩子在一起,只要她在,只要他在她的身边,他就什么不再需要,什么不再惧怕。
此时,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铃铛的声音,不止一次地从园子里传过来。声音虽弱,却很清楚,听上去很像夜里在牧场上听到的那种从牲口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低微的乐音。
冉阿让顺着那声音转过头去。他发现园里有个人。
那人好像是个男子,正在瓜地里那些玻璃瓜罩间走来走去,他时而弯下腰去,时而站起身来,好像是在拖着或撒播着什么。那人的腿像是有些瘸。
冉阿让为之一惊。白天,他们提防着,因为白天可以助人看到他;黑夜,他们提防着,因为黑夜可以助人发觉他。开始时,冉阿让因为园里荒凉而惊慌,现在,他又开始因为园里有了人而惊慌了。
他又从想象中的恐慌跌进了实现中的恐慌。他想到,沙威和密探们可能还没有离开,他们一定有人守候在那里。假如眼前这人发现了他,一定会大喊捉贼,这样他就逃不掉了。他把睡着的珂赛特轻轻抱起来,挪到破棚最靠里的一个角落里,放在一堆废家具后面。
在这角落里,他仔细地观察着瓜田里那个人的行动。刚才听到的那铃声,就来自他那里。他走近,声音也近,他走远,声音也远。很明显,铃铛是系在那人身上的。不过,这是怎么回事?身上系个铃铛,究竟会是个什么人?
冉阿让一面胡乱地猜想着,一面伸出手摸珂赛特的手。她的手冰凉。
“啊,我的上帝!”他叫了一声。他低声叫她:
“珂赛特!”她不睁眼睛。他用力推她。
她还是不睁眼睛。“难道她死了!”他说着,随即站了起来,浑身抖个不停。
他头脑里出现了一阵乱糟糟的恐怖的想法。珂赛特,脸色发青,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脚前的地上。他听到了她的呼吸声,还看到了她在吐气,但是,他觉得她的气息已经弱到快要停止了。怎样才能让她暖和起来呢?怎样让她醒过来呢?除了这两件事以外,他什么也不顾了。于是,他发狂似的冲出了棚子。
一定要在一刻钟之内让珂赛特躺在有火有床的屋子里。
九、系铃铛的人
冉阿让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卷纸币,把它捏在手里,向那个人奔去。
那人正低着头,没有发现他走近。冉阿让没跨几步便到了他的身边。
不问青红皂白,冉阿让便喊:“100法郎!”那人吓了一跳,眼睛瞪得溜圆。
冉阿让又喊:“如果您今晚给我找个地方过夜。我给您100法郎!”
月光照亮了冉阿让那惊恐万状的面孔。“啊,是您,马德兰爷爷!”那人惊叫了起来。在这样的黑夜里,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从这样一个不认识的人嘴里喊出这样的名字,冉阿让倒退了几步。
和他说话的是一个背驼腿瘸的老人,衣服穿得差不多像个乡巴佬,左膝上绑着一条皮带,上面吊了个铃铛。他的脸正背着月光,看不清。
这时那老人已经摘下了帽子,哆哆嗦嗦地说道:“啊,我的上帝!马德兰爷爷!您怎么会在这里?您是从哪儿进来的?”老头儿一句接着一句,带着乡下人的那种爽利劲儿,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让人听了感到痛快。他说话时表露出惊讶和淳朴的神情。
“您是谁?”冉阿让问,“这宅子是谁的?”
“啊,上帝,您在开玩笑!”老头儿喊道,“是您把我安置在这里的,是您把我介绍到这里来的。可您问我的是什么话!您会不认识我了?”
“我不认识您,您怎么会认识我的?”冉阿让问。“您救过我的命啊。”那人说。那人转过身去,一线月光正照着他的半个脸,冉阿让认出来了——福舍勒旺。“啊!不错,是您。”冉阿让说。
“亏了您还认得我!”老头儿带着埋怨的口气说。“您在这里干什么?”冉阿让又问。“嘿!我在盖瓜呀!”当冉阿让走近福舍勒旺时,那老头儿正提着一条草帘子准备把它盖在瓜田上。他已这样干了一会儿了,盖上了好多这样的草帘子。冉阿让在棚子里看到的他的奇怪动作,正是他干活的动作。
“您的膝部为什么挂着个响铃?”
“您说这铃铛?”福舍勒旺回答说,“它一响,好让人家听了避开我。”
“这又是为什么?”
福舍勒旺老头儿做了个挤眉弄眼的动作,阴阳怪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