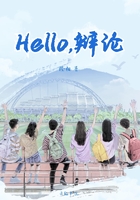彼得也不是没有心计的。普通应用的字凡是开头是一个难字母的,他就避了不用,另外觅了许多可以替代的字作为准备。因此猫(Cats)他总叫pussies,不是他故意学着孩子气,是因为P字比不可能的C字能念出口的多。coal(煤)他得说成更含混的fuel(烧料)。碰到dirt(脏)他总说,muck。他这发现替代字的巧妙就比得上早先盎格鲁撒克逊的诗人们,他们因为诗里只用头音(alliteration)不用尾音(rhyme)逼得去打找开头同字母的字。比如说到海,现成的sea字不用,因为要协waves或billows就得把海叫作whale-road(鲸鱼道)或bath of the Swflrls(天鹅的深池)。但是彼得却不能充分利用他的撒克逊祖宗的诗的权宜,因此有时,他搜索不到方便的常用的字来作替代时,就非得硬了头皮把最难的字一个个字母给拼了说,所以他逢到要说cup他就决不定还是说mug还是念c,u,p再要逢到egg,他知道决不能说ovum虽则那是唯一可替的字,他只能期期的念着c,g,g的了。
这时候堵着他的是dog那个气人的小字儿。彼得本来有许多别的法子说狗。因为p比d是一个稍为容易一些的字母。他在不十分着急的时候可以说“pup”。要是p来得不顺口。他还可以把那兽,虽则难免滑稽以及带些唱戏的腔调,叫作一只hound。但如今有这两位仙女在他跟前,彼得不由得有些心慌,这来一个d字固然念不出口。就连一个p字或一个l字都变了万难的了。他极苦痛的忍着不出声。满想这个不成那个总可以的来解决这问题。先想说dog,然后pup然后hound。他的脸涨得极红。他是在受罪。
“Here's your whelp.”他终于挣出了口。那个字,他未尝不觉得,是莎士比亚气味太重了些,普通用实在有些不合适。但他除了它再没有别的字说出口去。
“真真多谢你,”幽说。
“你是能干,你是真真能干,”哑说,“可是我恐怕你是受了伤了吧。”
“喔,不——不要紧的,”彼得慨然的说。一边他把他的手绢绕着,他把他的伤手插在口袋里去了。
同时幽已经扣上了绷瓜的领圈,“你可以放下他了,”她说。
彼得听话松了手,那小黑狗立时就向着他那悻悻然退去的敌人的一方猛跳,它一猛的向前使尽了皮带的长。激得它在后腿上站了起来,它这相儿,一面叫着,就像是一个徽章上的一只猖狂的雄狮。
“可是真的不要紧吗?”哑追着问,“让我看看。”
彼得又听话,拉去了绕着的手绢,把手伸了出来,这使他觉得事情来得都很如愿。可是他一发现他的指甲的脏他又不由的着急。嗳!要是他,要是他出来以前想得到洗一洗手多好!这叫看了多寒伧!红了脸。他想收回他的手。但哑拉着它。
“等着。”她说,然后她又说:“咬得很凶的。”“唷,糟极了,”幽也加入,她也偻着相他那手。“我真是抱歉,我的笨狗会得……”
“你得立刻到药铺子去,”哑打岔说,“叫他们替你洗干净了包起来才好。”
她把她的眼从他的手移起来望他的脸。
“到药铺去,”幽也同意,她也仰起了头。
彼得从这个看到那个,那张得大大的蓝眼睛和那眯细的奥妙的绿眼睛一样看得他眼花。他含糊的望着她们笑。又含糊的摇着他的头。同时他趁着她们不注意的时候把他的手重复用手绢裹理好了缩开在一边。
“这不——不要紧。”他说。
“可是你一定得去,”哑逼着说。
“一定得去,”幽说。
“不——不要紧,”他重说了一遍。他不要到药铺里去。他要跟仙女们在一起。
幽转过身去向着哑。“Qu'est-ce qu'on donne a cepetit bonhomme?”(这好孩子我们给他点儿什么呢?)她问,说得很快,声音也很低。
哑耸耸她的肩膀,抿一抿嘴,表示她没有主意。“llscrait offense,peut-etre”她说。(说不定他要生气。)
“Tu crois?”(你以为吗?)
哑飞快的望他们讨论的题目看了一眼,这一眼把他整个儿批评的看了进去,从他的破毡帽到他的破鞋,从他的惨白的长斑点的脸到他的极脏的一双手,从他的钢边眼镜到他的皮表带。彼得知道她是在看他,心里觉得一种带羞的含糊的快活,望着她微微的笑。她多美呀!他想不知道她们偷偷的在说些什么了。也许她们在那里商量要不要请他吃茶去。这念头一转到他就觉得准是了的。奇怪极了。事情来得正如他梦里的景象。他想不知道他有没有那胆子对她们说——这第一回——叫她们不妨到他的心里去找汽车。
哑又转身去向着她的朋友。她又耸了一耸她的肩膀。“Vraiment,je ne saispas.”她低声说。(我实在不知道。)
“Si on iui donnait une livrase?”幽出主意了。(给他一镑怎么样?)
哑点了点头。“Comme tu vonaras.”(你说好就好。)一面还有那个在她的手袋里装得没事似的摸索的时候,她对彼得讲话。
“你真是勇敢得很,”她微笑着说。
当着她那镇定的冷静的注视,彼得只能摇他的头,红着脸,低着他的眼。他真想看她,但事到了临头,他又受不住她那一双晶莹逼注的明眸。
“也许你是玩惯了狗的,”她接着说,“你自己有没有狗?”
“没——没有,”彼得挣着说。
“嗄噢,那更显得你的勇敢了,”哑说。这时候她一回头看见幽已经找着了钱,她就去拉那孩子的手,很亲热的摇着。
“好,再会吧,”她说,笑得益发的动人了。“我们感激你极了。真的感激极了,”她重复说。她一面说一面心里奇怪她何必这极了极了的尽说。平常她是很难得那么说话了。可是跟这孩子谈话仿佛这正合式似的。她跟下一等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极恳切,说话极使劲。满是个学生的口吻。
“G-g-g……”彼得开口了。她们就这么走了吗,他满痛苦的在想,忽然从他的舒服的桃色的梦里醒了过来。真的走了吗,既不请他去吃茶又不给他她们的住址?他想要求她们再呆一会儿,他想再有机会见到她们。可是他知道这一套话他是说不上来的。哑已以对他说了再会。这在他看来就像是眼见一种怕人的大难快要来到,他可一点没有能力去防守它。“G-g……”他微弱的挣着想说话。可是他发现他自己这一个致命的再会还没有咽下去又在跟那一个拉手了。
“你实在是好,”幽说,拉着他的手。“真好。说起你非得到一家药铺去立刻洗干净,你有咬伤。再会吧,多多的多谢多谢你。”她说末了的几句话的时候,她把一张叠得方方的镑票塞在他的手掌心里,再用那一个手帮衬,把他的手指给捏紧了。“多谢多谢你,”她又说。
脸涨得火红的,彼得摇着他的头。“N-n……”他想说话,又想叫她拿回那一张钞票。
但她却笑得更甜蜜了。“不错的,不错的,”她连着说,“请你……”她再不停留,旋转身轻盈的跟着哑跑了去,这时候哑已经向前走,走上了路,带着那气愤的绷瓜,它还在叫,蹶着想脱离那皮带。
“好了,全妥当了。”她说,跟上了她的同伴。“他收了吗,”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