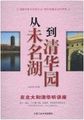她正为这一早的疯颤想来和她朋友商量,她一看莫须有太太已经出门去了,脸上立刻显露失望。但这只是一时的。一般妇人大概都有一种对于妇女的社交知识。她们交际的态度总是很好的。其实,她们仿佛都是彼此猜忌,必须用种种可能的方法;恭维,奉承,或郑重的手段,去互相调和。女子之间彼此很少自由,因为除了两个极端相反的东西之间没有真的自由或真的相识。同类之间只不过外表相像,异类之间才有一个空间使彼此的好奇与精神都可以在那里探险。两个极端一定会相遇,相遇是因为他们的急迫的需要,也就是他们所以有距离的原因;他们的距离愈远,回头愈速。他们的接近也就愈热烈:他们也许将各人撕成粉碎,也许彼此熔化成为不能熔化的,新奇的,但是再也产不出别的好东西,两性之间在交际上有一种非常的真自由。他们相识乃是识透了彼此的心理。一对不相识的男女在一刻钟之内可以完全相识。这大概是真的,他们见面不到几分钟彼此便竭力的说明自己;但是男子见了男子未必能如此,女子见了女子尤其不如此了,因为这些都是平行线永远不会相遇的。后者的相见,特别的,往往自始至终是在武装与算计的中立状态之中。她们用一种永远不离她们左右的严重的社交手段保守她们中间的距离与各人的意见,这种手段比什么都厉害,曾经帮助建立各种礼节,我们现代文明一半差不多就是这些礼节。男子们都知道女子与女子同住没有不打架的,她们也得不到旁的女子像男子替女子做事所用的那种好心来替她们做事。如果这话不错,这理由不应该在女性间的复杂情形,如同猜忌或激烈的竞争里寻找,应该在女子永远忍受的那种身体上的循环不已的变动里寻找。男子能够并且愿意用他拳头去答复别人对于他的侮辱,因此他们彼此见面反倒变为和平,好脾气了;女子在她们的同性与她们自己的容易受刺激的感情之间也设了种种规矩礼节作她们的防御线。
喀佛底太太藏起她的失望,格外和颜悦色的同玛丽谈天。她坐在床边谈论凡是女子可以谈论的各种问题,人都以为女子虽然不断的谈话,但是她们的谈话总不出乎客厅与厨房之间,更详细的说,就是在楼顶的小屋与碗盏室之间,但是这两个极端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狭隘,因为从楼顶的小屋望出去只看见星宿,由碗盏室开出去是厨房的小院或一堆垃圾——她们的眼界就是她们的地平线。死与生的玄妙占据女子的心里胜过占据男子的心里,对于男子要以政治与商业的投机为最合式。女子深深的从事于直接的买卖,和交易时所有的绝对的形式,所以女子对于商业的实际情形往往比较许多商人更明白。假使男子能知道家庭经济有女子所知的一半,他们的政治经济与他们的全体的重要政治也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无益的扰乱了。
以上这些话玛丽都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层,这时她正希望有人给她作伴。假使没有人在她身旁,她也许非遇见某种思想,记忆、影像不可,她心里恍惚觉得总以不过遇见这些为是。她昨天的工作,她在屋内遇见的那位姑娘,那个巡警——所有这些记忆她在心里一一绕着躲开了。她决意把所有于这些记忆有关系的念头一齐抛开。如今在她意识内隐约浮泛的巡警不是一个合意的人,甚至于不是一个人,一个距离,仿佛是儿时的一瞬,仿佛是已经忘了一半的怪物,一种永远不该复活的记忆。她的模糊的思想把他隐藏了,仿佛变成一个已死的人,她无论在那里永远不会再见他。所以她决计把他关在她心内的不舒服的牢狱里,他虽然无力,依旧在那里挣扎,不定那时候好像一个奇怪的问题或忽然的羞赧蓦地里跳了出来。她把他隐在一个玫瑰色的红晕里,这红晕只要吹一口气便可以满脸通红,她却掩在喀佛底太太的滔滔不绝的谈话后面躲着他,她仿佛从梦里纱里望出来似的,时时望见他的帽尖,跷着的坚细的胡须,和一对高耸的肩膀。她对着这些隐约的鬼相,就拿一大阵的话把他的鬼影子给淹了去,但是她知道他等着要捉她。而且他一定能捉住她,她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恨他了。
二十二
喀佛底太太提议要同玛丽出去买办那天的饭菜,她披上围巾,戴上帽子,吩咐了她的孩子们不许走近火炉,煤斗与脏水桶,她给了每人一片面包,又把每个孩子一一的交给其余的几个管束,同时玛丽的细腻的打扮只剩戴帽子的两层手续了。
“等你有了孩子,我的宝贝,”喀佛底太太说:“你就不会这样打扮了。”她又告诉玛丽,她自己年轻时她总要费一点半钟的工夫才能梳上她的头发,她特别注意穿一件外衣或套裙子在腰带上,这点事情要麻烦她两个钟头,但是她很高兴。“可是,”她大声说:“你一有孩子,所以这些打扮都完了。等你有了六个孩子,天天早晨要你给他们穿衣服,有的鞋子不见了,有的同别人的闹错了,一个个扭来扭去像盆里的鳗鱼似的,总要你把他们身上的魔鬼打出去才能够把他们的袜子穿上;你听罢,不是脚指头钻错了地方!就是埋怨你把别针扎了他们的肉!又说你把胰子磨了他们的眼睛!”喀佛底太太翻着两眼,举起两手,对着房顶默默的埋怨上帝,既而又很绝望似的落了下来,好像她这样的人上帝永远不理会的——“一个个的够你打扮的,有一点余暇为你自己打扮那真是幸福。”她说。
她满口称赞玛丽的头发,她的相貌,她的脚小,她的眼大,她的身腰苗条,她的帽子,阔的鞋带:她这样公平这样周到的赞美她,甚至在她们出去时说得玛丽脸都绯红了。玛丽一边感激她的赞美,一边又有女孩子应有的那种自信,相信她自己确是漂亮的。
这是一个美丽的淡灰的天色,天空是沉重的仿佛永远不能移动或改变似的,正是爱尔兰常有的那种满天云影的天气,空气非常澄清,连极远的地方望得逼真。在这样的天气各样东西显露得极清楚,一条街已经不是一大堆房子害羞似的挤在一起,怕缩缩的惟恐人家看它们笑它们了。这时候每所房子都恢复了它的个性。那些街道有一种胜任的精神知道它们身上背着它们的马,汽车和电车,用一种谦逊的态度作它们的装饰如同用花冠作装饰的一样,这美不是平常有太阳时候的一类,因为太阳光只是逞年轻,一种落拓相,这天色可不同,历史的面目,千百种陈迹的记忆,全都展露了出来:就比是一副沉静的面目,由经验结成知识又由知识化生慈悲的智慧。伟大的社会性的美在这天色下在市街上闪亮,那天空阴沉沉的孵着就比是一个有思想的前额。她们两人一路走,喀佛底太太计算她买的东西,仿佛一个带兵的将军计划他的战略。她的买东西与莫须有太太的买东西大不同,因为她所需要的是八口人的食料和衣料,莫须有太太不过是两口人的需要。莫须有太太是到离她家最近的铺子里去买,她同那个店主是有交情的。假使铺子里要的物价或给的东西稍有可疑的地方她立刻拿了去退回。第一次给定的什么价钱便成了莫须有太太终身不变的标准,要脱离这个价那是不行的。鸡蛋卖给别人都可以涨价,独有卖给她不能。假使莫须有太太一听得物价涨了,她立刻气的眼也睁大了,身体也战栗了,说话也多了,平日的交情也破坏了,非得她的条件被承认,并且定为适中的标准之后才肯罢休。喀佛底太太便不如此,她认为所有的店主都是各人的仇敌,也就是人类的仇敌,他们最好剥削穷人,所以凡是好百姓都应该用一种激烈的战争去反抗他们。她对于货物的材料,物质的好坏,新鲜的程度,本地与他处的价格这种知识很丰富。她利用一种很有效力的方法:在克兰勃拉西街上说莫利街上的价钱,假使那个店主不肯减去他的价格,她就会大声的不赞成的吵得别的雇主一看那个骗子的假面具被揭穿了,便都走开了。她的方法是出人不意的。她抓起一样东西向柜台上一放,嘴里说以下的话,“六个便士,多一个不要;我在莫利街上只花五个半便士就成了。”她知道所有的铺子里总有一种货品价钱特别便宜的,所以她交易的范围很广,她不是买完这样买那样,她常常离开她的战线嘴里这样说:“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她一进了铺子,她那只大圆眼睛只要一瞥,便把千百条货物与价格的条目都摄了进去,并且永远不会忘记的。
喀佛底太太的女儿,挪拉,不久将行第一次的圣餐礼。这是一个小姑娘同她母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礼节。一套白洋纱衣服蓝色腰带,一顶白洋纱帽子镶蓝色的缎条,棕色皮鞋一双与棕色最近似的袜子——这些都得备办的。这是个对于这事有密切关系的人的重要时间。世上每个姑娘都会行过这礼:她们都穿这样衣服,这样的鞋,在这一两天内所有的妇人,无论她多大年纪,心里都爱那个行第一次圣餐礼的小姑娘。这事的魔力就不定比什么都厉害,可使一个过路人回想到他小孩的时代有目前的快乐,目前的好奇与前途种种的希望,种种的冒险。因此给女儿打扮得合式竟是一种对于公众的义务。做母亲的个个都很劲的做那对的事情,并且竭力做到备受她的同伴的赞赏,哪怕就只一天的赞赏呢。
找一双棕色袜子同一双棕色鞋彼此要相配的是给喀佛底太太和玛丽的一个难题,但是高兴的。鞋是已经买妥了,现在要找一双袜子与鞋的颜色一模一样的真不容易。论千的盒子找开过,检选过,一个个都撂在半边,要完全相像的颜色终究没有找到,她们从这铺子出来到那铺子,走完这条街又走那条街,她们的寻觅带领她们穿过葛莱登街,路过看见了一家店,这店里喀佛底太太在一月前会见过有同棕色相仿的袜子,现在要有,大概可以配得过了。
她们一路走去路过大学院,走进那条益折的街道玛丽的心怦怦的跳起来了。这时她眼里既看不见来往的车辆与拥挤忙迫的路人,耳内也听不见身边那位同伴的热心讲演。她的两眼尽对十字路口瞧。她不敢转过脸来,也不敢对喀佛底太太说什么,一转瞬她便看见了他,魁伟的,静默的,正合式的,那个他的世界里的帝王。他是背朝她,他的高大的肩膀,坚实的腿,红色的脖子同那剪得短短的铁丝似的头发很奇怪的射进她的眼内。这时她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仿佛同他相熟的但又似隔膜的,这感觉使她两眼十分好奇的牢牢的钉在他身上,她看得连喀佛底太太都注意了。
“那男子很体面,”她说,“他用不着找姑娘去的。”
她说这话时她们两人正从那个巡警身旁走过,玛丽知道她的眼睛刚离开他,他的视线差不多像机械似的立刻落在她的脸上,她暗喜这时幸有喀佛底太太在她身旁:假使她独自在那里,她一定急得快走了,差不多要飞跑了,现在有她的同伴给她勇气,使她镇静,所以她敢昂头阔步的走。但是她心里已经震荡了。她可以觉出他的眼珠从她头上直转到脚上,她可以看见他的大手伸上来摸他的鬈曲的胡须。所有这些她都可以从她受惊的脑筋里看见,但是她不能思想,她只能感谢上帝因为她身上穿着那套最漂亮的衣服。
二十三
莫须有太太在那里计划赎回她病中当去的那些木器和家具。有的是在许多年以前她出嫁时从她父亲家里搬来的。这些东西是她生下来就看见的,她一生的记忆永远在它们的周围旋绕的老东西之中的几件。一把她父亲生前常坐的椅子,她丈夫向她求婚是曾在这椅子边上欠着身子坐过的。她女儿小时候曾在这椅子里缚过的。一长条地毯和几把刀叉是她一部分的妆奁。她极宝贝这些东西,假使她的工作可以赎她们回来,她决计不再舍弃她们。因此她不得不受像奥康诺太太这样人的气,这种气不是她愿意受,只因为上帝的命令勉强受的,这种命令虽然可以有合法的批评,但是必须要服从,莫须有太太很决绝的说她十分厌恶那个妇人,她是一个眼里无情的人,她的唯一的才能就呼喝那些比她能干十二倍的人。莫须有太太不得不为这样一个人工作,服从她的申斥,听她的指挥实在是她的苦痛,所有这些事情她以为都不应该。她并不希望这个妇人倒霉,但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她一定会叫她老实,不再如此乱闹,这是她天天所期望的一日,无论什么人只要收入富裕都可以买一所房子,可以花钱雇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足以骄傲。许多人,假使有这样的收入,一定可以有一所装修齐备的房子,对待侍候他们的人会更大量,更和气。当然不能人人都有一个当巡警的侄子,有许多人还不愿意同巡警有一点关系哪。强横霸道的东西们,拿谁都当做贼看!假使莫须有太太有这样一个侄子,她一定要毁坏他的骄气——那个混账东西!这时莫须有太太渐渐的愤怒起来。她的眼睛里冒火,她的大鼻子渐渐的缩小了,泛白了,她的两手使劲抖擞着。“现在你不是在法庭,你这猴子,——我这样说,你的满脸的老腮胡子,他的大脚,除了他那种愚妄的自尊之外世上没有比他的脚再大的东西。”“你有一个女儿的,是不是,奶奶,他说,她有多大年纪了,奶奶,你说,你的姑娘人好吗,奶奶,他说?——但是她止住了他——那个妇人得意他比一个皇帝得意他的皇冠还要得意!不要紧。”莫须有太太说,她在屋内奔过来奔过去的,把空气撕成了一片片的全都扔在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