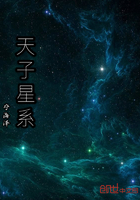从极远的地方时时传来一种哒,哒,哒的脚步声,一种遥远,微细的声音,有时渐渐消灭反应到旁的街上,有时铿,铿,铿的走向他站的地方来,这声音便渐高渐响亮,响了又响的变成两三个回声。那时候他深深的退到一家门洞里,仔细瞧瞧这深更半夜还有谁出来,那人便带着非常的使命走去,他的脚步向着极远的地方走下去,直到他走的最后的回声与最后的微细的震动旋转到了寂静。时时有一只猫很小心的躲在铁栏杆上,或一只迷路的狗惊慌的偷着在路上走,无论灯光底下,黑暗地里,到处都拿鼻子嗅嗅,只不作声,又饿又着急。他告诉她许多故事,那种令人惊骇的故事,讲到打仗与诡计,一生专弄诡计的男女,除了偷盗和强横不知别的事情的人们;天生会偷盗的人们,专靠诡计和偷摸吃喝的人们,用骗术结婚的,真古怪,低陋的路径走到死境的人们。他又告诉她许多故事:两个饥饿的男子,被盗的水手与一段有趣的笑话,讲一个发匠有两个母亲。他又告诉八个机器匠,半夜里偷鱼的老太太与他释放的男子的故事。他又告诉她一段可怕的故事,他在一间小屋内同五个男子决斗,他又指给她看压在帽子底下的大黑疤与他脖子上的几条伤痕,这些都是被瓶块扎破的,还有他的手腕上是被一个意大利的疯子用尖刀戳伤的。
虽然他永远说着话,并非永远说他自己。从他的谈话里引出一大串问话来——琐碎微细的问题从他的故事里滚出来钻入她的生命里。很巧妙的,自然的,自动的问题只有女孩子可以领会那发生这些问题的用意。他问她的姓名,她的地址,她母亲的名字,她父亲的名字;她有没有别的亲戚,她已经做事了没有。她奉什么宗教,她离开学校很久了吗,她母亲的职业是什么?所有这些问话玛丽都很高兴的,诚实的答复了。她知道每个问题的来临,并且预料问题背后的个人的好奇,她对于这些都很高兴。她也爱问他的个人的,切己的问题,关于他的父母,他的弟兄,他的姊妹,他祈祷的时候说什么话,他有没有同旁的女子走过,如果有的,他会对她们说些什么,还有,实在,究竟他以为她怎么样?她关于这种种的好奇心是很多,很热烈,但是她连提都没有胆量提。
有一个问题他屡次问到她,而她屡次闪开的——她躲避它好像是一个恐惧似的——这个问题就是“她母亲的职业是什么?”她实在不好说她母亲是一个做散工的女仆。这样说总有点不妥当。她忽然对于这种职业懊恼起来,羞耻起来。这是一种最下贱的职业。这似乎是一种最卑鄙的职业,人人都可以做的;直到这个问题用各种方法提出之后,她不能再不答复了,但是她隐藏了事实——玛丽对他说了一句谎话,她说她的母亲是一个裁缝。
十四
一天晚上莫须有太太回家来精神很不好。她又懊恼起来为什么她这样头痛,这样疲倦。她说要她提水这件事情最麻烦不过,并不是她提不了,实在她按不下心做这件事。支配她意志的机关仿佛暂时不在她脑里,用两手使劲按在一个拖布上,把它绞成螺旋形,绞得它干干的,这件事情假使她愿意干,她觉得她能干的,可是她心里真不愿意做。这些事情虽然在她手里正做着,觉得很奇怪,离她很远似的。那个水桶,虽然手不久还在那里在浸着的,不知怎的,好像离得老远的,要拿起那块放在桶旁的胰子来,得用一条比一臂还要长的胳膊才能够得到。洗完了,磨完了一方地板再要去够那没有洗过地方怎么样身子可以不移动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样疲乏使她吃一惊。她的头痛,虽然不轻,倒不在乎。人人都有头痛腰酸挫筋等小毛病,但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疲倦与稍微使点劲都不情愿的情形使她吃惊。
玛丽哄她出去看看那些去丽华戏院的人,她说今天有一个名角在那里演戏,所有都白林的女子,甚至于从老远的地方都来看他,现在立刻就去也许可以赶上看见他坐在汽车内停到戏院的后门,那时她们可以仔细留心他从车里出来走进戏院去。莫须有太太听了这些消息,便从她那种异乎寻常的冷淡之中一时高兴起来。自从吃茶以来她便坐在那里(不像平常那样笔直,那样指手画脚的),但是腰驼背屈的瘫着(两眼注视炼乳罐外的一滴牛乳)。她说了她想要出去看看那位大名鼎鼎的戏子,虽然她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女子都像发疯似的要去看他,但是不一会工夫她又回复她那种腰驼背屈的样子,又收回她的视线到那个炼乳的罐上。玛丽有点费事的将她放倒在床上,她们两人互相搂抱了一回,她便很快的睡着了。
玛丽为她母亲的病痛心里不免有点烦闷,但是向来在一个病人没有死去之前,旁人总是不容易相信他病势的厉害,所以这件事情不久也就在她脑中消灭了。况且她脑中装满了对话的许多杂碎的影像,这事更容易消灭得影迹无踪。
玛丽见她妈睡得平安,便带上帽子出去。在她当时的心境里她愿意找个冷落的地方走,这种冷落只于在人群里找得出来,她还愿意找点可以分心的事情。她近来所过的充满了冒险,连那楼顶上的小屋不但使她厌恶,并且要使她发疯,她妈的急促,困难的呼吸扰乱她的心思。屋子里的破乱家具在她眼里觉得丑极了,那块铺地毯的楼板与那没有遮蔽的沾污了的灰墙使她满心的不高兴。
她走出门去,不多一会便做了人群里的分子,这些人每夜都是来来往往的,从罗登达到撒克维尔街宽阔的路上,走过夏康内尔桥,到威斯莫兰街,经过三一学院,又穿过灯火辉煌的葛莱夫登大街圣司蒂芬公园门口的浮云里石门,从晚上七点半起都白林的少年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在这里过来过去。有时成群结队的少女们蹦蹦跳跳的跳过,每个都是嘻笑的化身。离她们不远一群少年偷偷藏藏的品头评足的跟在后面。不等走到桥边彼此便已熟识,有几个侥幸人的配上对了。但是通常都是成对儿走的。在头天晚上订的约,每条街上都充满了快活的无心无事的少年与少女——他们并非真是要求配偶,不过是享受些交新朋友的趣味,在这里将老话装新瓶子里,旧笑话变成新笑话,人人都是活泼的,除了他的同伴对谁也不讲礼貌,他们对面的或交身过的,或赶上他们而在他们面前经过的都是他们戏弄,嘲笑的目的物,同时返过身来,他们自己也是供给后来的每对的暂时取乐和谈话的资料。时时有在半途停步的,经过一番有礼貌的介绍之后,结果又重新配搭成了几对新配偶。他们分手的时候,转过头来笑着说“明天晚上”或“星期四”或“星期五”这一类话,表示对那个旧的伴侣并没有完全抛弃;于是他们各自前进。
在这些人群里玛丽急急的走过了。她知道假使走得慢些,便有那只于修饰一部分的男子,会突然问她自从上星期四以来她做过些什么事情?会把她算为嘉德爱伦介绍给与他模样相同的六个少年,这六少年便很温和的笑着,站着成一个六尺长的半圆形。这种情形她以先曾经逢着过一次,她逃走的时候那六个少年便在她背后“汪,汪,汪”的学狗叫,同时那第七个少年很起劲的高声的“苗,苗,苗”学猫叫。
她站了一会看看人们纷纷的拥挤到丽华戏院里去。有的坐汽车来的,有的坐马车。许多像出殡用的轿车将那些沉重的庄严的人们寄存到那个玻璃顶的门洞里去。那些驰骋的车在橡皮轮子上呜呜的叫着,车内载着穿着夜礼服的先生们与肩膀上轻轻飘着丝织围巾的妇女们,此外还有接连不断的行人在道上奔涌。玛丽掩在对面一家门洞里瞧着这些欢乐活泼的人们。她很天真的羡慕他们,心里念着那个高大的巡警不知会不会请她一同到戏院子去,如果请她,她妈会不会让她去。她想她妈不会让她去,但是她迷糊的觉得果真她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喜悦的邀请,她有把握会想法子出去的,她正梦想假使有这样的款待,打算要把她那件最好的外套好好的改造一下,正在这时,她恍忽看见葛莱夫登街的转角上露出一个高大个儿渐渐的向戏院走来。这人就是他,她心里乐得直跳。她但愿他不会看见她,又愿意他能够看见她,身上忽然一阵冷战,她看见他并不是一个人,一个年轻,肥胖,两颊微红的姑娘傍着他。他们渐渐的过来,那个姑娘伸手去挽着他的手臂,说了几句话。他弯下身去凑近她答复她的话,她对他嫣然的一笑。接连很快的交谈了几句,他们两人一齐笑了起来,于是他们消失到那扇卖两个半先令一张票的门里了。
玛丽回到那个门洞里。她起了一个怪想,好像人人都在看她,人人都怀着恶意的笑她。过了几分钟她走了出来,忽忽的走回家去。这时耳内听不见街上的杂声音,眼里看不见游行的人群。她走路时脸儿朝下,在她草帽的阔沿之下一双眼睛汪着两包酸泪,这种眼泪向来没有流过。
十五
第二天早上她妈身体不见得好。她也不想起床,就是听见隔壁屋里那个男子早晨起来下楼梯的脚步声都不注意。玛丽几次三番的叫醒她,但每次说完了“呕,宝贝,”她又昏昏的迷糊过去了,这种迷糊并非睡觉,实在是昏迷。她的老象牙色的焦黄的脸子薄薄上了一层颜色;她的两片嘴唇松松的张着,略有点丰肥,所以玛丽觉得她病时倒比健时好看些;但那搁在一床粗毛毡上的干瘪胳膊看去不但消瘦,简直是干枯,那双手比向来更黄,更像一个爪子了。
玛丽照常把早茶放在床上,又把她妈叫醒了,她妈望空愣了一会,用胳膊肘支起她的身子,于是毅然的决心一下,在床中坐起来,竭力把心按她在的早茶上。她一口气喝了两杯茶,但那面包,她往嘴里无味吞了一口之后,便把它放在一旁了。
“我一点不知道这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她说。
“妈也许是着凉。”玛丽回答说。
“我脸色难看不难看,现在?”
玛丽细细端详一下。
“不,”她回答说,“你脸上的颜色倒比平常红些,你的眼睛很亮。我看你的样子很好。你心里觉得怎么样?”
“我不觉怎么样,总是困。你把那面镜子递给我,宝贝,我瞧瞧我什么样子。”
玛丽从墙上摘下那面镜子递给她。
“我脸上一点不难看,带点儿颜色我总是合式的。可是,你看我的舌头,舌苔厚极了;完全是一个坏舌头。玛丽,你外婆临死时的舌头正是这个样子。”
“妈有什么难受没有?”她女儿说。
“没有,宝贝,就觉额前嗡嗡嗡的仿佛有件东西转得很快似的,害得我两眼好累,我的脑袋仿佛有双倍重。把这镜子拿去挂上。我试试睡一觉看,也许醒来能好些,你给出去买点牛肉,我们煮点牛肉茶喝。吃了也许于我好一点。我那裙子袋里的钱袋拿来给我。”
玛丽找着了钱袋拿到床边。她妈打开来拿出了一个顶针,一条靴带,五个钮子,一个六便士的银角子,在外又一便士。她把六便士的银角给了玛丽。
“买半磅腿上的肉,”她说,“还剩下四便士买面包同茶叶,不要这样罢;把那一便士也带着,到肉铺里花二便士买半磅零块的牛肉,买两便士一罐烂炼乳,这是四便士了,还要一便士半的面包,一便士的茶叶,这是六便士半了,再把剩下的半便士买葱,回头放在牛肉茶里,不要忘记了,宝贝,肉要挑瘦的,那伙人们常要搭上几块肉皮肉骨头。告诉他这是给你妈煮牛肉茶的,说我在这里不好过。替我问克文太太好;她好久不到肉铺里来了。我现在要睡觉。无论怎么样我明天总得去作工,因为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快点回来,宝贝,愈快愈好。”
玛丽穿上衣服出门去买这些食物,但是她不马上就买。她到了街上忽然转过来,两手紧握着作一种失望的动作,急急地望那反的方向走去。她转到旁的街上到那公园的门口。她的两手忽而紧握,忽而松放,心里着实不耐烦的样子,两只眼睛不住的东瞅西瞧,在几个过路的人间射来射去宛似两盏灯笼。她进了公园门,走到那条正中的大路,她在这里脚步渐渐的放缓了:她并没有看见栏杆后的花坛,甚至将世界浴在光荣里的日光也没有看见。走到纪念碑前她偷眼瞧了瞧她已经走过的路上——看见没有人跟在她背后。她又转到草地上,在树底下独自徘徊,这些树她也没有看见,连那上至土堆下至土凹的斜坡都没有注意。偶然间,她的零碎的思想中记起她妈病在家里,等着她女儿带食物回去,她这样想起时,便很惊慌的两手紧握在一起,立刻将这念头驱逐了。——一种暂时的念头,她竟会恨她的母亲。
她离开公园时已经将近五点钟。她颓丧的昏迷的走着。在她很熟悉的范围内这里走走,那里走走,走了总有好几个钟点,愈走愈任性愈没有目的了,这时太阳已经下去,一种苍色的薄暮降落到田野里;一阵小风沿草吹去吹得悉悉作响,有的摇动了那些轻细的树枝,使这薄暮生出一种阴寒萧条的景象。她走出大门陡觉寒气侵骨,但是记起她妈来,便急急跑回家去。这时她忘记了在树林里的寻访,一心专想她进屋去的时候她妈必要说什么话,与一场申斥,惊愕的眼睛怎样的瞪她,想起来不免又羞又惧。她有什么话可说呢?她想不出一句来。这样无端的,冷血的,难以解释的疏忽她怎么可以辩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