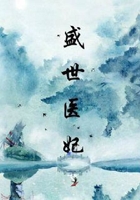他们正争论着,忽然听着一声炮响;炮声越来越大了。他们全拿着望远镜看,在三海里外有两条船正斗着。这法国船顺着风顶对了去,船上人恰好看一个仔细。一条船横穿放了一排炮,平着过去打一个正中,那一条立时就淹了下去,赣第德和马丁看得真切,有一百来人在那往下沉的船面上挤着;他们全举手向着天,高声叫着,不一忽儿全叫海给吞了。
“好,”马丁说,“这就是人们彼此相待的办法。”
“真是的,”赣第德说;“这事情是有点儿丑陋。”
正说着话,他看到一样他也不知是什么,一团红红发亮的,浮着水往这边船过来。他们把救生船放下去看是什么;不是别的,是他的一头羊!赣第德得回这一头羊的乐就比他不见那一百头时愁大的多。
法国船上的船主不久就查明了那打胜仗的船是西班牙的,沉的一条是一个荷兰海盗,强抢赣第德的正就是他。那光棍骗来的大财就跟着他自己一起淹在无底的海水里,就只那一头羊逃得了命。
“你看,”赣第德对马丁说,“这不是作恶也有受罚的时候,这混蛋的荷兰人才是活该。”
“不错,”马丁说;“可是那船上其余的客人何以也跟着遭灾?上帝罚了那一个混蛋,魔鬼淹了其余的好人。”
这法国船和那西班牙船继续他们的海程,赣第德和马丁也继续他们的谈话。他们连着辩论了十五天,到末了那一天,还是辩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可是,成绩虽则没有,他们终究说了话,交换了意见,彼此得到了安慰。赣第德抱着他的羊亲热。
“我既然能重复见你,羊呀,”他说,“我就同样有希望见着我那句妮宫德。”
二十一
这回讲赣第德与马丁到了法国沿海。
再过几时他们发现了法国的海岸。
“你到过法国没有,马丁兄?”赣第德说。
“到过,”马丁说,“我到过好几省。有几处人一半是呆的,要不然就是太刁,再有几处人多半是软弱无用,要不然就假作聪明。要说他们一致的地方,他们最主要的职业是恋爱,其次是说人坏话,再次是空口说白话。”
“可是,马丁兄,你见过巴黎没有?”
“我见过。我上面说的各种人都在那里。巴黎是一团乱糟——杂烘烘的一大群,谁都在那儿寻快乐,谁都没有寻着,至少在我看来,我住了几时。我一到就在圣日曼的闹市上叫扒儿手把我的家当给剪了去,我自己倒反叫人家拿了去当贼,在监牢里关了八天,此后我到一家报馆里去当校对,攒几个钱,先够我回荷兰去,还是自己走路的。那一群弄笔头的宝贝,赶热闹的宝贝,信教发疯的宝贝,我全认得。听说巴黎也尽有文雅的人,我愿意我能相信。”
“我倒并不想看法国,”赣第德说。“在爱耳道莱朵住过一个月以后,在地面上除了句妮宫德姑娘我再也不想看什么了,这话你能信得过不是?我只要到威尼市去候着她。我们从法国走到意大利去。你可以陪着我去吗?”
“当然奉陪,”马丁说。“人家说威尼市就配它们自己的贵族住,可是外面客人去的只要有钱他们也招待得好好的。我是没有钱,你可有,所以我愿意跟着你,周游全球都行。”
“可是你信不信,”赣第德说,“我们这地面原来是一片汪洋,船主那本大书上是这么说的?”
“我一点也不信,”马丁说,“近来出的书全是瞎扯,我什么都不理会。”
“可是这样说来这世界的造成的究竟是为什么了?”赣第德说。
“为苦我们到死,”马丁回说。
“你听了以为奇不奇,”赣第德说,“前天我讲给你听的那两个奥莱衣昂的女子会恋爱两个猴儿?”
“一点也不奇,”马丁说。“我看不出那一类恋爱有什么奇,出奇的事情我见过得太多了,所以我现在见了什么事情都不奇了。”
“那你竟以为,”赣第德说,“人类原来就同今天似的互相残害,他们顶早就是说瞎话的骗子,反叛,忘恩负义的强盗,呆虫,贼,恶棍,馋鬼,醉鬼,啬刻鬼,忌心的,野心的,血腥气的,含血喷人的,荒唐鬼,发疯的,假道学的,傻子,那么乱烘烘的一群吗?”
“你难道不信,”马丁说,“饿鹰见到了鸽子就抓来吃吗?”
“当然是的,”赣第德说。
“那对了。”马丁说,“如其老鹰脾气始终没有改过,你何以曾想到人类会改变他们的呢?”
“喔!”赣第德说,“这分别可大了,因为自由意志——”刚讲到这里他们船到了保都码头。
二十二
这回讲他们在法国的事情。
赣第德在保都没有多逗留,他变卖了爱耳道莱朵带来的几块石子,租好了一辆坚实的马车够两人坐就动身赶路;他少不了他的哲学家马丁一路上伴着他。他不愿意的就只放弃那一头红羊,他送给保都的科学馆,馆里的人拿来做那年奖金论文的题目,问“为什么这羊的羊毛是红色的”;后来得奖金的是一个北方的大学者,他证明A加上B,减去C再用Z来分的结果。那羊一定是红的,而且将来死了以后一定会烂。
同时赣第德在道上客寓里碰着的旅伴一个个都说:“我们到巴黎去。”这来终于引动了他的热心,也想去看看那有名的都会;好在到威尼市去过巴黎也不算是太绕道儿。
他从圣马素一边进巴黎城,他几乎疑心他回到了威士法利亚最脏的乡村里去了。
他刚一下客栈,就犯了小病,累出来的。因为他手指上戴着一颗大钻石,客寓里人又见着他行李里有一只奇大奇重的箱子,就有两个大夫亲自来伺候他,不消他吩咐,另有两个帮忙的替他看着汤药。
“我记得,”马丁说,“我上次在巴黎,也曾病来的;我可没有钱,所以什么朋友,当差,大夫,全没有,我病也就好了。”
可是赣第德这来吃药放血一忙,病倒转重了。邻近一个教士过来低声下气的求一张做功德的钱票,他自己可以支取的。赣第德不理会他;但那两个帮忙的告诉他说这是时行。他回答说他不是赶时行的人。马丁恨极了想一把拿那教士丢出窗子去。那教士赌咒说他们一定不来收作赣第德。马丁也赌咒说那教士再要捣麻烦他就来收作他。这一闹闹起劲了。马丁一把拧住了他的肩膀,硬撵了他出去;这来闹了大乱子,打了场官司才完事。赣第德病倒好了,他养着的时候有一群人来伴着他吃饭玩。他们一起大赌钱。赣第德心里奇怪为什么好牌从不到他手里去;马丁可一点也不奇怪。
来招呼他的本地人里面有一个叫做卑里高的小法师,一个无事忙的朋友;成天看风色,探消息,会趋奉,厚脸皮,赔笑脸,装殷勤的一路;这般人常在城门口等着外来的乡客,讲些城子里****的事情,领他们去各式各样的寻快活。他先带赣第德和马丁到高迷提剧场去看戏,正演着一出新排的苦戏。赣第德刚巧坐在巴黎几个有名的漂亮人旁边。他还是一样的涕泗滂沱,看到了戏里苦的情节。他旁边一位批评家在休息的时候对他说:
“你的眼泪是枉费了的;那女角是坏极了的;那男角更不成;这戏本更比做的戏子坏。编戏的人不认识半个阿拉伯字,这戏里的情节倒是在阿拉伯地方;况且他又是个没有思想的人;你不信我明天可以带二十册批评他的小书给你看。”
“你们法国有多少戏本,先生?”赣第德问那法师。
“五六千。”
“有这么多!”赣第德说,“有多少是好的?”
“十五六本。”
“有这么多!”马丁说。
赣第德看中了一个充一出无意识的悲剧里衣列查白女皇的女伶。
“那个女戏子,”他对马丁说;“我喜欢;她那样子有些像句妮宫德姑娘;要是能会着她多好。”
那位卑里高的小法师担任替他介绍。赣第德,他是在德国生长的,问有什么礼节,又问法国人怎样招待英国的王后们。
“那可有分别,”那法师说。“在外省你请她们到饭店里去;在巴黎,她们看你好才恭维她们,死了就拿她们往道上掷了去。”
“拿王后们掷在路上!”
“是真的,”马丁说,“法师说的不错。我在巴黎的时候孟丽姑娘死了。人家简直连平常所谓葬礼都没有给她——因为按例她就该埋在一个丑陋的乞丐们做家的坟园里;她的班子把她独自埋在波贡尼街的转角上,这在她一定是不很舒服,因为她在时她的思想是顶高尚的。”
“那是太野蛮了,”赣第德说。
“那你意思要怎么着?”马丁说;“那班人天生就配那样,哪儿不是矛盾的现象,倾倒的状况——你看看政府,法庭,教会,以及这玩笑国家各种的公共把戏,哪儿都是的。”
“听说巴黎人总是笑的,有没有哪话?”赣第德说。
“有这回事,”那法师说,“可是并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不论抱怨什么总是打着大哈哈的;他们竟可以一路笑着同时干种种极下流的事情。”
“他是谁,”赣第德说,“那条大猪,他把我看了大感动的戏和我喜欢的戏子都说那样坏?”
“他是一个坏东西,”那法师说,“他是专靠说坏所有的戏和所有的书吃饭的。谁得意他就恨,就比那阉子恨会寻快活人;他是文学的毒蛇中间的一条,他们的滋养料是脏跟怨毒;他是一个腹利口赖。”
“什么叫做腹利口赖?”赣第德说。
“那是一个专写小册子的——一个弗利朗。”
这番话是他们三人,赣第德,马丁,和那卑里高的法师靠在戏园楼梯边一边看散戏人出去时说的。
“我虽则急于要会见句妮宫德姑娘,”赣第德说,“我却也很愿意和克莱龙姑娘吃一餐饭,因为她样子我看很不错。”
那法师可不是能接近克莱龙姑娘的人,她接见的全都是上流社会。
“她今晚已经有约会;”他说,“但是我可以领你到另外一个有身分的女人家里去,你上那儿一去就抵得你在巴黎几年的住”。
赣第德天然是好奇的,就让他领了去,那女人的家是在圣享诺利街的底。一群人正赌着一局法罗;一打阴沉着脸的赌客各人手里拿一搭牌。屋子里静得阴沉沉的;押牌的脸上全没有血色,做庄的一脸的急相,那女主人,坐近在那狠心的庄家旁边,闪着一双大野猫眼珠留心着各家加倍和添上的赌注,一边各押客正叠着他的牌;她不许他们让牌边侧露着,态度虽则客气,可是不含糊;她为怕得罪她的主顾不能不勉自镇静,不露一些暴躁。她非得人家叫她巴老利亚克侯爵夫人。她的女儿,才十五岁,亦在押客中间,她看着有人想偷牌作弊就飞眼风报告庄家。那卑里高的法师,赣第德,和马丁进了屋子;谁都不站起来,也没有人招呼他们,也没有人望着他们;什么人都专心一意在他的牌上。
“森宝顿脱龙克的侯爵夫人也还客气些,”赣第德说。
但那法师过去对那侯爵夫人轻轻的说了句话,她就半欠身起来微微的笑着招呼赣第德,对马丁可就拿身分,点了点头;她给赣第德一个位置一副牌,请他入局,两副牌他就输了五万法郎,接着就兴浓浓的一起吃饭,大家都奇怪他输了这么多却不在意;伺候的都在那儿说:——
“今晚咱们家来一个英国的爵爷呢。”
这餐饭开头是不出声的,那在巴黎是照例的,静过了一阵子就闹,谁都分不清谁的话,再来就说趣话,乏味的多,新闻,假的多,理论,不通的多,再搀点儿政谈,夹上许多的缺德话;他们也讨论新出的书。
“你有没有看过,”那卑里高的法师说,“西安顾侠那神学博士的小说?”
“看了,”客人里有一个回答,“可是我怎么也不能往下看。我们有的是笨书,可是拿它们全放在一起都还赶不上那‘神学博士顾侠’的厚脸。我是叫我们新出潮水似的多的坏书给烦透了,真没法子想才来押牌消遣的。”
“那末那副监背德鲁勃荣的‘梅朗艳’呢,你看得如何?”那法师说。
“啊!”那侯爵夫人说,“他烦死我了!他老是拿谁都知道的事情翻来覆去的尽说!分明连一提都不值的事儿,他偏来长章大篇的发议论!自己没有幽默,他偏来借用旁人的幽默!他简直连偷都不会,原来好好的,都让他弄糟了!他真看得我厌烦死了!他以后可再也烦不着我——那副监督的书,念上几页就够你受的。”
席上有一位博士鸿儒,他赞成侯爵夫人的话。他们又讲到悲剧;那位夫人问有没有这样的戏,做是做过的,剧本可是不能念的。那位博学鸿儒说有这回事,一本东西尽可以有相当的趣味,可是几乎完全没有价值;他说写戏不仅来几段平常小说里常见的情节可以引动观众就算成功,要紧的是要新奇在而不怪僻,要宏壮而永远不失自然,要懂得人心的变幻,使它在相当的境地有相当的表现;写的人自已是大诗人,却不能让他戏里的人物看出诗人的样子;要完全能运用文字——要纯粹,要通体匀净,要顾到音节,却不害及意义。
“尽有人,”他接着说,“不顾着上面说的条件,也能编成受观家欢迎的戏,可是他那作家身分总是看不高的。真好的悲剧是少极了的;有的只是长诗编成对话,写得好,韵脚用得好,此外都是听听叫人瞌睡的政治议论,否则竟是平铺直叙一类最招厌的;再有就是体裁极丑的怖梦,前后不相呼应颠三倒四的,再加之累篇对神道的废话,无聊的格言,浮夸的滥调。”
赣第德用心听这番议论,十分佩服这位先生,他正坐在侯爵夫人的旁边,就靠过身子去问她这位议论风生的先生是谁。
“他是一个学者,”她说,“那法师常带他这儿来,他可不押牌;剧本跟书他都熟,他写过一本戏演的时候叫人家通了回去,又写了一本书除了他的铺子灰堆里以外谁都没有见过,我这儿倒有一本他亲笔题给我的。”
“大人物!”赣第德说。“他是又一个潘葛洛斯!”他转过身去问他说:
“先生,那末你对这世界的观察,道德方面以及物理方面,一定以为一切都是安排得好好的,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决不能有第二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