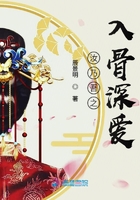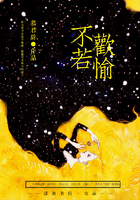终于走到了最尽头,这里面空间格外大。并排凿了两个山洞,右边一个依旧是用铁栅栏隔了,只左边这个是用了玄铁做的大门严严的封闭着,半点也窥见不得里面的情景。
此刻花角正举着火把站在右边的山洞前瞧着,我知道这一路上,她一直在寻着她的表哥。
大胡子和哈焦索站在左边的大门前,我稍稍扫了一眼右边的这个山洞。
尸体。
全是尸体。
我们所能眼见到的范围皆是尸体。
有的肢体不全,全身腐烂。有的已成干尸,全身仅是一副高大的骨架。各种千奇百怪的尸体,也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死法。
我只是略微扫了眼,便再也看不下去了。身边的苏诀浑身紧绷,握着我的手越缩越紧。我痛呼出声,苏诀这才反应过来,松了松手。
我只好拉着他往铁门那去了。
隔着那扇黑黑的厚重的铁门,我甚至能可以闻见那浓烈的血腥味。花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我们的身边,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双眼死死地盯着那扇门。
当哈焦索终于颤着双手将那扇大门推开时,迎面扑来的腥臭味差点让我窒息。我站在门口,清清楚楚地瞧见了里面的情景,苏诀直接跑到了一旁呕吐起来。大胡子站在门边,双手握紧成拳,湛蓝的眼都参了几丝血丝。
一个不大的山洞,里面的置物都十分简单:一个可以容一个强壮的成年男人全身躺进去的血池,一床同等大小的可以让人躺上去的台架,台架旁边有着一个类似衣架的挂子,上面现在正挂了大小不一的刀具,铁棍,各种我从未见过的铁制成的工具,现在这些工具都被鲜雪浸泡得发红了。在血池的正前方有一个用来捆人的十字木架,架子旁边有一个内嵌的锦盒,锦盒里是各式针刺,还有一颗可以用来照明的夜明珠。
身边的花角快步往前面走,突然她身子一软,似再也站不直,一步一步艰难地往里头走。我看着,也跟着她进去了。
这时我才真正看完整这整个山洞,在山洞最阴暗处似还有个池子,我是看不清里面是些什么。又转眼看到了离门不远的一个角落,只是稍稍地扫了眼,便立马收回。
那里有大半个人的脑袋,还有似乎是人的断肢。
哈焦索自进来后,便慢慢地往山洞里头去了。反正他也是待在着个山洞的,我这时倒也不再关注他,只看着安静祥和地让人心生异样的花角,心中不安。
血池正泡着一个人。
花角直直地走到血池旁,将手中的火把靠着血池,蹲下身去,小心伸手,将泡在血池里的那个人的上半身自鲜血里捞出来。
是一个没了大半边脑袋的男子,右边的手臂已经长出细鳞,只左臂自肩膀处就没了。
花角面带无措,抬头看了我,嘴唇微颤,似要和我说什么,但看见我一脸愧疚地摇头,表情扭曲奇怪地又低头去看怀中的男子。她抬着小小的手,顿在半空中,竟是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去将男子半边脸上的血污擦去。良久,花角方才颤抖着将手落到了男子完好的左脸上,动作轻柔地一点一点将男子脸上的血污拭去,露出有些苍白的皮肤来。
大胡子和我皆静立在门边,看着这个孩子模样的女子将浸在血池里的爱人一点点地往自己身上搂,她搂地那样小心翼翼,好几次因男子身上的血污而滑手抓不住他。
花角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男子的脸,眼泪就那么一滴滴地落了下来,滴到了男子惨白的唇上。
这半日,我见过花角的许多面,见到她的各种哭,却再无一种可以让现在的我觉得莫名心疼。
这是一个心狠聪明的女子。她懂得利用别人的心软来达到自己目的,她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柔软得如同一个平常的娇软弱女子,将人玩转于手心,也可以在转眼之间,毫不心软地将敌人斩杀。在别人的面前,她如此善变,阴狠得如同一条潜藏以待的毒蛇!
也只有这刻,我才真正瞧见了这个为了生存缩身成孩,心却比任何男子还要狠厉的女子最真实的一面。
我看着她,真是不能相信世间竟然会有这般坚强的女子。
她轻轻地将男子的半边脑袋怀进怀中,小心地将自己的唇印到男子的唇上,毫无俗世女子的矜持和羞涩,只有绝望和哀伤,她吻着他,用尽了自己所有力气,深情而绵长。她脸上的表情让我瞧不见她正经历着与爱人的生死离别,她所有的动作都仿若她只是在和怀中之人进行着一场淋漓的缠绵。
一吻之后,她将头俯在男子的颈边,开始低低啜泣起来。那声音只有浓浓的悲意,再无幻想。
我想世间最坚强的女子也不过如此了:接受爱人的离开,并且以全心的悲伤来承认自己对着他的爱意。清楚地明白,一吻过后,便是再也无法相守白首了。
她在哭,祭奠她此生第一份爱情,祭奠她此生最后一份爱情,祭奠她生命中唯一的寄托和依靠。
我听着她的哭声,心中只想着:我幕君何其有幸,得以遇见这么一份爱情。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到其中最真挚的情感。我默默又叹了一口气,这哭泣声,自此听后,便再无爱情了。
“你们为什么要破坏魔君的大业?!哈哈哈!魔君万岁!魔君万岁!”走到山洞最里头的哈焦索忽而哈哈大笑。我和大胡子这才回过神来,暗道一声不好,却见哈焦索站在十字木架旁,见我们皆看向他,他这才大笑着伸手猛地将那内镶的锦盒用力一推,那锦盒转了方向,整个山洞便开始颤抖起来。
哈焦索仰天长笑,状若癫狂。我欲去拉坐在血池旁边的花角,却不料她是一动不动:“你疯了吗?洞要塌了!快和我们走!”
这时一直在门外没有进来的苏诀也冲了进来:“发生什么事了?”话音刚落,又见着花角一身鲜血,怀里抱着一个只有半边头的残尸,顿时又受不住了,捂着嘴跑出去了。
大胡子一直站在门口,只双眼焦急地瞧着我。我一拉拉她不动,又听见那哈焦索疯狂大喊道:“你们!你们哪都去不了!你们!要死在这里!死在这里以平魔君之怒!”说着又从支架上抽出一把大刀锐利地朝我刺来。我手里正半拖着花角,哪里分得出身来避,正这时,我抓着的花角一使巧劲,便从我手中挣脱,直直扑向满脸狰狞的哈焦索!
哈焦索一时不备,被花角扑了个正着,两人齐齐地朝着山洞的最里边的那个池子摔了进去,下一刻,整个山洞便响起了哈焦索癫狂的嘶吼声,我转眼去看,便看见躺在下头的哈焦索身上沾满了不知名的液体,浑身冒出黑色的烟,整个人都疯狂地在那个池子里挣扎哭喊,花角扑在他身上,竟又被他的无意识挣扎给甩出了池子,落在了离血池的不远处。她见我还欲朝她跑去,被腐蚀的喉咙几是嘶哑地疯狂叫喊出声:“快走!快走啊!”
我这边还在犹豫,身后一只大手将我拦腰抱起,抗上肩就往外跑。
我的眼泪就这么掉下来了,模糊间,我看见在那个幽暗的山洞,一把正在幽幽燃着的火把照着花角的被那池中东西毁去一大半的脸上,她趴在地上,脸上带笑,一点点地去够男子落在血池外面的生了细鳞的手。我还欲看,只是一眨眼,那个山洞便轰然塌下,将那个叫花角的女子和她的爱人掩埋在了一处,将那个山洞里哈焦索哑得几不可闻的声音,以及一切一切的不堪都尽数掩去。
这是我见到的花角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