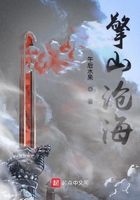我直视他,也不管他是不是会在心里觉得我恶毒,反正他也一直这么想的。他能如此坐视我而不理,有一回就会有第二回。
他在犹豫那么久之后才选择救我,我也能说服自己不怪他,毕竟那也关乎他的性命。但我不能原谅他本已在姥姥面前尊我为主了,却如此不将我放在心上。大不了他就和姥姥说去,让姥姥将他送下山去,这定雪山本就该是孤独寂寞的,有姥姥,雪兽和我也就够了。
梅开不知在想什么,我挣扎着就欲从他怀里起来,却又被梅开用手压住,他伸手探上我的脉搏,好一会儿才松开。转头神色凝重地问我:“珑主知道吗。”
我轻笑,“姥姥当然知道,不然你以为这世间还有谁有如此医术可以救我这将死之人?”
“内功被封,体内各路气息夹杂紊乱。”梅开皱着眉头道:“你身体怎会破败至此?我也只是听闻你是被银卿一剑穿心后又被珑主接上山,照理说不应该是这种脉相啊。”
我冷笑:“你听说,你听说,全是你听说。你可又听说过:‘以理听言,则中有主’我瞧你也是个不清醒的。”
梅开面上一黑,手扶到我的后腰:“你刚刚就这么走过来的?”他掌中输来的内力渐渐将我衣裳都烘干了,也将我胸口的郁气疏散开来。
我淡淡扫了他一眼道:“只这一回,你既已尊我为主了,就把自己的有些想法给我丢一边去,若有下回,不必姥姥,我自会送你下山的。”
他不再说话,良久,方才点头。又一把抱起我,我连忙环住他脖子,抬眼便看见他那精致地下巴,我顿时浑身僵硬,他低头看我:“怎么了?不舒服?”
我别过脸去,不自然道:“没,只是第一次被人抱,不习惯。”
梅开薄唇一勾:“大了自然就不能随便让人抱了。”他走得很快,就算是抱着我也不见半点不稳。
“自我记事后,也没人抱过我。”我的身子渐渐不那么僵硬了,便将头靠在梅开肩上:“她们都不爱和我玩,也不愿亲近我。我曾和我的三姐幕麒玩,因年幼尚不知控制力量,差点将幕麒的右手弄残,娘亲知道后便将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许我再出去了。”我说着说着又笑了起来。
“但她哪里知道,就那扇门,我一巴掌就能把它给劈了。但我不敢,我怕劈了一次后,娘亲会把我关到石屋里去。听身边的嬷嬷说过石屋可小了,连扇窗也没有,那石头又硬又臭,连只蚂蚁也爬不进去。还听她说里面关了好多武林高手,他们逃不出,很多就被闷死在里头了。我怕极,只好听娘亲的话整日整日待在屋里。现在想起便觉的好笑,那些武林高手哪是说抓就抓,说关就关的呢。我后来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娘亲才准我出去上课,但她要求我一下学就得回屋,不准在外逗留。我便是在那时认识的银卿,银卿从小就长得好,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总围在他身边叽叽喳喳个没完。可是我总是不敢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走到他身边和他一起玩,因为我怕伤着他,毕竟他那样像一尊玉娃娃,大概我一个不小心就会把他弄碎了。”
梅开听得认真,走得也越来越慢了,我也无意催促他,头发和棉衣早已经干了。也不觉得冰得难受了:“等我五岁开始向师傅们学武时,便开始经常性地呕血,性子越来越来暴躁,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将这一切告诉了娘亲,娘亲听后只让我莫要伸张,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我自是听她的话。却不曾想长到了我八岁上,我得了嗜睡症,有时干着别的事也会不自觉地睡去了,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不同的地方,再后来便有人说我干了怎样怎样的恶事。我只当有人在诽谤冤枉我,心想清者自清。事情越来越严重,我也察觉到不对了。直到后来那个侍女的死,我看到自己的金鳞鞭上沾了血,这才慌了神,可是晚了。我被父亲喂了散功丸,关进了小石屋,这一关就是五年。我至今还记得那间石屋,狭小、寒冷、黑暗。起初我也哭过闹过,也用我天之神女的身份要挟过,可没有人,真的没有人,仿佛天地之间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说着说着嗓子就哑了,感觉梅开抱着我的手越收越紧。
“开始我怕的时候就给自己唱歌,再后来怕自己忘记怎么说话就自己和自己聊天,到最后我不能说话了,就用手指去敲石壁,听那种沉闷的声音。父亲也不敢真正弄死我,每日都会有人给我送饭,但慢慢地变成了两日送一次,三日送一次。”
说到这里时,已经到了竹屋了,梅开径直将我抱入姥姥的屋里。进了里屋,将我放到床上,用被子裹上。又倒了杯茶水置于手中温热后递给我,我也不去接,只满眼期待地问他:“还要听吗?我想继续讲。”这么些年了,他是第一个愿意也是真正地听我讲的人了。我从来不和姥姥讲这些,但我知道她知道。
梅开挑眉,收回手,捧着茶杯走到窗子旁边的一张竹椅上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