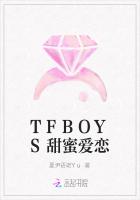张雱和夜紫夕急驰至大理寺监狱,已有一名探子在倚门翘首,等候多时,看见张雱跟看见亲人似的,“您可来了!快进去吧,狱官正在劝夜侯爷呢,也不知劝不劝得住。”一路唠唠叼叼的,带着二人快步向牢房而来。
牢房内,狱官紧皱眉头,强忍心头怒火,好言好语劝告夜子城:“有什么,您只看在我面子上,且放他一马。”监狱中人犯突然死亡的不是没有,通常报个“病亡”上去便罢了,也不算什么大事。可是这位安大人日日有人探望,狱官、狱卒哪个没收过好处?既然有人这般费心下力气打点,显是外边还是有家眷亲人眼巴巴看着呢,这时候哪敢真出事,真出事了谁兜得住?
夜子城冷冷看了狱官一眼,看你面子?一个小小狱官,你有什么面子?回头对着安赞暴吼一声,“快说!我女儿在哪儿?”手下到底是放松了,他还想要从安赞口中得到紫夕的下落,也不能真让安赞死了,安赞真死了他还怎么去找到紫夕啊。
狱官慑于夜子城的威势,只敢说些软和话开解;又见夜子城松了手,安赞没有生命危险,便也不深管。张雱和夜紫夕匆匆进入牢房时,见到的这样一幅情景:夜子城抓着安赞逼问,安赞呼吸不顺畅,满脸痛苦;狱官在旁干看着。
“住手!”夜紫夕大喝一声,跑过去用全部高级修士巅峰的幻力将夜子城的手狠狠地击中了一下,夜子城吃痛,举起被咬出血的手指着紫夕说道:“你这丫头,这样地不懂事!”父女二人头回见面是劫持亲爹,第二回见面是对着亲爹的手便一击,这是女儿还是仇人?
张雱塞了个锭金子到狱官手中,“劳烦,叫个狱药师,要快!”狱官摸摸手中沉甸甸的金子,点头哈腰道“成!成!”急急奔出去叫狱药师了。
牢房内,夜紫夕把安赞平放在地上,替他顺着气,眼泪流了满脸,“爹爹您怎么了,您别吓我。”看安赞脸色、嘴唇发青发紫,心中恐惧: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夜子城的脾气一向暴燥,抬起手就要打紫夕,手挥到半空中又停住了,紫夕小孩子家懂什么,都是被安赞这厮教坏的。要算账跟安赞算,老子不能打自己的亲亲闺女!张雱在旁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他,唯恐他对紫夕不利。见他脸色变来变去,手终于放下了,张雱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探子立马带着狱药师走了进来。狱药师是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不慌不忙的诊过了脉,施了针,“莫哭了,他死不了。”老者看着泪流满面的夜紫夕,慢吞吞说道:“好好养着罢,他这身子骨,还能活个二三十年。”收拾好药箱,施施然走了。夜紫夕和张雱深深施礼道谢,他连头也没回。
狱药师回到自己官署,闭目养神,静静地想着:这安赞听说是因得罪杨首辅而入狱,如今六安侯、靖宁侯府的人都招来了,背后究竟有何隐情?此人,能不能为我所用?
外面有脚步声传来,狱药师警觉的睁开眼睛,听得来人笑道“胡药师在么?于大人有请。”一边说着话,一边掀开门帘走了进来,狱医胡大夫见来人是大理寺卿于靖的贴身小厮来安,微笑道“正要拜望于大人。”跟着来安去了大理寺正堂。
于靖向有“于青天”之称,他一则是于刑名之事极有天份,破获不少大案要案奇案;一则是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在清流士林中很有威望,虽然杨首辅权倾天下,对于靖这样不攀附不同流合污的人颇为不满,无奈连深宫的皇帝也知道大名鼎鼎的于靖于青天,杨首辅倒也不敢轻举妄动。
胡药师进了正堂,见过礼,于靖待他极是客气,温言询问了狱中犯人“可有病、伤?可有受过虐待?”胡药师一一据实答了,“有无依无靠没有家眷照顾的,狱卒未免有些苛待,却也不曾太过;有贿赂过重金的,便将养的极好。狱中无甚重病、重伤、受虐之犯人。”
于靖微笑问道“如此,哪位是贿赂过重金,将养的极好?”听说是御史安赞,于靖沉吟片刻,没有再问什么,客客气气命人送了胡大夫出去。
看来,狱中倒还清明。于靖伸手拿过案头的卷宗,一宗宗翻看,翻到安赞时,停顿许久。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人下到诏狱,是当今权贵之徒常做的事,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人下到大理寺,可就少见了。这安赞,卷宗上只写着“触动圣怒”,这让人如何审理、定罪?于靖长叹一声,将卷宗放起,独自在室中踱起步来。
如今朝中形势,越来越不堪。圣上贪恋长生不老之术,镇日集结一帮江湖术士练丹药,已有十几年不上早朝,自己这正三品的大理寺卿,一年里头能见着圣上两三回面便算不错了,一年到头见不着圣上一面的朝臣,大有人在!
这些都还不算,还有更要命的事情:圣上年近五旬,只有两子,煌王居长,为宫女所出;晋王居次,为刘贵妃所出。二王既全不是皇后嫡出,自然该立长,偏偏圣上宠爱刘贵妃,意欲立幼子。事涉立储大事,满朝文武皆上书“不可废长立幼”,圣上虽面上依了群臣,却拖着不立储,煌王地位尴尬,群臣惶惶。其实煌王的修为比晋王多一大阶,又是本朝第一天才,要知道现在的煌王才十六岁就是大修士这已经名留青史了,后期成长起来到修神也不是不可能。
龙渊峡谷、凤渊峡谷、白霞山、夜霞山匪患迭起,近几个月来攻州府,朝廷派出能片惯战之将帅征讨,竟全部兵败于盗匪!这其中,有什么蹊跷?近日以来连京城也是治安越来越差,离奇案件一件接着一件:北城兵马司指挥高德,酒后溺毙荷花池中;府军前卫指挥使杜离,深夜死在名妓柳青青的床上;五军都督府中军参军卢知味,在自家宅院前被一流浪汉棒杀,流浪汉早已不知所踪。虽然他们所有人都是七阶高级修士了,但是杀他们的实力必须在大修士以上,可是本朝的大修士本来就不多,看来杀他们的后台实力估计也很恐怖,还是少惹为妙。
于靖思及近来京城中几件连环案,越想越觉心惊:圣上只顾在宫中修练长生不老,可知藩王中有多少人已是蠢蠢欲动?这几起案件明打明是直接对着执掌兵权之人下手!可叹宫中竟似毫无察觉一般。
这几起案件,如今都着落在大理寺。自己破案不难,难的是破案之后,若发现背后是皇族中人做祟,又该如何收场?证据稍有不足,便会被冠上“离间皇室骨肉”之罪名,万劫不复。于靖想至此,又是一声长叹。
说来是清名满天下,只是,清官,哪是那么好当的。
胡药师回到自己官署,看了会儿医书,写下一个药方交给小童儿,“送去给东城兵马司的金家,跟金家说,这方子对症,能治他家老太太的顽疾。”小童儿清脆利落的答应了,小心收好药方,去了兵马司胡同。
于靖此人,一定能为我所用!胡药师笃定想道,还有安赞,两榜进士,素有清名的御史,也是可用的,他又与当今这些权贵有仇隙,很是可以拉拢拉拢。只是不知,他和六安侯究竟有何冤仇?六安侯可是王爷要笼络的要人,念及此,胡药师略略皱眉,这可有些难办了。
牢房中。
“你家的亲老子好好的,哭什么哭!”夜子城见紫夕流着眼泪在安赞身旁精心照顾,对自己却是看都不看一眼,心头怒火噌噌噌往上窜,“亲爹你不管,为个不相干的人掉眼泪,你这不孝的丫头!”
夜紫夕擦干眼泪,冷笑道:“把养育我六年的父亲视作‘不相干的人’,也只有夜侯爷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才能说出这样冷酷冷漠的话!”安赞精神略好一点,少气无力说道:“不可如此,紫夕,他是你生父。”忤逆亲爹,那怎么成。
紫夕低低应道:“是,父亲。”夜子城在旁暴跳如雷,“老子不领你的情!”一头抢走我闺女,一头还说这太平话来气人!狂怒之下,又抓住安赞要行凶。
夜紫夕清清冷冷说道“打晕他!”张雱早就等着了,顺手拿起一方砚台砸在夜子城后脑勺上,夜子城盛怒之下哪有防备,竟被他得手,砸晕了。
“放心,我有准头儿的,他没什么事。”张雱见夜紫夕低头察看夜子城的伤势,以为她还是担心生父,忙忙的解释。紫夕似笑非笑抬起头,“大胡子,你武功和幻力虽然不太好,做这些事倒是很在行。”张雱俊脸微红,含糊说道:“我武功和幻力也就还过得去了,不算太差,不算太差。”
岳霆穿着飞豹武官服饰,狱官、狱卒都有眼色,知道这是三品、四品武官才能穿的,又见岳霆气宇轩昂,打赏丰厚,殷勤陪着走了进来,任凭岳霆寻找“舍弟”。
此时岳霆站在牢房门口,心头微晒:他自然在行,八岁的时候他就干过这些事。
安赞哑着嗓子叫道:“紫夕!”紫夕笑咪咪地凑了上去说道:“爹爹您放心罢,他什么事也没有!真的没有!”见安赞还要开口说话,忙拦住他,“我都知道了,都知道!您还不知道我么?最孝顺最听话了!您安安心心歇息,我有分寸。”一边甜言蜜语,一边拿过安神汤,哄着安赞喝下,其实这安神汤紫夕放了上古洗髓丹,这丹药可以帮助爹爹恢复曾经的实力又可以排除杂质,看他睡着了,紫夕这才转过头,不怀好意的看着夜子城。
“要不,咱们把他绑起来,逼他放出伯母?”张雱和夜紫夕一起蹲下来看着夜子城,在一旁出主意。紫夕笑吟吟地说道:“我看行!把他绑起来,押到六安侯府,看夜家放不放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先把谭瑛救出来再说。夜汝绍白天跟几个小孩疯玩,倒是开开心心的,晚上常吵着要娘,紫夕被他吵得头疼。
六安侯府?夜家?岳霆皱眉地偷听着,无忌怎么惹上夜家了?见张雱真的探手入怀要取绳索,叹了口气,“无忌,这是大理寺监狱,你莫在此胡闹,快跟哥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