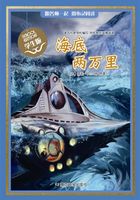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时间在神仙那里停滞不动,日子在庄稼人锄头下过得飞快。紧张忙碌的麦收过去了,晚茬也钻出了地面。前几天下的那场透雨,用田大明白的话说,是《水浒》一百零八将,坐头把交椅宋江的绰号:及时雨。那些晚茬播种的高粱苞米秧苗,如逢甘霖很快疯长起来,不几天黄灿灿的麦茬地就淹没在一片绿色之中。庄稼人一颗皱巴巴的心熨帖了,眉头也舒展开来,把一脸老褶拉平,荡出笑来。
节气已进入大暑,到了一年里最热的时候。日头从滦河岸边杨树林树梢上一冒出头来,天就像下火一样。这样的日子,庄稼人除了一早一晚到责任田里转转,剩下的时间便躲在家里落乏。到了晌火也有了城里人午休的待遇,稳稳当当躺在家里歇晌。
外面像火炉,屋里则像蒸笼,热得让人腻歪。男人先光了膀子,又甩掉裤子,身上只留一个裤衩。女人也脱去了外衣,一件松松垮垮的背心上,透出两个黑枣样的东西。还是有汗冒出来,身上一个个毛孔像是变成了一个个小泉眼,要时不时拿湿手巾在奶子下、后背上去擦。后来终于烦了,也学男人的样子光起了膀子。反正在自个家里,反正在自个爷们儿面前。不想惊动了男人的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像是第一次发现自家娘们儿身子这样白,奶子那样暄。忽然想起,这些日子只顾了在外面责任田里收麦抢荒流汗劳作,忘了在屋里的责任田里下犁播种。心里就火烧火燎按捺不住了,走过去抱麦个子样把女人抱到炕上。女人刚开始还扭捏,还嫌那一身臭汗,却禁不住撩拨,很快软在男人的胳膊弯里,闭上眼睛细着嗓子猫叫一样哼起一支曲子。不知是给外面树上的老哇哇听,还是在为男人加油。
庄稼人就是这样,忙时累个贼死,闲时闲得哼哼。三和尚田自高光棍一条,没有这份快乐。他那个“庙”里又太闷热,放下饭碗,拍拍肚皮,把一条湿手巾搭在脖子上,趿拉着一双破鞋片出了家门。一个人过日子也有好处,他那张饭桌一年也不收拾几回。一双筷子,一只碗,一个人用,刷不刷无所谓。只是夏天麻烦点,要用一块蚊帐布做的罩子盖起来。
晌火歪的日头,像红脖子绿身子长虫吐出的信子让人望而生畏,像无声甩下的鞭子抽在身上疼,田自高光葫芦脑袋上很快冒出了一层汗珠。
村街上见不到几个人影,安静得放个响屁半个街筒子都听得到。村头田大明白说发生过强奸案的麦秸垛下,卧着几只鸡和一条狗。平时它们是不能和平共处的,现在却躲在麦秸垛阴凉下相安无事。几只鸡斜着身子在地上扑噜出个坑来,不时变换着姿势,想借助潮湿的泥土降低体温。狗在这方面没鸡聪明,只会趴在地上把舌头耷拉出老长,拉风匣样忽扇着肚子,像是只有这样才能把五脏六腑里的暑气扇出来,那样子别说给主人看家,就是端了它的老窝,也顾不得吭上一声。这些鸡和狗,对跟它们一样沦落街头的田自高,没有一点同情心,甚至不愿多看他一眼。
出了村头,田自高朝滦河大堤上一棵老柳树走去。那儿高燥通风,有老柳树影投下的一片树荫,是田自高夏天里歇晌的老地方。
走上滦河大堤,几个秃小子跑过来,围住田自高要他帮忙套老哇哇。田自高在一个个小脑瓜上弹个脑崩儿,继续往前走。几个秃小子想起看过的电视剧《济公》,不知谁带的头,站成一排跟在他身后晃着脑袋唱: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酒肉穿肠过。
田自高听秃小子们唱,反倒学起济公走路的样子,几个秃小子越发开心,跟在后面扭起来,那情景如同一个大和尚带了一群小和尚走在化缘路上。
来到老柳树下,田自高选择一块平整地方刚要躺下。几个秃小子这个拉胳膊,那个拽腿,仍要他去帮忙套老哇哇。
去去,一边玩儿去,洒家要睡觉啦!田自高挥手哄孩子们。秃小子们却不依不饶,说不套老哇哇,甭想睡觉。田自高平时和孩子们耍笑惯了,知道不想个办法把他们打发走,这个晌火觉就睡不成。他用手在胸脯上搓一阵,搓下几个泥卷儿后想出了办法,问,你们都上学了吗?
上啦!秃小子们一起回答。上几年级啦?
一年级。好,现在我要考考你们是不是好学生!田自高站起来,两手下垂,劈开双腿问,这个念啥?几个秃小子眨着眼,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没人回答。
一群小笨蛋,这不是“人”字吗?田自高把两条胳膊伸平说,再看这个?这回秃小子们明白过来,异口同声喊:大——田自高两腿并拢,两条胳膊斜着伸向身体两侧。秃小子们研究一阵,看不出像个啥字。玉珍儿子多多也在其中,说,我看这个像飞机。
田自高说,刚才说你们是小笨蛋,这一会儿成小笨笨蛋了!这个是“小”,大小多少的小……多多说,不对,小是竖钩两边一点,你那钩呢?田自高一只脚在地上拍拍,翘起脚尖说,这就是那“钩”。秃小子们一起笑了,喊,再变、再变!田自高说,这是我发明的“大小人体操”,现在你们站成一排,听我的口令,从“人”字开始,把这几个动作连起来,我说大,你们把身体摆成“大”字,说小变成“小”字。说完,又连蹦带跳做了几次示范。
几个秃小子被这游戏吸引住,觉得很好玩,在田自高“大人小人,小人大人”口令指挥下跳了起来,不一会就跳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最后一个个跌坐在地上,再也跳不动了。
田自高见状问,你们热不热,都出汗了吗?秃小子们回答,热,出汗啦!田自高挥挥手说,现在去滦河里凉快凉快,洗澡吧,我要睡觉啦!秃小子们仍不肯离去,围住田自高问这“大小人体操”还能变啥字。田自高想想说,好,我再考你们一下,大字上面加一横念啥?
天!那顶破天呢?
秃小子们用手在地上划拉一阵,猜不出这个字。田自高说,顶破天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夫,你们长大了都是男子汉,记住男子汉不光要顶天立地,还要顶破天!多多抢着说,大字下面加一点,念太!
田自高说,对,对,还是多多聪明,又问,你们还记得大字是啥样的吗?几个秃小子争前恐后爬起来,把身体摆出大字的形状,田自高伸手拉下多多的裤衩,指着他的小鸡鸡说,这就是大字下面那一点。多多臊得脸通红,几个小伙伴则笑弯了腰,田自高招招手说,你们都过来,让我看看有没有这一点。秃小子们听到这话慌了,一个个夹紧小腿,撒丫子跑到滦河边,扑通扑通跳到河里打水仗去了。田自高望着秃小子们的背影笑了,脱下一只鞋当枕头垫在脑袋下,架起二郎腿舒舒服服躺在树荫下。老柳树上有很多蝉。蝉是学名,城里人和文化人的叫法,有好多种,庄稼人分不清它的类别,根据叫声叫它们老哇哇,唧留和唧唧。老哇哇个头最大,长得像京剧里的黑头,但它只会哇哇唱一个音调,如同舞台上黑头发脾气。唧留长得清秀,它的翅膀带有绿色,像透明的纱,“薄如蝉翼”的“蝉翼”指的就是它的翅膀。它能发出两个音节,喜欢孤芳自赏,常常在傍晚或清晨万籁俱寂的时候,独自飞到谁家窗棂或电线杆子上突然唱起来,声音婉转而美妙。唧唧则生得小巧玲珑,像老哇哇的孙子辈,声音也是细嫩的,唧——唧——拉着长音像是有着诉不完的委屈。这些声音在别人耳朵里是噪音,在田自高这里却像催眠曲。
往日躺在老柳树下,听着这吵吵闹闹的叫声,田自高用不了几分钟就会响起一串呼噜。然而今天躺下后,田自高架成二郎腿的脚上挂着的破鞋片一直晃动着,像是在和脚后跟打呱哒板。
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的田自高睡不着觉了,有了心事。昨儿个后晌,乔立新找到田自高,把一个小布包扔在他面前。田自高打开一看,是他想给玉珍包扎伤口时撕破的那件布褂子。乔立新绷着脸等说话,他却东张西望一直不开口。乔立新问,你是不是还恨着玉珍,恨她当年嫁给了那个煤矿工人?
听乔立新这样问,田自高盘腿打坐说,气也气过了,恨也恨过了,我这和尚虽没有去参禅悟道,在这破庙里也修炼得脱俗了,阿弥陀佛!
乔立新说,三和尚你别装神弄鬼耍活宝,还脱俗啦?我看你就是“文化大革命”时说的那地主老财,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看人家腿上流血了,把布褂子都撕了,还想去找伤口。
田自高闭上眼,双手合掌说,施主善哉,善哉!乔立新把嘴都气歪了,说,你是不是嫌玉珍是个寡妇,还想找个黄花闺女?田自高越发逞起强来,说,此言差矣,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分男女,何况寡妇与大姑娘乎?你这个花和尚就装气迷、端架子吧!正儿八经告诉你,玉珍那边可是有好几份提亲的,你掂量着办吧,这也是那个最后的通牒!乔立新说完甩手走了。玉珍回到村里时间不长,乔立新就来找过田自高,想从中牵线让他俩破镜重圆。当时他的心也动了下,但是看看这个家,想想自个的样子,很快又平静下来,说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然而这个麦收,他的心活泛起来。
乔立新走后,田自高打量起那件布褂子。见原本脏兮兮的布褂子洗得干干净净,有一股淡淡的香皂味,撕破的地方已用细密的针线缝好,丢掉的扣子也定上了新的。田自高发一阵呆,突然明白过来,乔立新刚才是来说正经事的,他却只顾开玩笑耍活宝,错过了机会。这让他后悔得拍完了光葫芦脑袋,又嘬牙花子。
这事还真是怪,不想的时候一点事也没有,一想起来就像灶火坑里迸出个火星儿,一下点燃起满灶膛的火。田自高被这火烧着,昨儿个黑介在炕上烙了一宿饼,后来想着乔立新那句,玉珍那里有好几份提亲的,这是最后的通牒!他竟紧张和害怕起来。现在田自高心里想的还是这句话,这事是真还是假?玉珍那里到底是个啥态度?他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办法,去乔立新那里掏个底儿,请这个喜怒冤家从中帮帮忙,并打定了主意,歇完晌就去找乔立新。
有了行动方案,田自高心踏实了些,也就在老柳树上老哇哇声嘶力竭的叫声中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