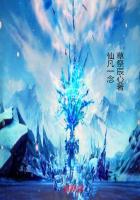第三十五章月下的狂舞
夜已深,风渐冷,人却未眠。
没办法,受伤的野兽在黑暗的长夜总是不敢入睡,它们总在时时刻刻戒备着,不敢有丝毫松懈,假若那根神经放松了,那么它们就会在下一刻成为一具尸体。
他此刻浑身无力,连手指也难得动一下,全身的骨头犹如发面团,整个人斜躺在冷硬的床板上。
他的眼睛紧闭着,但这绝对不是意味着他已经沉落在了睡眠的沼泽,不,这时他最不能睡觉的时候,他仅仅只是不想让眼前那盏孤灯的黄芒刺痛自己的眼睛而已。
既然害怕光芒,何以还要点燃灯火?
这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被碾碎了的幽灵还在半空中飞舞,他不得不点燃一盏灯,发出一点可怜的温存,一面自己被彻底冻僵,热度还不能太高,因为那又得灼伤了这些原本应该呆在另一个世界的幽灵们。
他的身体蜷缩着,瑟瑟发抖,承受着致命的低温,仿佛被置身于冰河时代的万古冰窟之内一样,但是更加诡异的是他的额头还在滴落汗水,好像热到不行,又像是被扔进了桑拿房那样。
冰火两重天,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矛盾天下无人可以改变。
只能承受。
他的舌头忽然伸了出来,舔了舔那干燥的开裂的嘴唇,那里的表皮现在和他的脸色一样,苍白如雪,唯有他的眼睛四周,红得像块烙铁,病态的红。
他忽然弓起身来,像条野狗也似得猛然咳嗽起来,左手迅速探出,抓住桌子上的一壶烈酒,粗鲁的狂饮起来,酒壶空了,他又像丢垃圾一样把酒壶扔到地上,这样的酒壶地上还有许多,桌上也还有许多,但是他之所以喝酒不是因为他喜欢喝酒,他之所以喝酒是因为他需要酒里的温度,这些酒其实也是密室的上一任主人留下的。
他嘴唇紧闭,鼻子里猛然突出一口气,成一条长长的白线,一股炽烈的火苗窜进肚子里,灼伤他的胃,又成为一个火炉,温暖了他的躯体。
呼!
舒服多了,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
眼前的景象乏味单调,一盏黄黄的孤灯,四面灰色墙壁,一张布满灰尘的桌子,地上扔满了各色酒壶,除此之外,没别的东西了,还有就是他身下冷硬的床板。
这是一间封闭的密室,一间谁也进不来的密室。
四周皆是由坚固的巨大石块砌成,固若金汤,将整个世界排除在外,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冷寂的空间,阴冷犹如墓穴。
但是只有这样的密室才会令他感到安全。
每一个丛林中的野兽在受伤时总是会寻找与世隔绝的角落呆着,它们必须这样,因为它们知道丛林里有太多的危险,很多人都在时刻窥伺着,随时准备咬断它们的喉咙,要想不被伤害,要么伤害别人,要么远离别人,这就是丛林。
这时他忽然艰难的翻了个身,全身随着他的动作发出剧烈的疼痛,但这似乎完全不能使得他的眉头皱一下,他已经习惯了,事实上他的全身无处不在疼痛,尤其胸膛那里的剑伤,由于长时间不清理已经开始发出腐臭,发出钻心的疼痛,十八道密密麻麻的切口笔直的倾斜,深可见骨,这些全都是由一把剑造成的,想起那把剑,他的目光忽然向上抬去,看向他的头顶上空的位置。
一道漩涡悬挂在那里,一道光柱从那个地方垂落下来,笼罩在他身上,而他就像一个在在石头下等着水地下来的口可得要死的人,每隔一段时间,总是会有一股阴寒的能量像液体从光柱中流下来,然后又在他的头上变成一个个光点,最后消失在他的身上,像光芒消失在黑洞之中一样。
这些能量原来属于一个个生灵,它们原来乃是虚无飘渺的灵魂,等到这些生灵死去之后,它们就会像摆脱坟墓一样摆脱肉体的束缚,然后进入另一个世界,踏过忘川河上面那座桥,忘却前尘的悲喜,从头再来。但是现在,它们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一道大阵像磨盘一样粉碎掉它们意识,最后以一种极低的利用率将它们身上暗藏的浩瀚的能量聚集给躺在床板上的这个人。
就在这时。
一声愤怒的凄号传来,让他再次睁开双眼,借助微弱的灯光他再次看到了那把剑的主人,可惜如今它已经失去意识,唯有与生俱来的倔强让它本能的狂吼,可惜,螳臂当车终无用,不久,它成为一片花火,坠落在杀死它的人身上,化为乌有了。
随着这一道能量的进入,他当即感觉一阵格外冰冷刺骨的阴寒袭来,比之以往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这正表明这道灵体比之其他灵体更为强大,他倒吸倒吸一口气,随后剧烈的抽搐,目光变得涣散,只有刀削一般的面孔看起来坚决无比,他身上的血管猛然突出肉体,发出那种粘稠的液体移动中遇到阻力时的声音,他赶忙闭上眼睛,嘴唇颤抖得厉害,面色惨白,发出极度痛苦时才有的扭曲。
这时他猛然抓住桌子上的另一壶酒,竭尽全力得灌进肚子里,一饮而尽。
直到许久之后,他的身体才像气球一样干瘪了下来,目光发出一阵灿烂的光辉,他胸膛上的伤口竟然在短时间之内愈合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很快消失,他长吐一口气,将方才那股令人胆寒的痛苦吐出来。
这个时候他明白,酒可以缓解疼痛,有时候痛苦又对人有好处。
呵!
他发出一声冷笑。
这座大阵当年由两位魂道始祖商衍子,天藏子创立,掩埋了无数蛮荒英灵,铸造了神州浩土九条龙魂,衍生出九圣铸鼎的辉煌传说,可惜现在已经沦落到只能为这两位始祖之一的后人聊作疗伤之用的地步了。
他永远为自己的姓氏骄傲,但却为自己感到羞耻。
现在他只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暗中疗伤,伤好了,又去伪装,去掠夺。
…………………………………………………………………………………………………
牧野之城是晋阳帝国南境十八城之一,比邻雾灵山前浩瀚的荒野,故此有名牧野之城。
今夜,牧野之城是很特殊的一个,当一轮明月照亮了晋阳帝国浩瀚的万里江山时,这座城池露天的一角上空,月光像水流一样不停游走,却无法穿透月下的一座光幕,也像水汽一样的暗中渗透,照亮下方可怕的景象。
迷蒙的飘忽的月光从天空向下垂落。
幽灵在空中狂舞。
吱呀一声。
叶苍推开这扇紧闭的大门,微弱的月光从门边挤进来,可是,门里的世界太黑暗,这点光芒照不亮的,只会狂风更加凶狠的吹进来,那里连至少的一盏孤灯也没有,早已经彻底陷落在无可救药的黑暗深渊之内。
无可救药。
借助幽邃的月色,叶苍望向他手中的剑,那目光像是臭水沟里老鼠的眼睛望向星空,他可以飞到那里吗?
他的面容是刀削的,很容易使人响起花岗岩,一头长发仍然被紫金冠紧紧的束缚住,额头上方的发尖尖锐如同手中长剑,他整个人此刻也如同手中剑,尚未出鞘却已经发出一股刻骨森寒的剑气。
大风忽起。
巨树狂摆。
叶苍横剑当胸。
“铮!”
剑出鞘,一个身影在挥舞。
一股尖啸,随着剑的拔出而发出,初时细微到不可听闻,转瞬间却已然响彻长空,直似雷电的飚鸣,又像清风的轻啸。
叶苍手执长剑,却不像是在舞剑,而是在书写。
剑不仅仅是杀人的利器,有时候也可以是一支笔,剑客有时候也会在狂乱的剑气之中挥毫泼墨,我手写我心。
对于叶苍来说,此刻他掌中的长剑就是一支笔,书写自己刻骨铭心的仇恨和狂怒,没有对手,他就在起伏转折中刺向虚空,仿佛对着自己的倒映练剑,批红判白,堪与造化争奇。
剑峰随着挥舞不停的颤抖,带动的气劲铺天盖地般像四周潮涌而去,卷起尘屑,每一粒尘埃都在狂烈的震荡,在大风中飘扬,在空中飞行。
月似冰轮,剑如匹练。
叶苍冲天而起,眼中炽烈的光芒透露出他刻骨的仇恨,他的身形突然变得诡异而僵硬,似乎他被披上了沉重的枷锁,而他只可以趁着阴暗的月色披着枷锁挥舞。
他的剑在风中凶狠的抡动,剑气披宵决汉,却怎也刺不破眼前的黑沉沉的铁幕,杀不死他放在心中的那个人。
噗
长剑没入一棵大树,好像刺进他仇恨的那个人的胸膛一样,他的目光也刺向大树。
忽然间!他的目光骤然转移,和他的剑一般的锋利,刺向聂铭和楚惜月两个窥探者的位置来。
聂铭心中大惊,料不到他竟然能这么敏锐的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已经隐藏的很深了。
他的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剑光更急,狂猛的气劲让大树寸寸爆裂,应声而断。
聂铭和楚惜月赶忙移出几丈之外,逃离那片区域,此时聂铭的内心大受震动,叶苍的剑法让他明白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虽然他现在已经明白楚天河身在何方了,但却苦于无法将其救出。
他们跑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发现叶苍根本没有追过来,处于安全考虑,两人又跑出了很长一段距离,这才停下来。
两人坐下,默默沉思,接下来如何是好。
沉思中的聂铭忽然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楚惜月此时也心绪难平,今晚的一切都是那样诡异,让她感到一股不可抑止的恐惧,她努力平静了一下,道:“那是我母亲的祠堂,她死之后,父亲特地为她建的。”
聂铭面色凝重不改,又问道:“那间屋子有秘道吗?”
楚惜月无奈的摇了摇头,道:“没有。”
聂铭无言,唯有沉默以对失望,眼前的困局几乎绝望到无解,不过至少至今仍然不见商明的身影,这让他多少感到有些欣慰。
情势实在令人无法乐观起来,聂铭习惯性的手中紧握他腰间的刀柄,手指在上面摩挲一会儿,口有点渴了,他忽然下意识的摸向他的酒壶,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他的酒壶不见了,聂铭奇道:“我的酒壶呢?”
楚惜月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一开始就不见了。”
聂铭闻言一拍脑门,道:“这次我们有事可做啦!”
楚惜月闻言大为激动,赶忙道:“怎么,你想到办法啦?”
聂铭道:“办法没有,酒一定要有,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酒。”
楚惜月一阵无奈,叹道:“你和我爹一样,嗜酒如命,要不是有我时常限制他,他简直要活在酒缸里面啦。”她说罢脸色又阴沉了下去,聂铭知道,她肯定想起了危在旦夕之中的老父。
聂铭为了缓和一下气氛,笑一声道:“那他没有酒喝的时候怎么办呢?”
楚惜月理所当然道:“忍着呗。”
聂铭嘿然一笑,暗道酒徒的手段你是不明白的,忽然间他心神一动,问道:“那你父亲是不是时常爱去你母亲祠堂呢?”
楚惜月面色黯然,道:“那是我父亲每天必去的一个地方!”
她话音未落,身体已经被聂铭拉起,被动的跑起来了,她惊骇的问道:“你这是干嘛?你要拉着我去哪里?”
“酒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