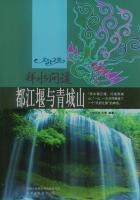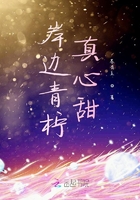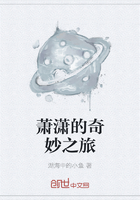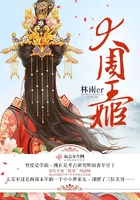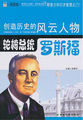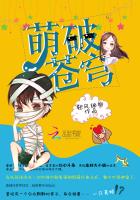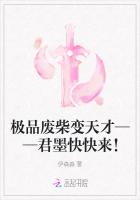佛教也认为赡养、照料父母是人子应尽的责任。佛教认为,僧尼辞亲出家,并不是放弃自己赡养父母的责任。佛教强调,吃斋念佛固然对修行大有裨益,但还必须以世间善行作为“助缘”,才能证悟佛法,而孝养善事父母就是世间最大的善行。所以,僧尼出家前要先安顿好父母的生活,出家后如果父母的生活失去依靠,也要节衣缩食、尽心竭力奉养父母。佛教进一步提出,布施圣贤“不如孝事其亲”,父母就是家中的佛,“有亲在堂,如佛在世”,要将父母当作佛陀一般来敬奉,孝敬双亲是最大的功德。佛教还提出了孝为戒先、孝为戒本:“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这就把持戒修行都统一到孝道上来了,孝敬父母成为得道成佛的必要条件。
儒佛孝道内涵上的歧异主要体现在对父母精神上的敬养方面。儒佛孝道都认为,物质上的养亲孝亲只是小孝,对父母精神上的孝敬才是大孝。如,儒家讲“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佛教说“孝之大者在乐亲之心。”但是,在“敬养”的内涵方面,儒佛孝道是有区别的。
莲池大师把世俗孝道概括为三个层次:“一者承欢侍彩而甘味以养其亲;二者登科入仕而爵禄以荣其亲;三者修德励行,谓成圣贤以显其亲。”最低层次的孝是菽水承欢、彩衣娱亲,让父母衣食住行没有匮乏、生老病有所倚靠,这是物质上的孝;第二个层次是登科入仕,让父母尽享荣华富贵,这是较低的精神层次上的孝敬;第三个层次是建功立业、成圣成贤,名声昭于时,利泽施于后,光耀门楣、显扬宗族,这是儒家孝道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但是,在佛教看来,世俗之孝只是尽一些琐碎的、微不足道的养亲义务,即使是显亲扬名、光祖耀宗,也依然是“小孝”。只有学道弘法、修德成佛,报答多世父母的恩德,才是真正的“大孝”。这种“大孝”由低到高也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出家修行,为父母修福造经,度父母亡灵脱离六道轮回之苦。佛教认为,僧人舍俗出家,表面看来是离家疏亲,实际上是舍小孝而成大孝,“一子成道,九族超升”,出家修行同样能够荣亲耀祖、光前裕后。僧侣修心念佛,“能为父母作福造经、烧香请佛、礼拜供养三宝,或饮食众僧,当知是人能报父母其恩”,因而才是对父母恩德的报答。佛教特别注重超度父母的亡灵,主张“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使其永出苦轮,常住正觉”,进行造经念经、盂兰盆会等的目的,就是祈求往生的父母离尘垢恶道,长驻净土,永享安乐。
二是善巧劝谕,让父母见佛闻法,勤修定慧,了脱烦恼生死。
佛教认为,“父母得生净土受诸快乐,岂不嘉哉?平生孝养正在此时。”莲池大师就讲:“出世间之孝,则劝其亲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愿往生,永别四生,长辞六趣,莲胎托质,亲觐弥陀,得不退转。
人子报亲,于是为大。”《佛说孝子经》中佛谆谆告诫沙门:“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亲者,虽为孝养,犹为不孝。”所以,在佛教看来,劝导父母皈依三宝,持斋念佛,断除三途辗转之苦,于女才算成就了大孝,“人子于父母,服劳奉养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显之,大孝也;劝以念佛法门,俾得生净土,大孝之大孝也。”
三是由救济今世父母而救济多世父母、普渡有情众生,这才是至孝。在佛教看来,竭尽股肱之力孝养父母,或为父母割股剜目、赴汤蹈火、历尽劫难,并不足以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为父母造经祈福、超度父母亡灵,这种孝道仍然是狭隘的、有限的。只有将救济今世父母扩大为救济多世父母,将报答父母恩德的孝心化为对有情众生的大慈悲心,以菩萨道解救众生困厄,让一切众生止恶修善,敬信三宝,才能报答父母浩大的恩德,才是最大的孝行。佛教的报众生恩,佛教的放生,无不是孝心的扩展。由此可见,佛教的孝心就是慈悲心,孝道也就是菩萨道,举凡六度万善、菩萨百行,无不是孝道的扩充:“孝养为百行之先,孝心即是佛心,孝行无非佛行。”
释迦牟尼和地藏菩萨被奉为佛门两大孝子。所谓“大孝释迦尊,累劫报亲恩”,佛陀躬行孝道,不仅在于他为父担棺、为母说法,更在于他舍身出家,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正如孙绰在其《喻道论》
所云:“故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还照本国,广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场。以此荣亲,何孝如之?”地藏菩萨发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以慈悲之心承担众生的苦难。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佛教的大孝精神。
可以看到,在对孝道内涵的理解上,儒家孝道世俗的、人文的旨趣与佛教孝道浓厚的宗教色彩,体现出人文与宗教,即世间与出世间孝道的分野。
三、推己及人与慈悲众生:孝道境界上的歧异
性善是儒家对人性的主流看法,性善论与佛性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儒家的“涂之人可以为禹”与佛教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出一辙。但是,儒家思想是即世间的,其关注点始终在于人类社会、在于人类自身,不出乎六合之外;而佛教思想是出世间的,佛教以无限时空为背景而展开自己的理论,佛教孝道所及,是整个三千大干世界的有情众生。佛教所谓的“众生”,不仅仅指人类,也包括一切有情识的生物,这就使佛学比儒学具有更宽广的理论视野,相应地,佛教孝道也呈现出比儒家孝道更开阔更深远的境界。儒佛孝道对于行孝主体和行孝对象上的不同看法,就是这种分别的反映。
儒家认为,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人优异于动物的独特之处,而佛教认为包括动物在内的众生都具有孝心,都可以成为行孝的主体。
儒家突出人的价值,强调“惟人,万物之灵”,认为道德是人的属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只有人不仅有气、有生、有知,而且有仁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所以,孔子、孟子在讲到孝道中所蕴含的“敬”的内涵时,都把“敬”视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孔子讲:“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可见,儒家认为孝道是人所特有的道德行为,是人和动物相揖别的标志之一,所以不忠不孝的叛臣逆子被贬称为“禽兽”。“有知而无义”的动物即使偶尔有“报答”亲恩的行为,也只是一种本能,如乌鸦之反哺、羊羔之跪乳。
佛教则不然。从缘起、平等出发,佛教认为有情万物皆有佛性,孝是包括禽兽在内的众生共同的本性。因而,佛教将孝道由人而扩展到动物,六道众生都可以成为行孝的主体。《大方便报恩经变相》中就记载了鹦鹉采谷孝敬盲眼父母的故事。
孝的对象是父母,这一点是儒佛孝道的共识。区别在于,儒家孝道所指向的只是自己今生今世的父母,佛教的孝则延及到多世父母。
儒家没有三世因果的观念,所关注的只是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生,所以儒家孝道也是针对父母此生的孝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养敬事、祭祀缅怀,这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都是对父母今生今世而言的。
佛教则超出了血缘关系的链条,把孝道扩展到佛法所及的整个有情世界:由孝顺自己的父母到孝顺众生的父母,由孝敬今世的父母到孝敬过去以及未来多世的父母,佛教把孝道普及到三界六道无量众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为我们展现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时空。
佛教认为,众生在三世、六道中轮回流转,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人的一生仅仅是无限的生命延续中的一个片断,是无尽的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众生关系密切,互相有恩:“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或为父母为男女,世世生生互有恩。”六道中的任何神、人、畜生甚至饿鬼,都可能曾经是、或者将要是自己的父母,一切有情都可能是自己多生多世的父母:“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