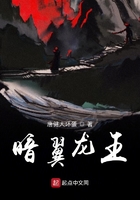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孝观念提供了滋生、成长的温床;另一方面,孝道也恰恰适应了农业文明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保障和支持,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农业自然经济基础的完善和稳固。这种保障和支持是通过伦理与政治的相互渗透,从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农业社会的特点就在于,“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社会,需要产生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政体和统治思想,这便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其实,这种“东方专制主义”不仅仅指政治领域的君主专制主义,它同样也适用于家庭关系领域。归根结底,孝“不外乎维护传统农业社会所奉行的父权家长制”,而家长制、君主制的存在,则起着维系农业个体经济再生产的作用。
从“国”的角度看,高度分散的农业自然经济需要以君主专制的集权形式,把众多各自为阵的小家庭、家族联系起来,把人们的意志统一起来,臣民必须维护君主的权威,这就是“忠”;从“家”的角度看,农业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独立的个体家庭同样也需要一个专制的家长来组织、管理生产,并负责调整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子女必须服从家长,这就是“孝”。忠孝二者彼此相通,双管齐下,共同维护和巩固着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基础。
总之,农业文明是孝观念孳长的息壤。宗法制的形成和兴盛,也与农业文明密不可分,如农业的集体协作与群体意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与聚族而居等等。宗法制是孝观念得以萌生、成长的又一个根本性的因素,这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血缘宗法社会的直接产物
孝观念固然是农业文明的道德结晶,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一点,就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农业文明,文明发育较晚的国家中也不乏农业国家,为何独独中国古代孝观念特别发达呢?如果从亲子之间的自然情感而言,或者说,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孝应当具有普遍的心理基础,为何只有在中国,孝被抽象、提升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并且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呢?于此,我们不能不注意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是血缘宗法社会。血缘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块基石,也是孝观念产生的社会基础。作为儒家伦理核心的孝道,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宗法社会的特征。
宗法制度起源于未充分解体的氏族社会血缘纽带。黄土地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以及四周繁盛的人口部落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使中国古代文明“可能在温室似的环境下成长,而有异于自然生长的希腊文明。”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与西方是不同的,西方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中国是以农业社会的形态经历着氏族制度的解体过程,是带着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公社进入阶级社会的。早熟的文明没来得及彻底清算氏族制度,就在它的废址上建立了“公族国家”,阶级社会直接由血缘部族脱胎而来,部族首领一变而为国家君主。前者是新冲破旧的新陈代谢,后者则缺乏一个质变的环节,新旧纠葛,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因而氏族社会的解体完成得很不充分,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比如,宗法观念、祖先崇拜以及其他一些氏族伦理观念等就作为中华文化的因子而沉积下来,进而又作为一种社会“遗传基因”,成为培育中国文化的独特土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的普遍根据。
在政权更迭的政治斗争中,统治者看到了亲族血缘联系与社会政治等级的关系及其价值所在,遂自觉地把它作为强化政治统治的重要资源凸显出来,上升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商朝已初步形成宗法,但并不严密,宗法制到了周代才全面确立。殷亡周兴的社会大变革,用王国维的话说:“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里的“新制度”、“新文化”,也就是指周代宗法制度的完善和礼乐文化的兴起。具体而言,“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日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日庙数之制。三日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立宗子、固大宗、别嫡庶、定继统、正尊卑、分贵贱、序世系、敬祖宗,周代以井田制为基础、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世袭分封为政治结构、以宗庙社稷为权利象征的奴隶制血缘宗法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古代延续几千年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统治的基础。
宗法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孝观念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血缘宗法制特殊的组织体系,使孝观念的产生成为必然。血缘宗法制度的组织体系,是一个塔层结构,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居于塔顶,政权与族权、君统与宗统、政治身份与血缘身份合为一体。从政治关系看,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从宗法关系看,他又是天下之大宗。天子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别子”即其他嫡子和庶子被封为诸侯。对于嫡长子而言,他们是小宗;在其封国内,他们又是大宗,其位同样由嫡长子继承,余子为小宗,封为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及至一般宗族,依此类推,由此又形成无数个小的塔层结构。很显然,这是一个秩序严明、结构庞大的组织体系。要保证小宗对大宗的归依和服从,维持这样一个组织体系的稳定,除了政治强制力外,还必须依靠道德向心力乃至宗教约束力。这是集政治、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孝”观念得以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历史根源。
其次,血缘宗法制度,决定了孝观念,尤其是早期孝观念的基本内涵。一者,血缘宗法制最根本的伦理道德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祖”,即对祖先权威的服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尊长的绝对服从。所以,在卑幼与尊长、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卑幼子女服从敬奉父母尊长,是自然而然的。二是“敬宗”,即对血亲关系的本能维护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亲子传承的极端重视。
宗有大宗、小宗之别,即《礼记?大传》所谓“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在宗族之中,大宗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宗族的代表,因此,宗奉大宗也就是宗奉祖先。其实,大宗、小宗的拜祭是相互促进的,如《礼记》中就多次讲到:“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尊祖和敬宗恰恰是早期孝观念的主要内涵。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的血缘纽带,都可以以“父”为元点无限地扩展,祖、宗可以无限地向上追溯。但是,鉴于实际上随着血缘纽带纵向和横向的逐渐延伸和展开,血缘情感因素也逐渐弱化、淡漠,所以,以父家长为中心,又有时间上上下九代即“九族”以及空间上左右“五服”的范围规定。
这样就保证了父家长在宗法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二者,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一方面,由此而决定对于财产以及父辈一切的继承权,都是以男性传承为主的,女性的继承权微乎其微。
这是父家长权力的直接来源,是孝道的经济支柱。另一方面,由此而决定父系血缘传承原则成为宗族延续的唯一方式,家庭结构以男性为中心、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儿子作为父亲血脉当然的法定的继承人,必须承当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的责任和义务。这两个方面是后世孝观念的核心内容。
再次,血缘宗法制的发展路向,影响着孝观念的发展路向,决定了孝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春秋战国时代,血缘宗法制受到重创,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趋于瓦解。但不管如何,兼具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一箭双雕之功能的宗法制度,已经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定势,血缘纽带数千年间始终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由一个男性先祖的子孙团聚而成的家族,形成稳固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有机体生生不息的细胞。与此相一致,尽管朝代更替、社会变迁,孝观念的内涵及其表现形态也有相应的发展变化,但是,作为宗法制度的产物和维护宗法社会基础的手段,孝观念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未发生根本的动摇,尤其是当它再次与政治联姻后,历代统治者对孝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巨大作用更是青目有加。
西周以降,血缘宗法制主要表现为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族、家族。宗族、家族是宗法制度、宗法社会的原生体,在一个横断面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及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白虎通义》中讲:“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一宗族,家族的人,世世代代“聚族而居”,因此,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宗族、家族一般都有供奉共同祖先的宗庙、祠堂,有记载宗族或家族世系源流、子嗣系统、婚配关系、祖宗墓地、族规家法的族谱、家谱,有的还有共同的族产公田。这些都为在宗族、家族内强化孝道观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宗族、家族都自觉地把孝观念作为维系上下长幼伦理关系、增强内聚力的法宝,并通过族约、家规的形式把孝规范予以制度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孝的道德、社会、政治功能。所以,“在传统的中国家族主义下,人自然会、也必须要实行孝。孝不必一定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当然的事,也是作子女者的一种义务,或一种应当扮演的家族角色”。
血缘宗法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有着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的理论和完善的配套设施的庙祭祀制度,既是宗法制度的内容,也是祖先崇拜观念的物化形态。
“宗”,《说文解字》释云:“尊祖庙也,从^从示。,,“庙”,《说文解字》
释云:“尊先祖貌也。”宗庙是宗族、家族供奉和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尚书?甘誓》上有“赏于祖”的记载,“祖”即祖庙。殷商时期,宗族中频繁地进行着祭祀活动,如殷代的祖庙有宗、升、家、室、亚等多种称谓。逮至西周,宗庙祭祀制度更加完备繁杂。《礼记,王制》中对西周庙祭制度有所记载: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在古人心目中,祭祀是至为神圣、至关重大的事,其制度之严密、仪式之繁多,鲜有堪与相比的。宗族的宗庙祖先祭祀活动,不仅对孝观念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是早期孝观念及孝行的主要内容。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独特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宗法制度是孝道产生、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它的派生物宗族、家族是宣传和实施孝道的重要主体,它的物化形态宗庙、祠堂则是阐扬孝道的有力的物质载体。由西周到清代,宗法制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强度绵延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并作为民间宗族制度而遍及城乡村镇,为孝文化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
三、祖先崇拜观念的突出反映
对宗庙祭祀的重视,与古人祖先崇拜的观念紧密相关。追溯孝观念产生的文化心理根源,不难发现,孝与祖先崇拜是直接关联的。祖先崇拜观念不仅使古代中国社会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而由氏族制发展到宗法制,它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钱穆先生讲:
“儒家的孝道,有其历史上的依据,这根据,是在殷商时代几已盛行的崇拜祖先的宗教。上古的祖先教,演变出儒家的孝道;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个古老的宗教。”这深刻地揭示了祖先崇拜观念与孝道的内在联系。
祖先崇拜根源于上古时代的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原始人低下的生产力及由此而决定的高死亡率和对自然界的畏惧,使得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普遍地存在于原始先民当中。生殖崇拜与图腾崇拜相结合,使得先民们总是把某一动物或某一物件认作他们的祖先,因此,最早的祖先应当是图腾祖先。在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图腾祖先崇拜的记载。如玄鸟被视为商民族的图腾祖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人们逐渐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界、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由祭天神到祭人鬼,从自然崇拜转向人类自身崇拜,图腾祖先崇拜被祖先崇拜所代替,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