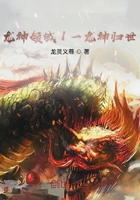李元吉侧头看了一眼李世民,转向李渊道:“父皇,儿臣从今日开始也要读一些书。说到修身养性此节,我比起二哥就差远了。二哥的底子本来就好,这一段时间又置文学馆,日日在那里谈经弄典,吟诗作文,所以有了处变不惊,决胜帷幄的本领。”他又转向李世民,“二哥,能修到这等本领,有什么速成的法儿吗?”
李世民微笑不语,心想四郎以前心直口快,说话不会拐弯儿,现在却能藏起锋芒,尽说些捧人的言语,细细听来,可以听出其话语之中暗藏机锋。
裴寂笑道:“四郎也好得很呀,你是我朝出名的猛将,现在又想读书。皇上,这是我大唐之幸啊。”
李世民见裴寂处处维护李元吉,心中不是滋味儿。心里忽然掠过一丝悔意,心想这裴寂虽不学无术,但与父皇亲密,自己满可以与他虚与委蛇,使他持中立地位。奈何自己不识其中滋味,示之以刚,生生地将他推入大郎和四郎的怀抱之中,使自己多了一名强敌。不过现在的局面已成,再悔从前,徒添烦恼。
李渊不明白两派的斗争目前已是水火之势,见李世民默默无语,日处府内与众学士谈经说文,还以为自己的一些平衡举措收到了好效果,因而不再往深里想。现在听李元吉要读书,心里大为高兴,赞许道:“好呀,说起读书此节,四郎自小就深厌之,小时候没少挨我的训诫。四郎,你若想读书,太学里的陆德明、孔颖达是当代大儒,你可拜他们为师,肯定会有教益。”
李元吉道:“谢父皇关爱,现在儿臣多从府中袁郎等人读书,陆、孔两人学问博达,儿臣须循序渐进,一时不敢惊动此两人。待儿臣有些进步后,再去请教他们不迟。”
李世民觉得李元吉在这里胡说鬼话,心想他若能潜心读书,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说道:“父皇,四弟想潜心读书,是我家之福,也为其他弟妹们树立了榜样。儿臣蒙父皇恩准,在府内设了文学馆,四弟若想读书,不必另起炉灶,可入府一同研讨。这样,我们兄弟在一起,可以日日读书习文,增进兄弟之间的情谊。”
李渊一听大喜,说道:“二郎此议甚好,四郎,你与二郎在一起最好,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你们两人若拧成一股绳儿共同辅佐太子,我与这帮老臣不用操心,大可出外游玩围猎,也许能多活些日子。二郎,你若看众弟中有才识卓异者,就多替我操一份心,早加培养,使他们长成后能堪大用,也算你尽了一份兄长的职责。”
这是皇帝的旨意,李世民起身恭恭敬敬道:“儿臣谨遵圣意,上辅父皇与太子,下抚皇弟,助其才略,精心为父皇出力。”
李元吉听了李渊的话,心想让自己入天策府与这位讨厌的二哥日日在一起,还不如把自己杀了来得畅快。他打定主意,可以当面敷衍父皇,但让自己去登天策府门,他李世民用一顶八抬大轿来抬,也休想让自己挪动一步。
李渊丢开这个话题,转对众人说:“这几日鞍马劳顿,想大家昨儿一晚都歇过劲儿来了。我昨日路过西山,见那里山势不算太险,又无人迹,很适合围猎。今日午时过后,我们就一同去那里猎上一回。陈卿,这事儿你先去安排一下。唔,二郎、四郎,今日围猎,你们所带府属都可参加,正好让我见识一下他们的本事。”
裴寂向李元吉看了一眼,意思是:瞧瞧,果然被我言中,二郎深谋远虑,有心再显一番本事吧。
午时过后,李渊在仪仗的护卫下来到西山。
裴寂注意李世民所带从人,发现他除了长孙无忌跟随外,其他府属未见踪影。他一时大惑不解,悄悄对李元吉说:“这二郎到底弄什么名堂?既然带了这帮猛将,又不来皇上面前显露本事,他意欲何为?”李元吉很讨厌这帮人,没好气地回答道:“他们不来最好,他们若来了,围着二郎像一群苍蝇一样,不弄得我头昏脑闷才怪,还有什么好心情来围猎?裴监,你现在怎么变得好操心了,上赶着想见他们不成?”
裴寂被李元吉抢白一顿,不以为难堪,微微一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李渊下车后,目光在群臣中搜索了一遍,问立在陈叔达身边的五坊使道:“刘卿,我那只豹儿来了没有?”唐初即设五坊使,专门负责狩猎事宜。五坊即指雕坊、鹘坊、鹰坊、鹞坊和狗坊。
五坊使刘爱素答道:“这只豹儿是陛下的爱物,臣不敢怠慢。”说完,他令人将李渊的马匹牵过来,此马系“玉花骢”的后代,由张万岁精心培育的,是去年李世民献给李渊的。
这匹马到了众人面前,只见它身材高大,依稀可见“玉花骢”当年的雄姿,身上披着耀眼的黄金鞍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最奇特的是其尻上的圆垫上,蹲踞着一头猎豹。猎豹两耳直竖,双目炯炯,前肢俯踞,后肢弓蹬,全身紧绷,力量集中在紧抓圆垫的前爪上,好像随时都会弹射而出。这只猎豹身上黄皮黑斑,脖项上戴着一枚黑色的项圈,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送给李渊的礼物。
李渊笑容满面,对刘爱素道:“朕狩猎多次,从未用过猎豹,今儿个要尝尝鲜了。刘卿,若猎豹堪用,你这五坊使的名称就要改一改,当称为六坊使吧。裴监,刘卿那里还有一只豹儿,你也试试如何?”
裴寂连连摇手,说道:“老臣不敢,只要皇上能够尽兴,就是臣下的欢喜。”
李渊哈哈大笑,移步过去上马。
随后,李渊驱马前行,众官和护卫围绕左右,开始驱赶猎杀。李渊性好围猎,众人心意共通,皆想法将猎物驱赶到李渊面前,由他张弓射之。李元吉就没有这份心思,他见猎心喜,嘴里大声吆喝,手下一刻不停射出连珠箭,野兽纷纷倒地。
他们在这里围猎,直进行了两个时辰,人人弄得浑身大汗。那只猎豹果然厉害,专寻大兽下口,每每看见猎物,就弹射而出,腾空时发出吼声,野猪等物一听见这声音顿时都吓呆了,很快就被猎豹冲上去擒获。
这场猎事下来,李渊猎获最多。再下来,就要数李元吉了,其他人都是寥寥无几。
李渊很是兴奋,觉得这场射杀爽快极了,遂笑对群臣说:“知道朕为何爱出行狩猎吗?当然狩猎本身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儿,然我大唐以武立国,不能忘了尚武的本分,这其实是朕心里最记挂的。”
李渊在这里自鸣得意,裴寂、封德彝急忙来颂扬数句,萧瑀、陈叔达、屈突通也点头附和。
父皇到底怎么了?李世民听着群臣在那里恭维李渊,又见李渊面带微笑,心中着实受用,思绪因飞开了去。近年来,国势渐强之后,他开始少问政事,例行的早朝他动辄不来,整日里与年轻的妃子厮混在一起,或者出外狩猎,俨然一个太平皇帝的模样。自去年开始,仅避暑的宫殿就连修了三处。
诸代皇帝中爱享受者多,励精图治者少,莫非父皇现在开始松弛心志,只想一味贪图享受吗?
想起父皇在处理自己与大哥相争的事情时,李世民不由得顿生怨怼之情。既立大郎为太子,不该再怂恿自己的夺储之想;既想立自己为太子,就该废立分明,不该拖泥带水。如今已酿成了争位之势,父皇又不分青红皂白,试图用平衡的手法来换取眼前的清净。如此重要事体,父皇不认真从根源上来消弥,仅仅做一些表面文章,岂有用处?
说到底,这都是父皇的性格使然。犹豫不定,左右摇摆,当为国君之忌。想到这里,李世民忽然心间涌出了一丝忧虑:眼前正准备的这一场大事,父皇当何以处之呢?
李世民在这里独自发呆,目光直直如傻了一般。这时李渊车仗开始返回,群臣骑马随后,李元吉诧异地看到李世民那木呆的样子,喊了一声:“二哥,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该走了。”
李世民方才惊醒过来,想起刚才自己失态的样子,自嘲地笑了一笑,打马随上前去。临近西门桥边,大队人员依例返回驻地,不能再往前行。这时李世民驭住了马,唤过长孙无忌,问道:“张万岁那里有什么新消息吗?”
长孙无忌见身旁无人,靠前几步,轻声说道:“自从我们离京时得了张万岁的飞鹘传书,此后再无消息。当时他已经动身,依时间估计,他现在应该得手了。”李世民在府里养了两只白鹘,可以用来传递书信。李世民为它们固定了两条路线,一路飞往洛阳,每天可以往返数次;一路飞往陇西张万岁的牧马场,每天可以往返一次。这样他在京师,每日可以与洛阳张亮、陇西张万岁频繁联络。如今来了坊州,白鹘不能随行,两地讯息就要滞后很多。
“京城里的人到了没有?”李世民临行前交代李安,让他每天将白鹘所传书信快马送到自己手中。
长孙无忌回答道:“算着时间应该到了,二郎,你先入宫,我到大路上迎候,一有消息,我立刻入宫禀告你。”
李世民点点头,轻声道:“事发之初,不可毫厘有错,这点你要切记。”说完,他拨马回宫。
李元吉要博李渊的欢喜,他从猎获的野味中挑出几种,亲自入后厨指点厨子洗剥、烹制,果然做出了几道独特的美味,李渊和群臣交相称赞。裴寂边吃边道:“陛下,老臣以为,要说这烹制野味的道儿,举目天下,难有人与四郎比肩。”
李渊笑道:“人言四郎善狩能食,果然不错。四郎,你今后若将这等聪明之处用在读书上,相信效果也会不错。”
李元吉很是得意:“可惜这次来未将趁手的厨子带来,父皇的御厨呆板得很,一招一式皆循老法,不求新变化,滋味就差了一些。”
李世民心中有事,不知食之滋味。他见李元吉沾沾自喜,心想他不务正业,偏爱在这些无聊的事儿上下工夫,若让他读书,无疑是痴人说梦。遂不发一言,伺候李渊吃完,然后离座返室。
李世民回房后先去洗浴一番,然后披上一件长衫端坐在孤灯前,拿出一本老子的《道德经》静读。不大一会儿,长孙无忌推门进来,取出一个管状的绢纸卷儿递过来,低声道:“二郎,来了。”
李世民起身放下书卷,接过绢纸,小心在灯前除去上面密封的蜡泥,轻轻展开绢纸,只见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李世民凑近灯前凝神观看。
李世民细细看完,眉头顿时舒展,轻声微笑道:“这事儿成了,张万岁的戏做得挺足。”说罢,他将绢纸放在烛火上点燃,那纸片儿化成青烟,很快燃烧殆尽。
长孙无忌也不禁狂喜,轻声道:“数月里的努力终于有成,二郎,没想到这事儿如此容易。我们等着看看好戏逐步登台吧。”
李世民沉吟道:“世事难料,不到最后,我们也不可将话说足了。无忌,你趁早回营吧,可以先将杨文干谋反的事儿,给玄龄、如晦等人透个信,让他们有个准备。”
“要不要将此消息透给三宝?”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找三宝说。嗯,我们要把握好节奏,不可乱了章法。你去吧。”
长孙无忌告辞退出。
第二天未时三刻,西门守卫急匆匆来见马三宝,说外面路上来了一溜装满甲戈的车。领头两人自称是东宫之人,口称有紧要事情求见马三宝,并要求觐见皇上。
马三宝急忙赶往西门,过了桥就见那两人立在当路,他细细一看认得他们,原来是东宫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
平日里,马三宝与他们甚是相熟,经常开玩笑,今天在这个场合见面,马三宝不敢造次,冷面问道:“两位不在长安,却随带甲戈来此,到底有什么紧要事儿?说吧。”
尔朱焕、桥公山脸色凝重,桥公山跨前几步凑到马三宝的耳边轻声说道:“马将军,事关重大,请借一步说话。”
三人一起过桥到了西门守卫房内,马三宝关上房门,目视两人道:“有什么事儿,现在可以说了。”
两人对视一眼,尔朱焕道:“马将军,这事儿说来实在令人胆寒。外面的车装满甲戈,是太子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的。”
马三宝点头道:“我知道,太子送给杨文干甲戈,也不是一回了。”
“是的,我们领太子之命送甲戈给杨文干,非复一次。然这一次事儿却很奇特,临行前,太子将我等两人叫入殿内,他屏退左右,秘密给我们说了一席话。我和公山领命出长安后,愈觉事关重大,到了豳州,说什么也不敢再前行了,听说皇上在坊州仁智宫,就来这里先见马将军,并请转禀皇上:太子要谋反了!”马三宝大惊:“什么?太子要谋反?怎么可能?你可将太子给你们说的话细述出来。”
“太子对我们两人说,如今杨文干练兵已成,让我们将此批甲戈送过去之后,就跟随杨文干一起举兵直奔仁智宫,想法捉拿皇上、秦王及众大臣。长安那边,太子也起兵响应,以此废了当今皇上,太子可登皇位。”
“啊,太子怎能这样?他可有书信交给杨文干?”
“没有。太子说,事关重大,让我们将话儿记熟,然后口传给杨文干。”
“好,你们所说的是实话吗?”
“我们两人愿以头作保。”
“你们若见了皇上,敢将这般话儿原封不动说出吗?”
“怎么不敢?我们拼了身家性命,原是为了一片忠君之心。”
“好,事不宜迟。你们随我马上觐见皇上。”
李渊冷眼看着尔朱焕、桥公山在那里跪诉,觉得事情不可思议。心想那杨文干居于弹丸之地,敢有什么胆子来举兵谋反,且太子一向忠厚淳朴,自己刚刚出京,他就想夺位,不似他一惯的作风。待两人将事情说完,李渊哼了一声,斥道:“你们两人好大的胆子,受了何人指使,敢来诬告太子?”
两人闻言浑身发抖,颤言道:“小人说的句句是实,不敢诬告太子半分,请皇上明察。”
这时马三宝跨前一步奏道:“陛下,臣一开始也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事儿非同小可,总能核查清楚。臣想,再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到皇上面前胡说。”
李渊点头道:“不错,这事儿一定要查个清楚。三宝,你先将这两人关押起来,慢慢再审。你出去后可将群臣叫进来,朕要见他们。”
封德彝却不请自来,他领着一人候在门外。马三宝领着尔朱焕、桥公山出门看见他,说道:“封令,皇上正找你呢,赶快进去吧。”
封德彝所领之人大有来历,原来是宁州刺史杜凤举。只见他满面蒙尘,浑身衣衫褴褛,显是经历了一番艰苦跋涉。他们入宫后,封德彝先向李渊介绍了杜凤举的身份,杜凤举匍匐在地,颤声道:“陛下,臣星夜来此,是想亲口向皇上禀报一件大事儿。那庆州都督杨文干,久怀不轨之心,一直勤练兵勇。前日他在庆州易帜举兵,宣称要拥立太子居皇位,并约臣一同反叛。臣不敢大意,一面约束手下拱卫城池,一面独身来此向皇上禀报。”
李渊大惊,诧异道:“真有此事?那杨文干到底仗了谁的势力,竟然敢起兵反朕。”
封德彝简要向李渊说了杨文干的来历,最后说:“杨文干起兵肯定事连太子,他虽居偏地,却事关全身,皇上,此事不可轻视。”
李渊听罢,急召群臣进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