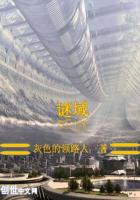“是啊,眼不见心不烦,还是玄龄知我呀。”李世民忽然想起李建成和李元吉如今得意的嘴脸,心中掠过一丝不快。
杜如晦道:“秦王,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太子如今蒙圣上恩宠及臣下颂扬,无非得其前段时间暗暗筹划之利。如今我们闲在边塞,难道就不能筹划一二吗?”
李世民不作言语,忽然抬头向天,继而极目远眺,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方缓缓言道:“玄龄、如晦,我现在忽然想起那帮老先生们。他们若在,我们就可围炉饮酒,好好欣赏雪景了。虞先生和苏先生若在这里,不知能添多少乐儿呢。”
杜如晦听到李世民提起府中学士,忽然想起一事儿,说道:“那帮老先生的身板儿都不错,可惜薛收年纪轻轻,竟然染病不起。昨日里京城传来消息,薛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看样子势头不妙。”
李世民早就知道了薛收染病的消息,听说其病加重,一丝忧色上脸,叹道:“汉武屈贾谊于长沙,惜不知才。如今正是我们大展宏图之时,薛收深陷沉疴,只能说天不与便了。”他仰天长啸一声,复对二人说道:“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我们横刀立马,岂能让这些烦恼事儿困扰我等?玄龄、如晦,我们今天就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我先吟一首,你们两人可以和之,以酬此良辰美景。”李世民所吟两句,为汉时贾谊《鸟赋》中的话。意思是说人与万物活在世上,如在一只大炉子里熬炼那样苦恼。
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开始吟诗,诗曰:
塞外悲风切 交河冰已结 瀚海百重波 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峰火 层峦引高节 悠悠卷旆旌 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 朔吹断边声 胡尘清玉塞 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 车徙振原隰 都尉反龙堆 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 纪石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 云台凯歌入
房、杜两人不善诗赋,听李世民吟毕,两人脸现难色,不愿作和。房玄龄道:“殿下此诗慷慨雄奇,极尽豪迈之气。玄龄记得陈叔达侍中有近作一首,名为《赋饮马长城窟》,我凭记忆试加吟出,来与殿下凑兴。”说罢,他开口吟道:
朔风动秋草 清跸长安道 长城连不穷 所以隔华戎
规模唯圣作 负荷晓成功 鸟庭已向内 龙荒更凿空
玉关尘卷静 金微路已通 汤征随北怨 舜咏起南风
画地功初立 绥边事云集 朝服践狼居 凯歌旋马邑
山响传风吹 霜华藻琼钑 属国拥节归 单于款关入
日落寒风起 惊沙被原隰 零落叶已寒 河流清且急
四时徭役尽 千载干戈戢
李世民体察陈叔达诗中之意,诗中充满平靖边塞的渴望,不禁说道:“陈侍中的想法挺好,这首诗的立意要比我的诗高得多。不错,历代多修长城,试图将夷狄挡在城外,又有李广、霍去病等人在边塞威震诸夷,看样子,用挡和杀这两种法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塞问题。我们今日来这里和颉利应付,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要想长治久安,还要另想别法儿呀。”
杜如晦道:“建长城却敌,为被动防守;深入敌境,斩将夺关,则是用进攻的手段杀敌人,也是一种防守的延续手段。现在我国与东突厥,正处于一个既有对抗又要怀柔的时刻,我想,随着国内逐渐稳固富强,这对付的法儿也该变一变。”
李世民似乎无心再说,就招呼他们回到了马邑。
到了这年十二月,许是年关将近,李渊诏李世民班师还京。李世民接诏后,带领随从一路向南,只见满目的山水皆现寒意,山上的树枝枯草上挂着冰条,大小水流顿失滔滔。以往每次班师,众人脸上都挂满笑意,沿途州县组织百姓夹道欢迎。这一路上却多是静悄悄的,他们到了太原,唐俭、李大亮还迎来送往一番,及至到了其他州县,四周了无声息。一行人得了李世民的命令,往往绕城而过,不去惊动他们。这样数日后,他们就到了龙门。其时河水已封冻,他们履冰过河。经此旧地,想起当初带领大军履冰渡河来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情景,李世民觉得非常模糊,好像时间很久远似的。
隆冬之际,李渊依旧耐不住寂寞,想出外活动一下筋骨。几天前,他带领近臣摆驾到了华山之阴,一连在这里狩了好几日猎。这天听说李世民已从龙门渡过河水,抵近华阴,想起以前每每亲迎二郎的情景,决定还要做做姿态。遂收下弓矢,令銮驾移到忠武顿,专迎李世民到来。
李世民回京后,急忙去探视薛收的病况。
薛收躺在床上已两月有余,李世民去探视的时候,他正倚在床头咳嗽,咳得双颊泛出潮红,胸间一起一伏,呼吸很是急促。他见李世民来探,眼睛顿时发亮,继而挥手喘道:“秦……王请出,这……这里太……太肮脏,别污了你……你的贵体。”
李世民一个箭步跨到薛收床前,握着他的手流泪道:“薛先生久病榻上,世民无缘来见,我在塞北,一直记挂着你啊。你让我出去,莫非怪我吗?”
薛收急了起来,然喘得厉害,无法出语说话。
薛收的侄子薛元敬候在身侧,他端起茶盏,喂薛收喝上几口清水,然薛收又呛了气,咳得更厉害。薛元敬用手掌轻拍其背,以舒缓其气。慢慢地,薛收缓过劲来,平卧榻上,张口大喘粗气,脸上依旧红得厉害。
薛元敬趁这个空儿对李世民说道:“禀秦王,叔父这些日子,天天挂念着殿下。他总怕今生今世难再见到你,每天他都让我到府上打探殿下的消息。”
李世民眼光中闪着泪花,握起薛收之手,颤声道:“薛先生,我知道你有话对我说。你且歇缓过劲来,我在这里慢慢等你。”
薛收的手紧了紧,用力点了点头。
众人见薛收有话要说,遂识趣地慢慢退出房外。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薛收止住了喘,脸上的潮红也褪下许多,方缓缓言道:“秦王……我看如今朝中形势……显然要不利于殿下。”
李世民点点头。
薛收继续言道:“祸福相伏……事在人为……秦王切不可堕了志气。”
忽然,薛收的言语流畅起来:“好多事情,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殿下,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此中之味唯殿下体会最深。”
李世民明白薛收隐晦所指,他其实是告诉自己,在争夺储位这件事情上,要主动。
李世民不接话,场面顿时静默了片刻,薛收费力地摇了摇手,长叹道:“殿下,就是这话。可惜,我恐怕不能再为殿下尽力了。”
李世民又流出了泪水,说道:“先生尽管养病,世民回去,当寻找天下良医,定为先生祛除疾患。”他见薛收神情委顿,不忍再扰,遂起身离去。
李世民出门后,问薛元敬道:“薛先生所患何病?缘何没有起色?”
薛元敬压低嗓音道:“听来的医生说,叔父这是患了痨病,所下药石毫无用处,眼见叔父的身子一日比一日虚了,近时还常常发烧。”
李世民心里一震,明白人若患了痨病,无药可治,他说道:“既然患的是痨病,为何不早一点把他送往岭南,却在这里苦苦相捱?”其时人们对付痨病,多将病人送往阳光充足的地方静养,往往也能收到一些效果。
“瞧叔父的身子,经不起大动,若将他转运到岭南,恐怕路上……”薛元敬忍不住也抽泣起来。
李世民回府后,伤心不已,对房玄龄道:“当初你和薛收在泾阳投我,已历七载有余。你的功劳,那就不用说了。薛收偏爱典籍,其诗赋文章,年轻一代中,他与褚亮最为拔尖。至于谋略胆识,当初在洛阳,窦建德来攻,独薛收敢于和朝中重臣相争,坚持分兵虎牢。仅此一件功劳,尽掩其书生本色,将彪炳史册。我看他的病,恐怕是好不起来了。”
房玄龄黯然道:“薛收今年刚刚三十三岁,正是为秦王出力的时候,现在若走,实在可惜。”
薛收又在榻上躺了一个月后,终于逝去。
李世民闻讯,亲往薛收府中恸哭。薛收出殡之日,李世民身带天策府属送葬,自己亲自扶棺,当街大哭。李世民作为一名皇子,封号为天策上将、秦王,竟为一名府属扶棺,明显不合礼制,礼官颇有微言。
李元吉听说了这件事儿,心里不甚明白,问李建成道:“不过是一名府属死了嘛,他二郎何至于呼天抢地,当街大哭?”
李建成冷笑道,“二郎这样做作,无非是给他的手下看,想让他们更加死心塌地。若失了这班府属,他还有什么呢?”
薛收死后,李世民十分挂念其家属,写信嘱托薛元敬多照顾其妻儿。
李世民对薛收的真情流露,深深感动了天策府内的众人。都想李世民能够这样善待手下,自己不枉了这番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