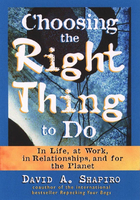钟鼓巷的旧楼传来震天动地的关门声,隔壁房东老太太拿着锅铲跑出来时,第十五次没看见人影。
前两天她家来了一个新房客,长得高大帅气,一看就非富即贵,特别是两道浓眉坏脾气的皱起时,老太太心花怒放的恨不得哄哄他。
“姑娘,你俩吵架了?”她伸长脖子,好奇地看着气喘吁吁的夏尧。
夏尧尴尬地点头:“有点儿误会。”
“床头吵架床尾和,小夫妻间更是家常便饭,你好好儿哄哄他。”老太太笑得眼角弯弯,“依我看,他是很爱你的。这几天你们俩的动静呀,可真是连我这个老太太听着都脸红哩!”
夏尧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看着老太太眉飞色舞的模样,她忍不住打断:“那个……”她往房东家里指了指,“锅糊了。”
老太太立即挥舞着铲子往屋里跑去。她拍着胸脯顺了顺气,连敲了半分钟的门,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回应。
这人的脾气还是这么臭,夏尧最后一次拍着门板,十分淡定地宣布:“你要不开门,我就先走了。”
约摸过了十来秒,里间的木门咚地被踢开,接着就是有窗的铁门。贺煜宸黑着一张脸,眉头紧锁,连看也不看她一眼,放了锁就往屋里走。
她关上门,看他一言不发地走到沙发跟前,猛地往下坐,小沙发的海绵瞬间陷下去。他拿过小茶几上的打火机点了支烟,长胳膊长腿的看上去和这间小屋子格格不入,沙发巾上的小图案却又让他显得更加孩子气。
夏尧走到沙发后面,唰地拉开窗帘,又波澜不惊地挥了挥半空中的烟雾:“烟掐了。”
贺煜宸半弓着背,用遥控器打开小电视机,依旧不紧不慢地吸着烟。她站在沙发扶手旁边,动也不动地看着他。又过了十来秒,他烦乱地将大半截烟摁灭在烟灰缸,端起茶杯猛灌一口凉水,重重搁下杯子时,里面的水溅出一大半。
“你什么意思?他都被我打残了,还不去医院守着?”
夏尧挨着扶手坐下:“我今天是去辞职的。”贺三的气焰并未消减,她顿了顿又说,“你要是不喜欢,我以后就不再见他了。”
他的眉头倒是松开,脸上的表情依旧臭臭的,不说话也不看她。夏尧伸手戳了戳他的胳膊,被他反应激烈地大幅度躲开,她又用手扯他的耳朵:“听见没啊?”
贺三又摆晃着脑袋躲开她的手,别扭的样子真像生气的小孩子。她忍住想笑的强烈欲望,往他跟前坐了,又双手捧着他的脑袋,将脸掰过来向着自己:“你要再不理我,我现在就回家去,反正家里住着比这儿舒服。”
他皱着眉毛瞪她:“嫌贫爱富的女人!欠收拾!”说完就用手在她的腰上挠痒痒,笑得夏尧赖在他怀里,跟猫似的窝成一团。
他轻轻掐她脸上的肉:“这样就想打发我了?”她躺在他腿上,睁大眼睛望着他:“那你想怎么样?”他笑得邪肆又诡异:“你说呢?”
夏尧狠狠瞪他一眼,忽然也笑得诡异,细白的手指点着他的胸膛:“当年为什么提分手?”这事情放在以前贺煜宸肯定会找理由赖过去,可看着她诡异又笃定的笑容,心下倒有些发慌。该死,陆翊明这小子又欠揍了!
一把握住她乱戳的手,他扬起眉毛得意地说:“把爷伺候好了就告诉你。”
“切!”夏尧不屑地撇撇嘴角,“不说拉倒。”
贺煜宸郁闷,他怎么会爱上这种女人,不但脾气坏还如此不解风情。夏尧伸手点他的下巴:“又
摆臭脸给谁看?”
他歪着脑袋看别的地方,并不回答。她又伸手扯他的耳朵,揪领子,捶胸口……方法用光了,他
依旧岿然不动。最后她只好烦闷地闭了下眼睛:“好啦好啦!”然后就慢慢从他腿上坐起来,伸长脖子吻他的脸,再到唇,感觉到他喉头有深意地滑动,她胡乱地啃了啃他的下巴,就将阵地转移到他的脖子。
这种事情,贺三如何被动得起来,三两下就反被动为主动,抱着怀里的女人啃得她连气都喘不上来。半裸着下身往床上走时,夏尧蓦地想起什么,捶着他的肩嘀咕:“别在房间,隔音不好。”
每次她想忍住不发出声音,可神志不清又被他弄得死去活来,到要紧时刻根本就忘记隔不隔音的问题,娇喘连连的媚叫声连窗户外的白杨树听了都差点站不直腰。
他性子急,还未放她到床上就已经钻进去。疼得她两只小手将他平展的衬衣抓得皱巴巴,嘴里还娇嗔着说他讨厌。
心情霎时极好,他笑着搂着她转身往厨房走。厨房的隔壁是空地,这下该是安全了。当贺煜宸把夏尧放在流理台上时,平常冷淡自若的女人又羞红了脸。他看得心里暖洋洋的,搂着她的腰就开始律动。
双林湾别墅的前庭,放寒假的凌烟正蹲在翠竹下逗狗。宋将军拄着拐杖从怀里拿出一只镯子:“烟烟,太姥爷送你这个。”
她转过头嫣然一笑:“太姥爷,我真不知道舅舅在哪儿,他连路叔叔都没给说,还怎么可能告诉我一个小丫头。您老送多少镯子我也还是不知道的呀!”
老爷子闻言差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洒出来,谢东奎已经被罚去马场驯马了,竟连跟踪这么点儿事也办不好,一个手无寸铁的大活人也让他给跟丢,也不知道当年他是怎么活着从战场上走下来的。
一失去贺三的消息,老爷子顿时焉了一大半,隔天要拄着个拐杖才能走动。谢东奎遛马的时候满腹叹息,什么样的藤结什么样的瓜,他老将军的外孙子能弱到哪儿去,怕是早知道有人跟着,才领着一帮人瞎溜达一晚上。
到剌花胡同时终于跟丢了,他找到胡同里卖宵夜的店老板打听,才知道这死胡同其实不死,尽头拐弯连着一堵矮墙,墙里有家幼儿园。鬼点子乱转的贺三肯定是越墙,从幼儿园出去了。
宋婉绿已经成功病倒了,只因为过于思念自己的儿子,但是还有老大老二在床前伺候着。她迷迷糊糊地说梦话,一口一个三儿地叫唤着。
贺煜景将毛巾甩进盆里,抱怨道:“你说咱俩跟这儿凑什么热闹?跑前跑后地伺候着,人压根儿连看都不看一眼,满心眼儿里都是她的宝贝儿子。这么喜欢儿子,当初怎么不把咱俩送人算了!要我说,三儿就是被她给惯的,现在找不见人了也是她自找的!”
贺煜娴把汤碗交给吴翠翠,嗔怪地看她一眼:“你这会儿倒抱怨了,前两天是谁催着我把钱给三儿送过去?急得也不送烟烟上课了,恨不得拿命换似的。”
“你还说呢?我跟这儿急得团团转,揣着钱跑他那儿去连人影子都没找着。”说到这里又叹口气,“这小子从小就拧,摔哪儿磕哪儿了连吭都不吭一声。可这回不一样啊,谁不知道他那公司是他第一次认真完成的大事儿,都到这节骨眼儿了也不说找家里人帮忙。姥爷生气不管他,还有俩姐姐摆着不是?”
贺煜娴笑:“他那脑袋瓜里装什么你还不知道?表面上吊儿郎当没个正经,实际葫芦里可藏了好几味药呢。也说不定是他借着姥爷出手的机会故意把公司让出去。”
贺煜景张大眼睛:“他疯了?这么多年心血舍得放掉?就算要放掉也不必借姥爷之手呀?”
贺煜娴意味深长地笑:“一来他爱面子,二来也得给公司上下跟他多年的人一个交代。”贺煜景的好奇心完全被激起:“姐,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你快告诉我?”
“我只知道他为什么要借姥爷之手散了公司,可不知他为什么要散。都说了他脑子里的水深着呢。”
钟鼓巷旧楼,床上熟睡的女人被手机铃声吵醒,她推了推身边的男人:“不上班么?”贺三咕噜一声,扯过她紧紧抱着:“工作都没有,上哪儿的班,老婆你先养着我。”
“要女人养,你好意思!”
“别的女人不行,老婆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我养着你,你养着别的女人?”
他咬她耳朵:“正宫娘娘在这儿候着,小的没那个胆子。”
她咯咯地笑:“可是我也没有工作了呀!”
他闭着眼睛耍赖:“但是你又没有破产,快点些,把存款拿出来给老公发点儿零用钱。”
响过一轮的手机铃声再度发出声音,夏尧笑着掀开他的手,说是要上厕所,实际去了厕所接电话。他没有工作,她其实可以帮他找工作呀,女人踌躇满志地笑着看了看手机屏幕,来电显示上赫然跳跃着三个字,筱言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