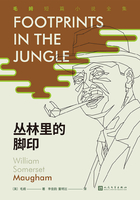“舒展,我对不起你。我不能给你长久的幸福,却支取了你的爱情。我是有罪的,今天受到惩罚也咎由自取。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想向你说明,虽然我答应过你的父亲,永远不道出实情。你的父亲他很爱你,竭尽全力保护你。你父亲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们的恋情,那年夏天他突然来到飞行团,向组织上告发说我利用职务诱骗了你。你父亲很气愤,无论我怎样向他发誓我们之间没有真正发生性关系,你父亲就是不肯原谅我,他要把我撵出军队、要置我于死地。
“舒展,你是知道的,我多么热爱我的军人身份、热爱我的职业,迫不得已我向组织上撒了谎,辩称说你勾引了我,缠着我带你上天。哦,舒展,你那次在电话里质问我,为什么那天早晨没有要你。我无法回答你,我没有脸面对你说,我是怕伤害到你的纯洁。舒展,我之前对你说过,虽然你认为我那天没有动你是贻害无穷,但我坚信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如果说我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错误,从来就是错误,那么这是这其中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舒展,上面这些话都不重要,下面的话你要听好,要用心记住。第一,你要爱惜自己,爱惜你的身体,不要挥霍它、践踏它,要把它留着给一个值得你爱的人。第二,不要为难你父亲,他做了一个爱护女儿的父亲应该做的,你也要爱他。第三,我给你留了一些钱。我的家被抄了,全部财产都被查封,但有一笔钱我放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它是我在深圳掘到的第一桶金,对我意义非凡,所以我一直保存着没有动。这笔钱数额不算多,但足够你出国留学和将来创业的基金,还够你给自己置办一份像样的嫁妆。我希望你收下它,我受到的惩罚已经可以洗刷它的肮脏,它们是干净的。你记住,银行的密码是那次在蓝天上,我吻你的当时我们飞机所在的经纬坐标的头三个数字。第四……第四……啊,没有第四了。如果有,舒展,你能允许我能再叫一声你的小名么?能允许我还能再说一声‘我爱你’么?闹闹,我真的很爱你!”
嘟,嘟,嘟……嘟,嘟,嘟……
我像一块被液氮冻住的标本,僵硬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能行动、不能思维、不能让心感到痛。
恰在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我以为还是许安阳,急忙抄起听筒喊:“喂?喂?”
对方是收发室李大爷,他说门口有我一份特快专递,深圳来的。我听“深圳”两个字,放下电话便向学校门口跑去。我拿着信封往基础楼走,路过翠湖时在一块山石旁停下。我看左右没人,撕开信封,一个卡片掉出落进草丛里。我拾起来看,是一张招商银行的自动存储卡。许安阳人在看守所里,居然还这样料事如神,时间掐算得分秒不差,没法不叫人佩服。许安阳一直是一个要把握命运的人,他唯一没有把握好的,就是对我的爱情。这一点毁了他的人生。
我正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传呼机忽然叫了起来。我一看,是梅丹冰找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把β-安脑活素送过去。我连忙跑回教研室我的办公室。
可是,书桌上,我之前放着的β-安脑活素却不见了。
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人将它偷走了。忽然,我的脚下踩到什么,我低头看发现一支破碎的安泡。我弯腰拾起,竟就是那支β-安脑活素的玻璃残骸,而药品已经流失殆尽!
我的脑袋又大了一下,“嗡嗡”作响。我想这下完了,那是贺兰唯一的证据啊。我记得清楚,离开办公室时我特地将它卡放在一本打开的书中间以固定,它怎会掉到地板上呢?我看着想着,猛地,心里一惊,脱口喊道:
“小白!小白——!”
房间里很安静,没有一点回应。
我收养小白很久,和它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小白是一只极聪明的豚鼠,我后来就将它放出笼子散养,允许它在房间里自由活动。平时我到办公室,小白远远就能嗅出我的气味,我一开门它就会过来迎接我跟我亲昵。可是,我才注意到,我从刚才进屋,一直没见小白的影子。
一个不祥的念头猝然袭来:小白出事了!
我喊着小白的名字,翻箱倒柜,几乎把办公室所有的家具都挪动了一遍。最后,我在书架后面的角落里发现了小白。
它已经死了。
小白眼球严重地充血外凸,舌头耷拉在外面,嘴角渗出鲜红的血丝,身上遍布出血点。我猜想,可能是小白在我办公桌上玩耍将β-安脑活素的玻璃安泡碰落到地上摔碎,而它又误食了洒出的药液,中毒身亡。
我有大约3分钟的思维空白。大脑停止思维的同时,我的双脚已经离开了办公室。我捧着小白的尸体向动物房走去。我把小白放到手术台上,转身去配生理盐水和灌注固定液。几乎就是本能,我木然而熟练地解剖了小白的尸体。我取出小白的大脑和肝肾器官,将它们保存到福尔马林液里。
做完这一切,我收拾手术台上小白零落的残肢。直到这时,我才仿佛确认小白它已经死了。眼泪夺眶而出,肆意地流淌在脸上。
传呼机又发出振动,是梅丹冰的,她一定急坏了。我索性关掉传呼机,回到办公室把自己反锁了起来。
结束前的仓皇
我离开基础部大楼,径直向行政楼走去。我上到三楼,找到挂着“党委书记”标牌的房间,敲门进去然后反锁上了门。
吕正荣诧异地看着我,半张着嘴不知所措。良久,他困惑地眨了一下眼睛,接着就又困惑了。我在吕正荣的困惑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高度污秽和高度近视的镜片放大了他眼睛里的贪欲。我和穆晨锺的事闹出来后,吕正荣曾恶毒地诅咒穆晨锺,愤恨他“又老又驼背的样子”,居然“艳福不浅”。在吕正荣看来,如我这样青春勃发的性资源是应该他首先享用的,穆晨锺哪里配得上消受?
我可以让吕正荣消受吗?在来之前的路上,我对此是毫无疑虑的。我打碎了贺兰给的β-安脑活素样品,失去了揭露马炳财吕正荣的最后机会,也失去了可爱的小白。悔恨之极,我想到来找吕正荣,我要跟他做一笔“交易”。如果我允许吕正荣进入我的身体,我就能获得反制于他的把柄。与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和屁股底下的金交椅相比,吕正荣一定会放弃对马炳财的保护。只要马炳财失去了吕正荣撑腰,即使没有β-安脑活素的毒性实验报告,单凭既有的事实也可以告倒他。谁让马炳财那样对待穆晨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坏心眼的人,他必须为自己的卑劣负责。
至于吕正荣,他一样也要为自己的罪孽抵债。对于一个党务干部,作风问题往往是撕开他诸多问题的导火线,是让他致命的第一粒子弹。我反正要出国了,不介意在博雅的名声。——我原本名声就不好。
再说,我一直渴望完成“V计划”,却总是不能够。这样正好,若做成了这些事,它还要更值得。
吕正荣从桌前站起,朝我走了过来。吕正荣不傻,他从眼睛里也看出了我的意图——或者说,他误解了我的意图。吕正荣伸手松了松领口下的领带,下意识地捋了捋那根长东西。符号学家说,男人打领带是天生性欲和征服欲的公然外露。想到这儿我笑了一下。我想要是那样,那岂不满大街都是雄起和裸奔的男人?
一想到雄起,我忽然反了胃,一阵恶心涌了上来。我记起那次在党校宿舍里,吕正荣让我看到的他那截“皮样手套”一样丑陋的性器。那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性器,它细软多皱,色泽暗淡,浑身散发着腐败的气息,你简直不相信它是一截活物。
吕正荣的手离开领带,向他的下体摸去。我忽然恐惧,生怕他又将那东西掏出来。我不是怕那东西本身,或是怕它增粗长大,成为一条真正的阳具;我反倒是怕它不能长大。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惊叫了一声。我的叫声暂时制止了吕正荣,他停下来观望我的反应。
我又后退了一步,几乎抵住了门。我在心里鼓励着自己,用之前巨大的仇恨鼓励着自己。可我越鼓励心里越恐惧,越恐惧心里越厌恶,到后来竟然真的有了胃肠反应,呕吐起来。吕正荣这时已经走到我面前。我一下没忍住,“哇”地一声将宿夜的食物混着发酵的牛奶和果汁,一点儿不剩全吐到他的身上。吕正荣被我的举动吓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我来找他就是为了冲他呕吐。吕正荣立即又变得污秽和腐臭,愣愣地站在那儿。
趁着这个空当,我返身拧开门,夺路而逃。
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过《法医学图谱》和类似的东西。吕正荣用他没有拿出的性器,治愈了我对那些东西的恐惧。
我在翠湖边转了很久,直到把想吐的欲望安抚回肚子里,把自己清洁干净。
我又回到基础楼。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大楼里冷冷清清几乎没了人。我去药理教研室找梅丹冰,梅丹冰等不到我已经离开了。我重新开启传呼机,里面有梅丹冰的三条留言和贺兰的三条留言。她们都在找我,但我无法面对她们。
我返回科里,十分沮丧。路过尚尧办公室,房门玻璃里透出灯光。我忽然想见尚尧,便推门进去。尚尧办公室的外间空无一人,里间的门关掩着。我没有多想,压下把手推开了房门。
蓦地,一幅场景扑面而来:丁薇面对面骑跨在尚尧身上,两人正忘情地拥吻。半年前,丁薇与他父亲手下的一名技师闪电结婚,不久肚子就大了起来,再不久大肚子又没了。学校里流传着难听的传闻,丁薇也似乎受到打击,人突然间增肥了许多,像一个更年期的女人。尚尧和丁薇看见我都愣住了,而我像完全没有看到丁薇的存在,径直走到尚尧前面对他说:“教授,我有话跟您说。”
尚尧原本可能想对我发火,但看到我失魂落魄的神情又改了主意。尚尧推了推还赖在他身上想向我示威的丁薇,脸色沉了一下。我看着丁薇离去的背影,想起三年前我也是在这个位置,从丁薇离去的背影上顿悟了辨别处女的眼光。当时我还为此吃醋,想想真是幼稚。我从丁薇的背影收回目光,转头对尚尧说:“教授,我犯了一个大错!”
我把小不点意外死亡的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尚尧,我说:“我弄没了贺兰手里唯一的证据,我现在怎么办啊!”
从我唐突闯进房间那一刻起,尚尧一直凝视和倾听着我,丝毫没有为之前的尴尬而感难为情,仿佛他专门为了等我才在这里坐着。尚尧待我断续说完,问道:“那只死亡豚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给它灌注了固定液,取了器官标本。
“你这样做是对的,很好。”尚尧简短地夸奖了我,接着又问,“那支β-安脑活素的残骸在哪里?”
“啊,我忘了收拾,还在我办公室。”我说。
“你带我去看。”尚尧说着从大班椅里站起,取下白大衣麻利地穿上,不等我缓过神儿,先就开门走了出去。
尚尧检查了小白的心肺肝肾脑等器官,初步判定小白的死系药物中毒。尚尧要我把小白的器官做冰冻切片,然后做抗原抗体孵育。尚尧又到我的房间看了地上的β-安脑活素玻璃碎片,要我用消毒瓶将它们收起来保存。我都照着做了。最后,尚尧说:“这件事基本上就这样了。等你的实验结果出来,我来写这个报告。根据这些证据,应该可以认定是一项责任事故。”
“教授,这么说,您答应替小不点做主?”我惊异地问。
“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主持公道。”
“这件事牵进去了很多人,还有学校的上层,您不担心……”
“你把我看成什么了!”尚尧板起面孔说,“我是一个科学家,一名医务工作者!”
“可是,我以为……”我心里想着事情,嘴上就支吾起来。
“你还是不了解我啊!”尚尧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强调说,“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人命关天的事,我是一定要管的。”
尚尧实在聪明,竟知道我刚才想到了那次贾鸿图破格晋升弄虚作假,尚尧并没有出手帮助穆晨锺。因为这个,我对尚尧产生看法,拒绝他的求欢,还不客气地说了他。尚尧当时没作反应,可这一记就是三年,今天到底说了出来。
尚尧肯在这个时候出面给予支持,对我是莫大的安慰。就如一年前我遭遇“桃色事件”,穆晨锺又撇下我偷跑出国,我内外交困被众人所指,当时也是尚尧挺力出手给了我容身之地。尚尧平时多情而轻佻,为人又精明、敏感,不讲情面;但他这两次帮我,却如同救命,绝非一般人可以有的胸怀和胆识。比起穆晨锺的执著和专情,尚尧这样的男人也有他感人和动人的一面,也不全是冷漠和薄情呢。
我脑子跑了神儿,想到当初若是我没有在那个夕阳西下的傍晚看到穆晨锺的名字投考他的研究生,我从一开始就跟了尚尧,那后面的情形会是怎样呢?我会和尚尧产生感情、发生关系吗?我想一定会的。——要是那样,会不会比我跟穆晨锺的这一段更好呢?
也许会呢,我想,尚尧还是一个值得爱的男人。
这样想着,我不禁上前一步拥抱了尚尧。我将身体贴住尚尧的身体,尚尧也抱住了我。尚尧看了我片刻,随即吻住了我。我回应着尚尧,手伸向尚尧的下体。
我一下就碰到了那里。尚尧的那里,已经无比地坚硬了起来,并且火热。
“噢,教授!”我被尚尧的身体刺激得动了情,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动手去做下面的动作。
“噢,不!舒展!”尚尧忽然反手抓住我,固定住了我。我愣愣地看着尚尧,尚尧将我的手从他的身上拿下,推开我到一肘的距离:“舒展,我告诉过你的,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我没说您没有原则啊。”我不知尚尧在说什么。
“看来,你真的是不了解我。”尚尧放开我,和我面对面地站着,摇头笑说,“我跟你说过的,我不做‘交易’。”
“我没有做交易啊。”听到尚尧这样说,我手足无措一头雾水。
“‘感激’我也不要。”尚尧说,“你不必用这种方式感激我,你不欠我什么。”
我的脸“刷”地红了,几乎无地自容。尚尧真是太敏锐、太犀利了,居然看出我心里复杂的情感波动。而这些,有时是我自己都难以体察、难以说清的。我刚才对尚尧的冲动里面确实有投桃报李的成分,但不能说全部都是感激,应该还有爱意在里面。尚尧这样讲,我也不好意思辩解。因为就在十分钟前,我还撞见尚尧和丁薇的缠绵。此情此景,即使我对尚尧心有爱恋,自尊也不会让我说出口的。我默然站在尚尧面前,一时不知进退。
尚尧又看出我的心思,他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脸颊,说:“对不起,我刚才的话不全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你知道我第一次想要你是什么时候吗?那次在尸体房,你给那个死者剥脸皮时跌倒了;但你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况下,仍然完成了必要的操作,把他的脸皮固定在下颌上。这个细节让我对你十分满意。你当时倒在我怀里,一缕阳光从天窗射进来,笼罩住了你。我看得到你脸上细密的绒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层闪光的绒毛刺痛了我的眼睛,那一刻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记得那件事。几乎就是那次,我差点儿相信了人是有灵魂的。”
“坦白说,我一点都不怀疑我将得到你,——但不是现在。”尚尧把我揽在怀里抱了一下,又放开,“现在,你还是一个处女,你身体里的灵魂还在沉睡。它不应该由我来唤醒,应该由一个值得你爱的人来唤醒。我已经老了,我是一个老头子啦。”
“您怎么知道……”我惊叫,欲言又止。
“傻瓜,”尚尧俏皮地抬了一下我的下巴,笑说,“一个姑娘和一个女人太不一样啦,这谁都看得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