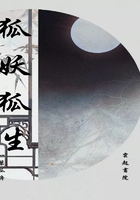法国现象主义美学家杜夫海纳认为,作为审美对象最重要对象的艺术作品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所有这样的审美对象都是“一个历史的纪念碑”。审美对象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基本保持一致的过程中,或死亡或再生,或消失或复活。一种新的审美对象也将依赖于历史为其指针的审美知觉。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艺术形式就应该停止自己的演变。各个阶段的发展决定的只是阶段自身的高度。而演变则决定的是整个艺术形式的发展。阶段上的发展终会达到不可逾越的高度,而横向演变,则永无尽头。这一点由中国诗歌的发展可以看得尤其明显。中国诗歌由《诗经》的四言为主演变为乐府的五言、七言为主,又演变为唐诗的严格格律形式,又演变为宋词的长短句(然后又有了元曲。但成就无法与前者相比)。各个阶段都有传诸万世而不衰的绝唱。然后是很多年的停滞,终至失去活力,几乎僵死。至清代黄遵宪等发动诗界革命,想用新名词刷新旧形式,结果是不伦不类,或有政治意义,却无艺术价值。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彻底摒弃了旧形式,连同陈旧的语言方式(文言),出现了白话诗,自由诗,中国诗歌才如江河之临春讯,重又奔腾澎湃起来。文学史上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格律诗词在唐宋业已写完,此说是颇有见地的。在现实主义社会观和浪漫主义人生观的艺术表象上或有独步的毛泽东诗词,由于因袭旧形式,亦不能在艺术形式上有革命性的建树。因而毛泽东同志本人尽管认为新诗“迄无成就”,也仍然劝诫青年不要写旧体诗词。以免“束缚思想”。确实,今天的中国诗界尽管也不同程度地出了某种困惑,但恐怕不会有人想到要用旧体来挽救新诗的所谓“颓势”的吧。
任何艺术形式都无疑是必须发展变化的。在某种意义上,形式的变革,即体现内容。中国小说由文言而至白话,中国诗歌由旧体而至新体,其中反映出多少历史沧桑,时代风云!(彼其时也,倡导白话文,发表自由诗,是要被遗老们指为“乱党”的。中国人为了丢掉一条辫子又丢落了多少人头)。自然,新形式的产生是在旧形式的基础上(往往受到外来影响的推动)演化而来的。但一经演化,则便是本质上的改变。即使有一天向自己的发端回归,那也必然是螺旋形的上升,完全处在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正如马克思在谈到“高不可及”的希腊神话时所说的:“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
由此可以说明,体现某一艺术样式在整个人类文化创造背景上的制高点的,只能是坐标横向轴后部阶段发展的最高点。弄清这种横向演变和纵向发展的关系,我们关于俗文学与纯文学的讨论就不至于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的庸俗圈子里无谓地兜来兜去了。某些通俗小说作家完全不必通过贬低纯文学或硬 以纯文学充数借以抬高俗文学的地位(这本身即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映),更不必以读者的恩人,以力挽当代文学大厦之将倾(实不必杞人忧天)的救主自居;某些纯文学作家也不必自视清高或是硬行挤进通俗小说作家之林故作屈尊之态来哗众取宠。至于纯文学作家写通俗小说,通俗小说作家写纯文学,抑或是“两栖”、抑或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各敲各的锣,各卖各的糖,只要是没有丧尽艺术良知,只要是真正执著的艺术追求,就更是于情于理于法皆不相碍的事,又何顾虑之有?还是多一些平心静气,多一些费厄泼赖,多一些自信自重,以共图当代文学繁荣发展之大计的好。
二律背反现象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
关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讨论,几乎同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产生一起发生,至少当代是这样。这类讨论,常常像其他文学讨论一样,在某些相似的问题上反复盘桓,以至形成颇有趣味的怪圈。其实,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同其他文学创作一样,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烦恼,引起似乎永无休止的争论和探索。又正是这些争论和探索,不断地提高和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只是这矛盾在其呈现的时候常常形成一种迷雾,这迷雾即二律背反。
真与伪
正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真实性。而且,他们还对如何达到这种真实性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这一品格,是由它所遵循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决定的。早在马克思评论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时,他就揭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这一认识基础。马克思的评论中批判了欧仁苏创作中所遵循的思辨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它指出,思辨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从观念到实在的方法,必然导致艺术形象的虚幻性,也就是使艺术内容失去客观实在性。他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他首先应该严格地区分主观和客观、意识和存在的界限,如实地把现实看做存在于人们意识之外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家、艺术家所描写的,不应该是思辨中的即想象中的现实,而应该是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即客观存在的实际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承认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承认存在于作家、艺术家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是艺术的源泉和出发点。因此,它强调艺术内容的客观性,认为客观性是艺术真实性的基础或前提。认为判断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是否具有真实性的标准,不是人们的主观意识,而是作品是否包含有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生活内容。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的客观性,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应有的素质;对生活的描写和反映的客观性,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最基本的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莎士比亚化”,即客观的真实而不是主观的真实,对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历史真实性是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特殊性,无历史即无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历史是前提,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必须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历史事实是有绝对性的,历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事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必须有充分的考据,充分地占有史料,并加以去伪存真的剖析,得出精确的结论,以为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提供实事求是的根据,使之最终恢复或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50页)。这是凡企图经由历史题材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社会观、人生观,道德伦理观和美学观的作者决不可以游离的基础。因而历史已经确定的情节是不可改变的。留给艺术创作的空间,只是通过对历史已经确定的情节及其发展逻辑的推理、推测、揣摩作出心理、细节、氛围的描写,以及作者对历史的思辨、评判、评价等等。实事求是是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经受历史考验的唯一标志。作者的任务是遵从历史的真实:不是作者去支配历史人物而是由历史人物支配作者。以史料增强历史的规定性,限制作者的随意性,从而给作者创作的典型人物增加依据性、参照性、真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特性在其现实的具体性中永远要比它的反映更丰富。许多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命运的跌宕变化常常超过艺术家最大胆的想象。使人不能不惊叹生活的惊心动魄、丰富多彩和曲折复杂。与此同时,历史小说的根本任务之一是经由秉笔直书的史笔,说真话、露真情、求真理,以教育后人,启迪未来。
总之,在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各种规定性中,作为它的生命或存在形式的,是直接的现实性或直观性。所谓直接现实性或直观性,是指事物或现象的实在的、具有感性形态的特性。艺术的真实性,就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来说,同样具有这种品格。这是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不同的。真理是理性的对象,它不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人们不能用感官直接感知它,而只能用思维才能掌握它;真实则不同,它虽然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却是以感性的形象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人们可以凭着感官感知它的存在。如果艺术所表现的内容缺乏直接的现实性或直观性,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即使浪漫主义艺术或抒情诗,哲理诗等等也不例外。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德国的所谓“倾向诗”和“倾向小说”在艺术上存在的缺陷,同样是因为这类文学的作者不善于再现具有直接现实性或直观性的生活真实。在我们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在从事历史题材文学时,既未在充分的占有史料上下工夫,也未在用历史唯物主义驾驭、支配史料上作更多努力,以至造成程度不同的片面性与表面性,把当代意识对历史的观照变成对历史的任意阉割与改造。重蹈马克思当年就表示过深恶痛绝的让人物穿着历史的外衣演绎今天的人事的故辙。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反题:艺术创作的中心问题乃是想象。无想象即无艺术创作可言。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既为创作,就必须接受艺术创作这一普遍要求的检验。艺术创作的真实,仅仅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真实反映的是生活(历史)的本质,而不是生活(历史)的表象——尽管哲学观、历史观和社会观的不同立场对生活(历史)本质的认识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比如,同是写梁山起义,有人写《水浒传》,有人写《荡寇志》),但在反映本质这一出发点上是完全相同的。至于在艺术表现过程中,艺术家着意描摹、状写生活(历史)的外观,那只是加强艺术真实可信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艺术真实只对自己的艺术使命负责,而无意于重复生活(历史)的真实;艺术创作只服从艺术使命的要求,而无意于对史学的要求承担责任。即便就表现生活的真实而言,艺术所表现的也可以是可能发生的事而未必是真有的事。我们判断一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是否具有真实性,不是根据作品是否写出了生活中的个别事实,而是用生活来对照,看它是否符合生活的情理,即是否合情合理。正如别林斯基在谈到席勒的《强盗》时指出的:“在这部作品里,没有生活的真实,但却有感情的真实;没有现实,没有戏剧,但有无穷的诗;状态是虚构的,情势是不自然的,但感情是真实的,思想是深刻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443—444页)。
艺术中的合理性,就是符合生活所固有的逻辑,就是符合生活中的因果律和必然律。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所描述的是“按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这就是说,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人和事,不一定是生活中实有的人和事,完全可以是按照客观的生活逻辑可能有的事。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这样要求文艺创作的。他们在评论拉萨尔的《济金根》时,批评拉萨尔违反了历史的真实,但是他们并没有拘泥于剧本是否忠于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看做品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是否符合历史的必然性。例如,拉萨尔在剧本的最后一幕写了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这在历史上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历史上的农民领袖弗里茨早在济金根暴动前几年就去世了。但是,恩格斯却肯定了剧本的这个情节,并且赞扬拉萨尔描写的这个农民场面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蛊惑者”弗里茨的个性也描写得很正确。又如历史上的济金根究竟与农民运动有没有联系,据恩格斯说是“无法判断”的,但他也不反对拉萨尔“假定”济金根与农民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他甚至不否认拉萨尔“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这些都说明,恩格斯要求拉萨尔的,并不是忠实于历史上个别的事实,而是服从历史的必然性。为了给济金根、胡登这些在前台表演的人物提供积极的背景,从而使贵族的国民运动显示出本来面目,恩格斯甚至为拉萨尔设想过把农民和平民运动引进戏剧的种种方案。并且,恩格斯还声明,他所“设想”的方案,仅仅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并十分肯定地说,恩格斯的“设想”所依据的决不是历史上实际存在或发生过的个别事实,而是历史生活和历史活动本身所固有的因果律和必然律。
历史题材的特殊性在于它确实提供了若干“真有的事”,但历史并没有提供所有“真有的事”。进一步言之,即便是那些由史料证明的“真有的事”也还不能否认其中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把这种不确定性变为相对的确定性是史学的任务。艺术家即便承担起这一任务,也并不能最终保证艺术创作的成功。恰恰相反,艺术家仅仅遵循生活的逻辑和艺术创作的规律,不关心甚至无视个别历史事实的真伪甚至有无,保持决定主题和基本人物性格的艺术构思的自由,完全依凭想象杜撰虚构出某种情节、事件和结局,甚至针对某些历史人物在一般大众中久已形成的形象特征,作完全相反的悲剧式或喜剧式的艺术处理,反而获得了极大的艺术效果。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而对历史事实所作的浅表的纪实性表现,满足的主要是一般大众心理的窥探欲和好奇心,与艺术的旨趣有相当距离。事实上,生活的原始面貌在其审美意义上永远比它的反映要贫乏。任何反映都不可能是一面纯客观的准确无误的镜子,任何主观折射都是会变形的。而艺术创作的变形则更是有意识的、主动的和积极的。这正是艺术创作的一种特权。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所描写的生活之所以比实际生活更真实、更可信,原因就在于作家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深切的体验,以及艺术家的匠心,把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和必然性揭示得更充分、更深刻,使读者更能看清生活的真实面貌,这也就是艺术有别于生活,比生活更典型的原因,拙劣的艺术家往往使真实的东西显得虚假,而优秀的艺术家则会使虚构的东西显得真实。被作家虚构的生活,其历史面貌虽然大为改观,却闪耀着比历史本身更为深邃、更为久远、更具永恒性的光彩。因此,历史事实只是引导艺术家进入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艺术思维广阔天地的线索,而决不应该成为决定以至束缚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的绳索。倘若把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钉牢在“史”的十字架上,则其“诗”化的翅膀也就无法展开。作家心游万仞的自由感也便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失落。当人们面对那些木木枘枘地在“史”的框规里爬行的平庸作品时,如何能不为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这种自由感的失落而付之以慨叹呢!
大与小
正题:这里所谓的“大”,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是指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选择重大题材;其次是指表现重大题材所概括的巨大时空;第三是指同上述二者相适应的小说的宏大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