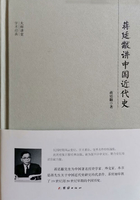鹦鹉螺号沿着西经50度坚定地向南疾驰。
3月14日,在南纬55度,我见到了一些小块的破碎浮冰,它们在海潮的冲击下形成了暗礁。一条炫目的白色长带在南面的天际闪耀,英国捕鲸人称之为“冰映光”,它预示着前方有浮冰区的存在。
果然,冰山不久后就出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的光泽随云雾的变化而变化,让我和康塞尔惊叹不已,但捕鲸出身的尼德·兰对此却见怪不怪。越向南走,一路上的冰山更多,无数的海鸟在上面栖息,它们铺天盖地的叫声让我们震耳欲聋。
尼摩船长常常站在平台上,从容镇定地指挥着他的潜艇在这些冰山中巧妙地穿行。
到了3月15日,我们驶过了南设得兰群岛和南奥克尼群岛的纬度。16日早上8点,鹦鹉螺号沿西经55度穿过了南极圈,我们身处在冰山的包围中。沉着的尼摩船长总是能灵巧地指挥着鹦鹉螺号顺利地向南行驶。但究竟要去哪里,我还是不知道。
我陶醉在冰山的千姿百态中,对这漫长的探险毫不厌倦。四周的冰山崩塌破裂的声音即便在水下也能清楚地听见。这时,冰山坍塌产生的巨大旋涡能让鹦鹉螺号颠簸得几乎失控。但就是在它被冰完全封住的时候,尼摩船长依旧能在冰原中找到出路解脱出去,再不然就指挥鹦鹉螺号猛冲,强行破冰前进,让人觉得惊心动魄。我断定,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了。
3月17日,鹦鹉螺号终于被冰完全封住了去路。这次的拦路虎竟是一片连绵不断、巍然不动的大冰山。
“这是大浮冰!”尼德·兰叫道。
中午,尼摩船长测得我们正处在南纬67度30分、西经51度30分的南冰洋深处。这里的冰山星罗棋布,远处的峭壁折射着太阳的光芒,犹如一面大镜子;这里满目凄凉,只有偶尔的几声鸟叫打破无边的死寂。鹦鹉螺号在这样的境地里只能停止不动。
“先生,”尼德·兰说,“您的那位船长要是能穿越这大浮冰,倒还是号人物。可惜,他是奈何不了大自然的伟力的!”
鹦鹉螺号现在被困在这冻结的冰层中不能动弹了。我看着眼前的情形不禁觉得尼摩船长也有他轻率鲁莽之处啊!恰在此时,尼摩船长已经登上平台看着我了。
“教授,您如何看待我们当下的情形?”
“明显被困了,船长。”
“被困?阿龙纳斯先生,被困的情形是不会发生在鹦鹉螺号身上的。我们还要继续开向南极呢!”船长语出惊人。
“您给您的潜艇安上翅膀飞到南极么?”我略带嘲讽。
“就一定要从上面过去吗?”船长平静地说,“我走下面。”
“下面!”我惊呼。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冰山水下的部分和浮出部分之比是三比一,按水上冰山的高度推算,它们在水下的部分是不会超过900英尺的。鹦鹉螺号就只需要储存足够用几天的空气,然后下潜到900英尺的水下,就算南冰洋完全冰冻,它也能用冲角沿对角线直冲而出。我将这些想法一一对船长说明后才发现,聪明的船长变主动为被动,弄得好像是我在催促他去南极了!
船长紧锣密鼓地招来大副,二人冷静地商议起来。
我将这消息告诉了两个同伴,康塞尔竟平静地用一句“只要先生乐意”就把我打发了。尼德·兰则耸耸肩泼起了我的冷水:“你们或许能到南极,但你们别指望能回来了。”
下午四点,船长下令关闭了通向平台的嵌板,我又最后望了一眼雄伟的冰山。十几个船员下船凿开了周围的坚冰。不久,鹦鹉螺号就开始下潜了。
我和康塞尔在客厅的窗后看见,鹦鹉螺号确如先前所料,在下潜到900英尺时就到达大浮冰的底部,它一直下潜到2600英尺的深海,然后沿西经52度向南极行驶。再过40个小时,我们就在南极了。
3月18日凌晨5点,鹦鹉螺号撞上了冰层,它缓慢地上升,反复尝试了一天,但都碰上了天花板一样的冰墙。直到晚上,仍没有多大好转,但鹦鹉螺号依然坚持着试探性的上冲。
第二天凌晨三点,我发现浮冰底部的冰层在150英尺的深度就被我们碰上了,浮冰一点点地变成了冰原。
鹦鹉螺号沿对角线缓缓上升,慢慢地,冰层越来越薄了。
终于在3月19日这值得纪念的一天,凌晨六点,尼摩船长推开客厅的门,对我说:“自由航行的大海到了!”
我飞奔至平台,是的,我们又在没有冰封的大海上了!眼前只有一些散乱的浮冰,远处辽阔的海面波光粼粼,空中鸟群飞翔,水下鱼类遨游。
“这是在南极吗?”我问船长,心怦怦直跳。
“不知道,中午要测定方位。”他回答。
南面10海里处有个露出水面700英尺高的孤岛,它的周长四五英里,一条狭长的水道把它和一块辽阔大陆或是大洲隔开。船长、我和康塞尔,还有两名带着仪器的船员乘小艇到了海滩。康塞尔正要跳下小艇,被我一把拉住了。
“我想,第一个踏上这片陆地的特权应该属于您。”我对尼摩船长说。
“如果我毫不犹豫地踏上这南极的土地,一定是因为迄今还无人在这土地上留下足迹。”
船长说完,轻快地跳上了海滩,显得异常激动。他爬上一个岬角的岩石顶上,交叉双臂,静默不语,好像他已主宰着这个地方的!五分钟后,他才转过头对我们喊道:
“先生们,上来吧!”
我和康塞尔跳上海滩,两个船员留在艇上。这块土地上有大片红色的火山岩,证明这是一座火山岛,但却看不到任何火山的影子。这是块荒凉的大陆,地上动植物有限,但空中却充满生机。各种鸟儿在空中飞翔,一群群海燕挤在岩石上,我们走近时它们还亲热地聚到我们脚边。另外还有鸽子一样的南极水鸟、炭黑色的信天翁、弓形的大海燕、黑白交错的海棋鸟、腹部多油脂的南冰洋海燕等等。走了半英里远,地上布满了企鹅巢,无数产卵的企鹅从里面爬出。后来尼摩船长猎杀了好几百只,因为它们的肉很好吃。
直到上午11点,太阳也没有出来,所以不能测定方位。我心中烦闷,船长也沉默地靠在一块岩石上,似乎也在犯愁。中午过后,天空慢慢飘起雪来,船长便毅然决定回船。
暴风雪持续到第二天才停止,期间鹦鹉螺号又向南行驶了十海里左右。我希望今天能测定好所在的位置。没见到尼摩船长,我便和康塞尔上了海岸。
我们见到了一些温和的海豹,我们靠近后他们也没逃走。现在是早上8点,离我们有效观察太阳的时间只剩四个小时了。我走向岸边被悬崖包围的海湾,目之所及,全是这种哺乳动物,它们布满了这块陆地!
又往前走了两英里,一座直插入海的岬角挡住了我们去路。从岬角的另一边,传来很大的像牛一样的吼声。我们艰难地爬上了岬角,向下一望,一片广袤的白色平原上满是海马,它们正欢乐地嬉戏玩闹,发出欢快的吼声。海马的下颚有两根30英寸长的粗大门牙,这两根门牙质地比象牙的坚硬,不易泛黄,很受人类青睐,因此海马每年要被捕杀4000头以上,已濒临灭绝。现在,这些珍稀动物就在我眼前,它们红褐色的皮又厚又粗糙,毛短而稀疏,有些足有13英尺长。
观察完海马,我们沿一条陡峭的斜坡返回。11点半,我们到达了登陆的地点,见小艇把尼摩船长送来了。他正在一块玄武岩上眺望天边,仪器架就在他的身旁。正午已到,太阳还是没有露面。今天是3月20日,明天春分一过,这里就要进入六个月的极夜了。我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船长,他也意识到了这点,但他说如果明天太阳出来他还是能测定方位,可不是靠测量太阳的高度,而是在明天正午,如果太阳被北方的地平线一分为二,那我们就在南极点上了。
船长说完就回船了,我和康塞尔则在海滩上逗留到了下午5点。我们捡到一个纹路很像象形文字的大海雀蛋,回到船上后把它放进了客厅的陈列柜里。
晚餐后我就回房睡觉了,睡前虔诚地祈祷明天有个好太阳。
第二天,3月21日凌晨5点,我登上平台时尼摩船长已经在那里了,他说今天可能出太阳。于是早餐后我和他及两个带着仪器的船员就登上了小艇,9点,我们到达了海岸。
我们花了整整两小时才登上了一座尖峰。站在峰顶,伸展到北面海平线的辽阔海洋尽收眼底。脚下方是晶莹炫目的冰原,头上的天空蔚蓝无云。北方的太阳,已经被地平线切去了一角,游动的鲸鱼在海面喷出众多壮观的水花,鹦鹉螺号也如同一条在远处酣睡的鲸鱼。
差一刻正午,通过光的折射,我们看见太阳如金盘一样升出,在这荒无人烟的大陆上投下最后的光芒。船长用他那特殊的能矫正折光的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渐渐下沉的太阳。如果正午时分太阳刚好有一半没入了地平线下,我们就在南极点上了!
“正午!”我喊道。
“南极点!”船长庄严地宣布。我接过船长递来的望远镜,透过它,我看见了太阳被地平线切成两半。
“船长,用谁的名字命名这大陆?”我问他。
“我的名字!”
他说着,将一面黑色的旗帜展开,上面绣着一个金色的字母“N”。接着他转身面对着天际那还有着余晖的太阳,大喊道:“再见了,太阳!去自由的海底安息吧!让六个月的黑夜将它的阴影笼罩在我的新领土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