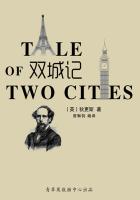是有一天我们去赴一个同学的婚礼,席间有人无意中开玩笑,说:莫北,你不会毕业的时候又一个人作逃跑新郎吧?莫北几乎是想也没想,便回道:当然不会,而且即便是我逃跑了,安安也会追随我一块逃到那个城市的。有人便笑,说:没有问安安就那么自信吗?莫北的脸,在这句话里窘下去。而我,亦在莫北的回答里,突然地想起那个收到莫北短信的毕业前的夏日午后。很快地有人将这样尴尬的话题岔开去,我和莫北,却是不约而同地,再也无法参与到热闹的闲聊中去。
回程的车上,我们一路沉默。快到站的时候,莫北突然问道:安安,你会不会跟我走?我看着窗外飞快滑过去的单调的沙滩,冷冷回道:弥补之后,你,还是会逃。莫北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握过来。那么温暖又有力的掌心,可是我却感觉不到它任何的温度。原来一切的重复,还是会走到那个冰冷的尽头。
我想了一个长长的夜,终于在黎明的时候发短信给莫北。我说,莫北,让我们都感谢命运赐给我们的这段冷而少的相聚;感谢它让我们明白,爱情不是侯鸟,冬天走了春天还会再完好无缺地回来;所以我们要在以后的路上,学会珍惜,而不止是弥补。亦让我们各自对彼此说五个字:对不起,谢谢。这于你我,已是足够。
爱诱
她向来淡定从容,对人对事,皆波澜不惊,走到这样无情的一步,连她自己,都大大吃了一惊。
她与他的相识,是再老套没有。
她是一个平面广告设计师,在业界也算是小有名气;而他,则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骨干,素日穿梭于客户于设计师之间,在行业内也有一定威信。职业使然,让他对她,了解颇多;而她,因了从不会主动与人交往的个性,则使得她对他,完全陌生。
是他先打来的电话,彼时她已经辞职,在北京飘着,慢慢做一本自己喜欢的画书。要约她为某个厂家的背包新品,设计图案。这样的电话,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个,所以她并未放在心上,只说会在最后的期限,交上图案。他却多说了几句废话,与她套着近乎。原来他也是苏州人士,与她虽不同乡,但同一个城市里出来,在这个人际淡漠的北京,也算是老乡;只是,能与她这样的才女同乡,他心底多有惶恐。她听了只淡淡一笑,当然是对于他的拍马,不怎么放在心上。
挂掉电话,她便将他忘记,继续读书画画,安静生活。她租的四合院,平素极其安静,皆是上班的年轻人,不像她,无需早起,亦不必在下班后,乘公交,换地铁,长途跋涉,方可到家。所以日间里只闻鸟语花香,不见人声鼎沸。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所以在第二日,她在院中洗漱的时候,手机短信频繁响起,让她颇为惊讶。几次去看,竟都是来自同一个号码,努力地去想,又到通话记录里去查,才终于想起,这个问候她早安,又找了刻意修饰过的语言,试图将她打动的男人,原是昨日找她的那位“老乡”。
她不是个冷淡到绝情的女子,所以习惯性地,对他的每条短信,都给予简短的回复。这样的结果,是招来他更浓郁的热情,一条条地,让她几乎有些招架不住。这样的攻势,让她终于觉得有些烦,不再搭理。但他还是执着地,通过短信、QQ、邮件,甚至包括快递的鲜花,来对她示好。
她其实有一个相爱的男友,只是在另一个城市,且放任她在北京游走上两年,再回去工作。所以很久以来,她因了这种稳定持久的爱,而对其他的男人,皆不感冒。接触到的人里,也有许多,给她写过情书,送过玫瑰,说过甜言,但都不长久,不过是泡沫般,便化为乌有。而她,当然也就随即将这些男人,忘在了脑后。
但这一次,却有了不同。
是她闲来无事,随手点击了他发过来的自己博客的链接。页面上,是一篇关于他在业内出色成绩的综述,看上去繁花似锦,葳蕤茂盛,但她对这样的虚荣,并不关心。她带着一点点的好奇,键入他在其上,链接的私人空间。
打开来,果然除了工作,还有他记录的生活的点滴,以及,他的家庭。她从零星的日志里,知道35岁的他,有一个算不上漂亮但也悦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有那么几张全家福,看上去,幸福无懈可击,下面陌生人的留言里,是微微的嫉妒,说,看这一家,多么完美。
而她,就在这样的完美里,突然觉出生活的可笑。看似无瑕疵的一个男人,却背着信赖自己的妻子,发暧昧的短信,给刚刚结识且未曾谋面的女子。而这世上,又会有多少这样微笑着探出头来闻墙外花香的男人?又有多少女子,以为自己活在甜美的爱情里,却不知,旁边的那个人,一只臂膀揽着她的腰,另一只,却伸了出去,采摘路边芬芳的花朵?
明明知道那甜言蜜语是无底的陷阱,下去,便出不来的,但她还是没有能够抵挡得住,答应去一家新开张的咖啡馆里,赴他的约会。其实她对他的敞开里,带着那么一点少女的狡黠与邪恶,她想要去看看,这个想要偷吃新鲜桃子的男人,究竟,会如何探出他的左臂。
那个阳光微凉的午后,她带着一点点的保留,和故意探出一朵花来的诱惑,与他弯来绕去地,玩着语言游戏。尽管心内对他,始终保持着距离,但,还是被他专业的素养,及其外在的风度,幽默的谈吐,给稍稍地吸引了去。这的确是个让女子心动的男人,知道说什么样的话,才能讨得女人的欢心,她开始怀疑,自己此次赴约,是否真的像自己认定的那样,是毫无城府的。他是个并不讨人厌的男人,不是么?
临走的时候,他开玩笑似的,过来握她的手,跟她道别。她犹豫了几秒钟,还是伸出了右手,放入他宽大又极富温度的掌心。
他潮湿温热的左手,当晚,在她的梦里,再一次,温柔地抚过她的右手。
第二天清晨,她还没有睁开惺忪的睡眼,他便发来短信,问她早安,又让快餐店,给她送来一份早餐。
她吃着酥软可口的蛋糕,喝着香浓美味的牛奶,突然就想,与他聊些什么。哪怕,只是说一句谢谢。她飞快地打开电脑,登陆Q。他的头像,是灰色的。带着一点点的失落,她打下一句话:谢谢你的早餐。落寞地要关掉窗口的时候,他的头像,突然亮了起来,且很快地回复过来一个微笑的小人儿,说:喜欢吃么?
她绕过他的话,但却发过去一朵羞涩袅娜的莲花。她的心里,那一刻,真的是有纯白的莲花,一瓣瓣地,悄无声息却又任性放肆地,绽放开来。
她从没有像那一刻,在一个中年的男人面前,如此袒露无遗地敞开过自己。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有些喋喋不休。他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听众,用柔软的话语,慢慢地开启着封闭了许久的她。
这样说了不知有多久,他突然转移了话题,问她,能否,将昔日她认识的一些客户的联系方式给他?他近日想要刻意地提升一下自己把握市场的能力,所以要与一些新的广告客户建立联系,而曾经被众多商家青睐的她,定能给予他这份帮助。
她当然毫不犹豫地,将手头所有的商家信息,及其有用的资料,全都发给了他。又说,他可以借助她的名义,再从他们那里,打开跟多的窗口。
他连连感谢,说,有时间一定要当面谢她。她不知为何,听他这样忙不迭的一句谢谢,心里高涨的热情,突然急剧降了下去。
她没有说再见,便关了Q,起身去画那幅没有完成的莲花。她画了许久,画到天色暗了下来,光影在室内氤氲盘旋着,直至将她完全地罩住。
而与他相识以来,一直热闹的手机,在饥饿袭来的时候,却没有如约响起。
她终于意识到,原来生活中那个滑稽可笑的人,不是他,而是自己。他不过是一只手,触碰到了她的花瓣而已,而她,却痴傻地,想要将一整朵,都呈献给他。
她等了许多天,终于还是,没有收到他的只言片语。似乎,他根本就没有在她的世界里,存在过一样。
她第一次,对一个并没有真心在意过的男人,撕裂般地,有了疼痛感。她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弥补这样蚀骨的疼痛。
她像陷入了某种疯狂的漩涡之中,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留言,发短信,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咖啡。而他,亦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敷衍她突然席卷而来的热情。要么隐身,要么关机,要么哄骗她说,在忙于工作。
可是,她不是那么好哄骗的,她从他得到想要的东西便沉寂无声的那一刻起,便知道,这场仗,她是打定了的。无论如何,她,都是要赢回那曾经失去的自尊的。
她的百般攻势,终于让他无力阻挡,不过是几个来回,便溃不成军,缴械投降。她开始像一根藤蔓,悄无声息地,攀附着他,向枝干爬去。起初,并没有人注意到她,以为她与他,不过是以朋友的身份,出席私人的派对。但,当她爬到了那最高处,且将一朵一朵娇艳媚惑的花,开遍他的身边时,所有人,这才诧异地发觉,原来,一向自称婚姻幸福家庭美满的他,竟是同时踩踏了两条船!
这其中,当然包括他的妻子。
一次全公司的会议上,他的妻子,大闹会场,致使他的这桩绯闻,在公司上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了解的,说他是咎由自取;不清楚的,责她第三者插足。
但,她早已不在乎什么声名,北京,原本便不是她的居所,她不过是飘在其中的微尘,碰巧,有那么一点,落在这样一个世俗的男人身上,便成了一块洗不掉的难堪的污痕。
她在听说他辞职后的第二天,便换掉了所有的联系方式,而后离开北京。
她记得那是夏末秋初的清晨,天很明净,阳光透过树隙,洒在她的颈上,酥酥麻麻的。蝉鸣已经少了,而她,早已经将这一切混浊晦暗的过往,淡漠地忘记。
我只为你绽放
我从没有告诉过柏,我认识他已有许多年。或许他永不会相信,我曾像一个侦探一样跟踪了他六年。我整个的年少时光,都给了他。而他,却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
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相距不是很远,但相识的可能性,却是极小。他住在戒备极严的富人区,我偶尔骑车子过去溜达,远远地便会被门口的警卫,当作贼一样地密切监视起来。柏当然不会去我们居住的“贫民窟”,那里靠着嘈杂的市场,穿过那么长而脏的集市,会把他名牌的鞋子和衣服弄得污浊不堪。我穿着哥哥宽大的白T恤,还有姐姐褪色了的牛仔,斜挎着帆布的书包,晃荡在其中,常会因为短短的头发,和没有发育的胸部,被无事可做的小痞子误认为男孩。
这是我的生活,我从一出生的时候便极力想要逃脱掉的混乱贫穷的生活。妈妈总说我太过痴心,常做不可能的美梦,希望飞到城市另一端的富人区里去,这样不安分的妄想,迟早会让我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听不进她的话。我依然向往着像柏一样地生活,或者,找一个像柏一样富有的男人嫁掉。
或许就是这样,我才会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只为在那个经常堵塞的十字路口,会见上一眼那么炫目的柏。隔着十米远的距离,我会看到孤独又冷漠的柏,那么高傲地单脚着地,只等着交警的手一挥,便朝东郊的学校飞驶而去。
那时的我,总盼着堵塞的时间会再长一些,或者,我犯了路规,被交警罚去举旗。如果时间允许,我乐意这样举着旗子,站在被四面八方的行人都可以看到的位置上,等着神情淡漠的柏,不经意地将视线扫过来。但柏,却是从没有望过来。或许他曾注意过我,但和那些小痞子一样,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否则,几年后当我终于引起他的注意,他的眼睛里,写满的怎么会全是陌生。
我就这样把学习外的光阴,都给了柏,直到六年后我读了大学,将打工挣来的钱全买了衣服来打扮自己,又跟着乐队频频地去邻近柏的大学里演出,让柏终于注意到那么张扬不羁的我。
我知道很多的女孩子都在追求柏,拿了与她们一样鲜嫩娇美的花送给他,只为奢望他能对她们微笑。我没有钱买花给柏,我亦不会这么傻。我在许多年前就懂得柏,他喜欢的东西,是不能用钱买来的。我只是若即若离地诱惑着柏,我带别的男孩子到柏常去的酒吧,有时候也会有陌生又有钱的男人。我点很昂贵的红酒,而后在这些一脸心疼的男孩或男人的视线里,望向角落里的柏,又在他望过来的时候,向他遥遥地晃一晃酒杯,而后与身边的男人,亲密无比。
我在柏常去的每一个地方守候着他,不经意地用视线引诱着他;又无数次地与他“偶遇”,碰触到他温凉的手臂。柏的心,终于从许多女孩子的包围里,走到我的身边来。我记得清楚,那天我唱完歌,回到后台,和一群男生嬉笑打闹,柏安安静静地朝我走过来,我笑看着他,手依然搭在一个男生的肩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着柏,他那么高,我昂着头,脖子几近酸痛。柏说,琼,我让你做我的女朋友。我依旧笑倚在另一个男生的肩头,说,好啊。
我就这样让柏爱上了我,在我认识他八年后。柏不知道我的过去,我只是告诉他,我和他住在相邻的城市。而柏的过去,我一直清楚。我在柏向我求爱的那个晚上,叫上几个哥们,去酒吧里欢歌。他们问有什么喜事么,我说一个有钱的男生爱上了我,当然是喜事。他们便都举杯向我庆贺,说那要记得替我们好好宰他哦。
我把哥们的话嘻嘻笑着告诉柏,柏直直地看着我,说,琼,你爱我的钱,还是人?我坏笑着看他,回道,当然是钱,我是个活在物质里的女孩,你早就应该知道。柏摇头,道,可是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直觉告诉我,你和别的追求我的女孩子是不一样的。我将手里的哈根达斯在柏眼前晃一晃说,那我们谈谈看,小心我让你破产哦。
我不必再去打工养活自己,有了柏,我就有了一切。年少时对物质疯狂的渴求,还有做回漂亮女孩子的迫切愿望,柏为我一一地实现。我在他的身边,像一只飞蝶,终于从梦中苏醒,破壳而出,在阳光下绽放出最绚丽夺目的光彩。
没有人知道我那时的心情,我当然不会告诉柏,告诉他煎熬了我整个青春的痛苦,曾被父母骂过的狂妄的理想,穿着男式的T恤被痞子们抓住扁平的前胸时的愤怒,在那条污浊的集市上看到父母被市霸踢打时的绝望和恐惧;这些,爱我的柏,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他对我的爱里,与过去无关;而他的过去,却曾经那样强烈地刺激着我。就像如今,我在柏爱与物质的双重呵护里,突然被一种混合了羞耻、征服和欲望的东西,强烈地攫取住一样。亦是这样一种柏不明白的东西,让柏为我迷失掉自己。
我在疯狂玩走的大学里,花掉了柏数不清的钱。我因此不再隐匿住的青春,让我在昔日的朋友们面前,可以像我发育完美的胸部一样,那么招摇地昂起头来,将那些曾经鄙视或讥笑的视线,一一地扫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