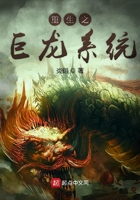恩将仇报!这是真澈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亲眼目睹同伴被妖兽屠戮殆尽,自己肝胆俱裂侥幸逃生,然而还未来得及庆幸,恶魔再次降临。绝处逢生,愈加惜命,为了保住自己这条得而复失的性命,不惜对救命恩人暗下毒手推下马去,以求多得一分逃出生天的机会。怀抱野心和欲望在这蛮荒之地求生,或许这才是应有的生存之道。
真澈见识过人心之恶,至交反目、兄弟相残的事都是平常,被救助的人反咬一口又算得了什么呢。可他还是为被背叛而惊愕乃至愤怒:
姑娘你倾城国色我见犹怜,怎么能干出恩将仇报这种如此没有格调的事!
他十一岁被阿宛所救住到清桐苑,阿宛待他亲厚无间不说,园中歌伎舞姬或自真心或看阿宛之面,也都对他温婉可亲。后做游侠四处闯荡,那些粗犷彪悍的女佣兵纵有心计脾气,常年山野奔忙风吹日晒的,又能好看到哪里去?所以在他的印象里,姿容艳丽的女儿家,品行大都不会差——原谅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少年吧,他不姓张,没有一个女人在他开始伶仃漂泊前告诉他: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林月容并没有趁机逃走,反而将青骓带住停了下来!
美人披着如霜月色从马上下来,冲营地那边喊了一句:
“别看啦,过来把他弄回去。”
然后冲地上的真澈嫣然一笑,盈盈屈身道了个万福:
“重新认识一下,煌州云氏女,单名一个澜字,见过李郎。”
真澈有些懵,怎么回事?她还有同伴?我这是……中了什么圈套吗?云澜看他一脸疑惑只是笑而不语,牵着马缰转身朝营地走去。
正恍惚间,真澈忽觉得脸上似有人在吹气,一扭头,顿时一阵酥麻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
一张毛茸茸的大脸,两颗如玉的大牙,月下泛着光泽的银色皮毛,还有那一双如有熔岩暗涌的金色瞳孔——正是那如白玉豹一般的异兽!而还未等他叫出声来,就觉得身子一下腾空,竟是被这兽衔着衣甲叼了起来。
云澜牵着青骓在前,异兽在后面叼着真澈连拖带拽的把他又弄回了猎妖师营地。
真澈此时才有点明白过来:这女人根本不是猎妖师,她和这妖兽是一伙儿的!自己早该想到,她若是被妖兽所伤,臂上又怎么会是刀剑创。想来她和这群猎妖师很是恶斗一场,将之尽数屠灭,自己也筋疲力尽受了伤。荒山月明夜,杀人放火天,谁料正碰上自己这个孤身就敢走夜路的。可笑自己还高声问礼,提醒她做好准备,简直是浴后空手入虎穴了。只是她若能和一妖兽合力斗杀十余猎妖师,自己对她毫无戒备,猝不及防必遭毒手,又何必演戏敷衍拖了许久才动手呢?
不过如此说来,是自己大意入她圈套,那救命之恩就无从谈起了;既无救命之恩,那就更说不上恩将仇报了。勾连起这番歪理,真澈竟觉得某处心弦放松了下来,甚至不顾自己性命之危对那云澜起了一丝激赏之意:
入其彀中是自己心智不敏技不如人,怨不得别人;她能调教妖兽为己所用,又连施巧计将自己放倒,这份才能急智也足以行走天南了。便是虐杀了这群猎妖师,说不得也是一群恶汉见她孤身貌美心怀不轨,不料人家有后招而被反杀。
为了自己那被阿宛调教的世界观不被摧毁,真澈这番推想也堪称绝妙了。
这厢云澜将青骓马上的行囊解下丢在地上,翻了几下,一扭头正见真澈看着自己发愣。少年的脸上一派从容淡定,非但没有恐慌,反而在嘴角挑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不由得在心中暗赞一声:好胆色!
啪的一声打了个响指,云澜指了指真澈,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了!”
少年身子动不得,只是撇撇嘴,
“显而易见。”
“我不会杀你。”
“哦,多谢?”
“想知道为什么吗?”
少年冲她歪头一笑,
“因为我是个好人。”
云澜愣住了,盯着这个小郎君不知她是真傻还是真无畏。她行走山南多年,从来奉行的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是这幅容颜却如能让人神魂颠倒的秘药,引得无数英雄豪杰都想要“犯”她一下,按照惯例,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下场都很惨。而讽刺的是,闯荡多年因她而死的人远多于兽,虽然她真的只是个猎妖师。
三天前加入这支来自煌州的队伍时,还只是两三个人看她的眼神有些不对。至今夜在此扎营,在那个貌似宽厚的头领的默许下,几乎所有人都意图对自己施暴——他们在自己的汤里下了软筋散。这也是为什么真澈来时,她之所以浑身无力了,那不是伪装,而是药劲未散。
之后的事情就是曾经悲剧的再一次重演,她奋起反抗,他们持刀威逼,在药劲发作不慎负伤后,那个自己最亲近的人被激怒暴走了。
血雨腥风,惊惶哀嚎,尘埃落定……
此间的真相和真澈的推断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者只是一个外貌协会成员幼稚且浅薄的臆想。不知两人知道对方的想法后又当作何感受。
真澈的到来是云澜没有料到的,毕竟几乎没有人会在夜半时分行走在山南的山野间。真澈的招呼传来时,暴走者去追逐逃窜的落网之鱼,她浑身无力的倚着帐篷休憩。无法躲避就只能面对,瞒住对方然后拖延时间,这是她唯一的计策。而危险就在于,如果自己欺瞒不住亦或来人看到她后同样意图不轨,那她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万幸,她遇到了一个好人。
好人就该有好报,云澜就这样看着真澈,展颜一笑,明媚动人,
“不错,你是个好人,所以我不杀你。作为对你刚才给我疗伤的回报,我允许你赎回自己的自由身。”
她一屁股坐在真澈的行囊上一摊手,
“现在,开个价吧。”
真澈愣愣怔怔的有点摸不着头脑,搞不懂这姑娘脑子里怎么想的,对一个好人勒索钱财居然可以说的这么理直气壮。但山南从来都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句话他还是听过的,那女人旁边的妖兽还卧在那里盯着自己舔舌头呢。
“我的皮囊里有一个暗袋,里面有赤金五十两,你可以拿走了。”
真澈很肉痛,阿宛给的程仪就这么没了。
“不不不,我想你误会什么了……”
云澜一脸笑容的摇了摇头,指着坐着的皮囊道:
“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已经不属于你了。我是说,你得另外掏钱赎身。懂?”
“你怎么不去抢啊?”
“那你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
真澈被噎的哑口无言,有那么一瞬间,他都觉得眼前这女人被阿宛上身了。要不就是她专门派来玩弄自己的——这事儿她干得出来。
丢开不切实际的幻想,真澈咽了口唾沫,试图以理服人。虽然这四个字向来是弱鸡的专属用语,眼下也顾不得了。
“云姑娘,我只是一个穷困的游侠,你看我的年纪像是存了很多钱吗?行囊里的哪点金子已经是我的全部储蓄了呀。”
“你的马是北地良驹,在南疆一匹能卖到赤金两百两;你的靴子是西陵乘风阁的,走南荒的没几个人能穿得起;你束甲的蹀躞带头上有个云篆的薛字,那是慈航斋大匠作薛子渡的花押。”
云澜拍拍手道:“你没钱无所谓,你家里有钱也是一样的。”
天可怜见,这身行头都是阿宛给他置办的,哪知道会在这上头露出破绽。
“如果我亲眷不愿赎我呢?难道你还要杀了我不成?”
“我当然不会食言杀你。”
云澜闻言笑的越发灿烂,
“我会把你卖到煌州的青楼里做兔子!”
“刚从南荒回来的那些莽汉憋得狠了,只要细皮嫩肉,可不分什么雄蕊雌蕊水道旱道。有的还偏偏好这口呢。”
贱人!烂娼!蛇蝎毒妇!
真澈所有的淡定从容连同先前对云澜的那一点欣赏瞬间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