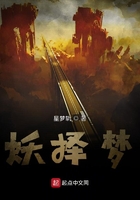我们来到黑城脚下。古城静极了,听不到一丝声息,迎接来客的只有拂面的沙雨。
一行人从西门进城。西门外有瓮城,呈方形,入口朝南。进得城来举目四望,但见满目荒凉景象,瓦砾废墟,断垣残壁,被四堵土墙拱卫着,天幕下,酷似一具硕大无比的扶乩沙盘。
信步城中,在流沙掩盖下的街区巷道仿佛可辨;衙门府第、寺庙佛坛、店铺民居的遗址分布其中。民居中的灶台、火炕和土仓历历在目。在城内北区的一座佛寺遗址露出的断垣下,我轻轻拨开半掩的沙土,露出的是一尺见方的残壁,拂去尘土,犹见彩绘丹青,衣袖飘洒,只是分不清是佛还是菩萨了。漫步城里,不时可见弃于路边的磨盘石臼,还可拾到古钱、陶瓷片、玉饰、朽铁用具与青铜残片以及残绢、麻鞋等物。我们也随手捡了瓷片、瓦当、滴水、铁钉等作为纪念物。
寻路登城,城墙高达十余米,夯土筑成。城垣两侧,到处是漫过墙体的黄沙堆积,极难攀登。我们仍走登城道,沿西北甬马道爬上城头,眼前豁然开朗。附着于西北城角的圆形角台上,一座高达十余米的覆钵式喇嘛塔,巍峨挺立着,成为黑城的标志和象征。城垣外的流沙装饰了的马面,如铆钉般的加固了。城外,干涸的河道循城自南逶迤东北而去,隐没在茫茫沙海中。
伫立城头,沙雾迷蒙,眺望天边,沙浪起伏似波涛汹涌。我屏息着,不愿惊扰这悠悠思绪……
看着那遍布城内外伤痕累累的盗坑,你能分辨清楚是哪个强盗干的吗?
那是1908年的初春吧,一队由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领的全副武装的探险队,越过那条干涸的河床,欢呼着,跳跃着奔向黑城来了。进城后,从4月1日到13日,科兹洛夫和他的手下人在城内的官衙、民居、寺庙、佛塔遗址上到处乱挖乱掘。科兹洛夫本人在日记中就曾自供,他和他的手下人“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断呀,都干了”。初战告捷,战利品有佛塑、麻布和绢质佛画、钱币、金属碗、妇女饰物、日用器具,佛事用品以及波斯文残卷,******教写经和西夏文抄本残卷。在城西南的一座佛塔中就挖出了“3本西夏文书本和30本西夏文小册子”,一下子装满了9个俄担箱(1俄担=16公斤)。这批文物立即通过蒙古邮驿分批经由库伦运往俄京圣彼得堡。
黑城的发现震惊了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副会长格利戈利耶夫立即通知科兹洛夫,取消去四川的计划,重返大漠黑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再次探寻发掘。
1909年6月4日的一个早晨,科兹洛夫又一次率队进入黑城,他们在城内西墙一栋大屋遗址旁扎起了营帐,雇用了当地土尔扈特蒙古人给他们运水、运粮和挖掘土方。科兹洛夫把他的手下人分成两组,从城内到城外的远近荒漠、残垣断垒中搜索探察。科兹洛夫亲眼看到一年以前他们挖掘的地方,还保持原样;他们当作废物扔掉的东西,也依然无人动过。天气渐渐热了起来,白天地面气温被太阳烤灼,高达60摄氏度以上,热浪扬起的沙尘令人窒息。他们就利用早晚干活。尽管日有所获,但已不能满足科兹洛夫已增长的贪婪欲望。科兹洛夫又派人到城外探察,在西城外不远处干河床右岸的几座佛塔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果然,一座高大的佛塔与其中藏有的大量书籍、文献、佛画、塑像和种种宝物展现在他们的眼前。
从6月12日至20日,发掘佛塔的工作进行了九天,由于发掘不是科学地有序地进行的,没有留下完整的发掘报告。根据科兹洛夫的日记和著作中的有关记载,大致的情况是:这座塔也是一座覆钵喇嘛塔,高约十米。方形基座,阶式上收的塔刹,塔顶半陷。塔内底部约十二平方米,四周平台上摆放着泥、木彩色塑佛。平台中央立柱,周围是喇嘛塑像,面前摆放着大型的梵夹装经卷。塔的北墙有一具坐姿势的骨架,四面墙上挂满了佛画。塑像和墙壁间空隙处,紧密地叠放着成百上千册的书籍、经卷和卷轴画。书籍和经卷大小尺寸不等,装帧式样各异,有的是各色的绸绢与花色封套,井然有序地堆放在一起,越往上部,越显得杂乱无章,可能与塔顶塌毁有关。塔中取出的书籍经卷,是用大帆布包了运到城中营地的,他们无法辨识其文字和内容,只好按外表形状进行“分类”,造成次序混乱与后人整理研究的极大困难。
佛塔中发掘的宝物太多了,致使科兹洛夫无法把它们一次运走。于是,他在离开黑城之前,挑选出一部分佛像和物品,大约有五十件,藏在了城南的一座壁龛中,然后填了沙土,准备再次来取。据说1926年科兹洛夫再到黑城时又运走了一部分。
科兹洛夫究竟从黑城盗走了多少文化宝藏?在这里我仅举出1926年12月8日,科兹洛夫在俄国的讲演中自供道:“19年前曾从黑城废墟运出40驼,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2.4万卷。”他还举出佛塔中发现的一部西夏文字典,就能帮助读懂其中的700卷西夏文书籍。佛塔中仅佛画就有537幅……
够了,我在这里不想再提那个英国强盗斯坦因和美国窃贼华尔纳了,不愿再触动黑城太多的痛楚了。据说1935—1936年间,日本在额济纳旗设立特务机关,曾先后数次派汽车至黑城发掘过。日人秘而不宣,详情亦无人知晓。
凡来黑城的人都听说过黑将军的故事,或者说他们都是听了黑将军的故事后被吸引到黑城来的。故事是这样的:黑城为西夏故都,末主号称黑将军,武勇盖世,与中原王朝争雄。中原边将闻警亦率师讨伐,与黑将军遇于黑城东边。黑将军出师不利,退守黑城,中原大军四面围攻,久攻不克,因以沙袋堵塞城外河流,以断城中水源。守城军民于城西北掘井取水,深至八十余丈,犹涓滴未见。黑将军欲倾全力作最后一战,出战前,将府库所藏黄金白银及其他珍宝八十余车,悉倾井中。遂手杀其子女及二妻,免污于敌手,然后亲率大军冲出北城,身先士卒,直麾敌垒,终因寡不敌众,自刎而死。中原大军攻入黑城,大肆搜索,而井藏竟未找到。以后不知有多少人冒险来到黑城,都是为探宝找宝而来。
漫步黑城头,在用土坯砌成的无垛口矮矮女墙下,触目皆是一堆堆拳头般大的石块,传说那是当年黑城居民抵御入侵之敌的武器。可是后来黑城废了,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任强盗和窃贼们作践、蹂躏。悲愤不禁涌上我的心头,默颂我的《黑城记事》:
黑城屹立戈壁间,
风沙漫漫越千年。
街衢繁盛遗址在,
农事兴旺阡陌现。
老盗挖坑捆载去,
新贾待价入市廛。
将军应愧不战死,
城头石垒是碑传。
(1976.9.17)
黑城的大门自从被科兹洛夫打开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当1900年俄国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曾试图寻找黑城时,当地的土尔扈特人故意把他引向歧路。不久科兹洛夫派遣他的同伴卡赞科夫又来寻找黑城,同样遭到土尔扈特人的拒绝。科兹洛夫毕竟比他的同胞高明多了,他学习了他的同种人斯坦因、伯希和之流在敦煌使用的手段,用欺骗和收买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一切。近一个世纪以后,我和我的俄国同行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似乎各执一词,彼此有过的指责,还不免耿耿于怀。他们强调科兹洛夫到黑城的考察发掘是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和地方当局的支持的。还是请看科兹洛夫的自供状吧!1908年3月12日,科兹洛夫在给俄国地理学会的信中写道:当地蒙古王爷巴登扎萨克和他的手下人得知我要去黑城的打算时,都“竭力使我相信,在我要去的方向是没有路的。但是礼品帮了大忙。首先是左轮手枪和步枪,宴请和留声机,还有那封请俄国驻北京使团转请清廷加封巴登扎萨克的信件。此举将使他从博格多汗朝廷所得俸薪增加两倍”(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城》)。对腐败愚昧的清朝政府和他的走卒仆从来说,丧权辱国尚且不顾,只要能发财升官安坐龙廷又何惜这陈年的古董废物旧纸呢。我的俄国同行也承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到中国边疆从事科学探险活动,“亦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清朝政府对此无疑作出了一定让步”,但他又接着说:“但是,在这些探险时间已过将近百年的今天,仅就敦煌和黑水的发掘和保存而言,此对研究中国文化史甚至中国学术,显然都是最宝贵的贡献。那些很可能毁而不存的东西,哪怕是部分地得救,并保存到现在。”呜呼!让我们接受这种逻辑去感恩戴德吧!在我的心里只有庆幸的安慰和伤心的哭泣。
宁静的黑城,你不胜骚扰了吧?当你一夕名扬四海之后,在这一方十余万平方米的废墟上曾吸引过多少人呢。有真诚的学术考察者,有寻胜探险者,也有心怀叵测者。当中国学术界觉醒,再不允许外人单独进入时,便有了1927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黑城探察。其后是中法学术考察团。此后,国内的各种考察团和旅行者,凡到额济纳旗者都要到黑城考察与发掘。如解放前额旗驻军18旅曾派一连士兵到黑城发掘,得获西夏文书籍、陶瓷器、箭镞,并运走石磨数十盘。据说这些东西都流落士兵之手。我和史金波去黑城之前,于8月间在兰州听说有一部从黑城流出的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保存在甘肃著名学者、收藏家冯国瑞后人手中。我们千方百计找到这位某中学教师时,他坚决不承认有此事。后来我们得知冯老先生1957年被打成****,曾遭到批判时,便不再去追寻了。
新中国成立后,黑城所属的额济纳旗曾先后划归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管辖。1962年和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曾两次派员到黑城进行考古调查,1963年秋季的调查中发现一些文书,在清理黑城附近的一座古庙中发掘出25身西夏时代的泥塑佛像,有的至今还保存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1972年以后,额济纳旗属甘肃省建制,甘肃省考古队曾几次到黑城遗址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踏勘,在黑城发现了一批元代文书。我们在额济纳旗碰到的甘肃省居延考古队,他们不是在黑城附近又有新的西夏文书发现吗。今天,我们也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黑城,我们不是考古队,无权动这里的一方土。我们随手在地表捡拾到的瓷片、瓦当、铁器之类,后来也送归了内蒙古博物馆。当时陪同我们来的旗政府干部是带了两把铁锹来的,他们说黑城外有上千座古墓呢!当然他们也来不及挖到什么。
我站在城头,任朔风贯体,沙雨扑面,尽情地领略这黑城风光。在司机的催促下,依依不舍地离开黑城。
20年后的又一个秋风萧瑟季节,我和史金波又到河西走廊考察,在张掖仅停留了一天,无暇北上再去拜访黑城了。黑城疲惫极了,我不再忍心去打搅它。据我所知,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额济纳旗,与外界的交往日渐增多,到黑城访问的国内外宾客人数倍增,也成为该旗的旅游服务项目之一。文化和科研部门组织的考察队,拍摄电影、电视片者纷至沓来。著名的如1980年4月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和日本学者共同组成的丝绸之路考察队和1991年中央电视台《望长城》大型纪录片摄制组都到过黑城及其附近摄制。涌到黑城来的游客们,许多人竞相拾取地表的遗物留作纪念,甚至乱挖乱掘寻找珍藏,使黑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8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下拨专款,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共同对黑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经过1983年和1984年两次发掘,基本上将全城布局勘察完毕,查清了西夏时期修筑的旧城址和在旧城基础上元代扩建的城垣、街区、建筑。清理出房屋基址二百八十余处,出土大量的文物文书,文书中有汉文、西夏文、畏兀体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文种,共计有三千余件,都收藏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80年代中期,一次我问起主持黑城发掘工作的内蒙古文物考古所所长李逸友先生,黑城遗址清理得怎样了?李逸友先生幽默地回答,在他们重点发掘的一万多平方米遗址上,都过了筛子,连老毛子留下的俄文报纸和啤酒瓶残片都清出来了。
1996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在河西走廊距离黑城最近处的张掖市,遥望北边大漠的黑城,顶礼祝福,愿黑城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