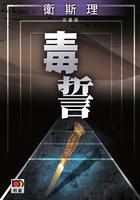总政派来的同志带着程、曾二人去王部长家,目的是争取能见上面,接上头,确定选题范围和访谈时间。考虑到领导同志工作忙,上班时间不好找,电话上又说不清,故而选择上午11时左右去,留出一段机动时间,等候王部长下班回来。
中午12时都过了,仍不见王部长下班回来,跟随王将军多年的湖南籍的老炊事员,已经做好的午餐端上撤下好几遍了,这是第三次端上桌,仍不见首长的影子。部长夫人只好同上中学的一个儿子“先行一步”。直到过了下午1时,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首长终于回来了。老炊事员迎上去,操着厚重的浏阳腔说王部长,毛(没)得等住哟,吃剩饭了,我给你回锅热热。”王将军爽朗地笑道:“开会开晚了,一顿饭做了几遍,太麻烦你了!”
总政来的同志向王将军说明来意,王点点头,一面脱去外衣和帽子。
被再加温过的三个小菜、两碗米饭端上饭桌,不长时间,便被主人一扫而光。
吃完饭,坐到沙发上,王部长拿过茶几上放的一盒“红山茶”牌香烟,享受“饭后一支烟”并与来客中包括曾源在内的“烟民”们共享。
总政来的同志将有关“南泥湾大生产”部分的征稿提纲递给王部长审视并选题。
王部长饶有兴趣地翻看着征稿提纲,手中拿着军事指挥员常用的、粗粗的红蓝铅笔不时在上面做记号,回首往事,不时流露出对战争年代甘苦胜败的伤感和对逝者的追念。他还根据不同的选题推荐了军内的好几位“当事人”和“知情者”。
编辑部的征稿、预约,得到了王部长的爽快承诺。不过尚需时日,因为他最近要去越南访问,回来后还将去新疆视察,真正要挪出时间谈稿子要到秋后。那只好由总政方面另做安排,曾源为此深感遗憾。
根据原定计划,拟向防空军司令员侯世春上将采访,选题是1943年我晋绥解放区军民在粉碎日寇“大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翻家庄歼灭战。当时侯世春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
这次采访时不凑巧,适逢侯世春同志离京外出,计划内要办的事,难以如期实现,只好插空子干“计划外”的“捎带任务”一采访总后张副部长,向他了解1947年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司令员指挥下,遵照中央的方针,采取“蘑菇战术”,取得“三战三捷”中的第二捷羊马河战役。当时张副部长任我参战部队某旅旅长。
找张副部长约稿进行得颇费周折:先前去总是扑空,得知张副部长已人高级军事学院深造。曾源和程继章上街找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两碗面,中午也没顾上休息,忙乘市内公交车前往位于北京西郊的髙级军事学院。
到达目的地,正好是下午刚上班时间,经询问门房值班人员,得知此事归战史部管。二人进人了办公大楼,登上二楼,欲问战史部的位置,正好有一位小个子军人迎面走来,时逢阴天,楼道里光线昏暗,曾源隐约看到小个子军人领章上是一个花花,没有框框,以为是一名列兵,是否向他打问,犹豫不决。倒是小个子军人主动上前问话:“同志,你们找哪个部门?”听口音他是湘赣一带人。程继章视力好又细心,他发现小个子领章上的花花大着哩一一是一位少将,连忙立正敬礼致意:“您好,少将同志。”小个子还礼,亲切地问:“有么子事哟?”程继章连忙说明来意,少将同志热情地充当“向导”,将程、曾二人领到战史部办公室,此时曾源因粗心认错人一时颇为尴尬。
进人战史部办公室,接待者是一位三十岁上下姓张的上尉军官,估计是档案员之类的行政人员。他体形微胖,刚刮过胡子,下巴有点发青,还有一二处挨过刀的青春痘露着红点点。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一副焦急不安的样子,多有忙中出差错。程继章递上介绍信,正准备说明来意,上尉军官眼睛盯着介绍信问:“你们要找的程继章和曾源在哪个系学习?”程、曾二人先是一怔,旋即明白过来是对方把采访人和采访对象弄颠倒了,当即给予纠正:“不,我们要找张副部长……”姓张的上尉军官立时脸发红,为自己的粗心和唐突感到羞愧。他急忙告知程、曾二人张副部长所在班的位置,又说:“你们现在就去找他,我马上打电话过去。”
离开战史部办公室,曾源心中暗自好笑:想不到全军的最高学府里也有“马大哈”。他转而又想:看样子这同志怕是要去赴约,瞧对象,心急火燎,神不守舍哩。今天是周末,很有可能。
程、曾二人找到张副部长所在的班:一位上将正在队列前布置任务,队员们不是荷枪实弹去搞军事训练,而是扛着铁锨、扫帚去按划分的区域打扫校园卫生,这是每逢周末的例行公事。那年头,提倡领导干部做“普通劳动者”,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人民文学》曾发表过王愿坚同志写的一篇短篇小说《普通劳动者》,十分生动、感人。曾源来自基层,眼中见多了连级干部、尉级军官,见到一位中校、上校军官,禁不住也要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如今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将军,而且是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经与张将军商量定下周二详谈“羊马河之战”。
已经过了下午4时,赶回城里去,黑灯瞎火,诸多不便,周末的公交车上拥挤不堪,能不能挤上去也说不准。两人合计了一下,干脆在这里的招待所住下来,明天再说。
返回城里去时间过晚,留下来富裕的时间蛮多。办完住宿手续,等了个把钟头,吃完晚饭,太阳还老高。程继章忽然想起何不趁此空暇时间去拜访一位叫柔刚的老熟人。柔刚在兰州军区工作期间,任成少龙司令员的秘书。程继章曾与他一同下基层多次,两人相处不错,三年前随成司令员调来北京总参工作,两人常有书信往来。柔刚年初来信说他又被组织调到军事科学院,仍在成司令员身边工作,住在北京西郊,信中告知其电话号码,以便日后有机会来京时与他联系。
程继章挂通电话,接电话的人却大出意料接电话的人竟是当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成少龙上将。他一听说对方是兰州来的,格外亲切。问对方的姓名、行止等等,好像因为他曾是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大院里工作的一般成员他都认识似的,特意邀请程、曾二人过他那边去,好好谈谈。
程继章放下话筒,有点作难:去还是不去?去之唐突,却之不恭。他看了曾源一眼,拿不定主意;曾源忽然想到’家里那篇“太原战役”稿子,占有的资料不足,特别是攻打敌人的核心工事一一牛砣塞部分更显得单薄,讨论了几次均未通过,何不就此机会请成司令员谈谈,这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吗?两人转愁为喜,立即起程前往,好在军事学院与军事科学院只隔一道山梁且内部有小路相通,倒也方便。
贺老总手下有“三把手”是说当年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属下有三位旅级“独臂将军”,个个战功卓著,声名显赫,各有千秋。有一位便是此时此刻坐在程继章和曾源面前的这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成少龙上将。曾源对成少龙将军有更多的崇敬感和亲近感。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曾源聆听过他的几次讲话,印象是他谈问题能切中要害,干脆利落,令人信服;二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在晋西北任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后来任西北野战军第七军军长,长期与罗副部长搭档共事,同甘共苦,休戚与共,曾源在写成罗副部长那边的两篇回忆录之后,采访成少龙将军,由此及彼,备感亲切。
对于“太原战役”,成少龙将军并未从高级指挥员的角度,居高临下去评述战争,而是以深厚的战友之情追忆广大基层干部和战士们的英勇顽强,怀念英烈们的无私奉献。他列举了我军一位排长盘肠大战,用刺刀挑翻顽敌,一位班长腿被敌人的炮弹炸断,硬是用膝盖跪着装填机枪子弹,还有许多有名的、无名的指战员为革命献身,其悲壮惨烈,催人泪下。
后来谈及本部队的一些人和事,对于包括炊事员、马夫在内的许多故人寄于深切的怀念。他说原先我们大纵队的那个山西柳子剧团,很有些人才哩,文唱武打都过得硬。后来精减整编,一下子解散了,怪可惜的。有的演员给我写信不想散一一对部队有感情嘛,我给他们回信做了一些解释工作,还把几位年轻的同志送到速成中学学习,也只能如此了。”他和我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一样,对于战争年代为部队带来欢乐和激情的各个剧种的剧团、篮球队等文化战线的同志,都有着某种特殊的情结。
侯世春将军终于被盼来了。
已是盛夏季节,酷热难当。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场大雨过后,带来酷热中的短暂凉爽。曾源和程继章去拜访侯世春将军,走进院门,没想到时任侯世春同志秘书的竞是曾源似曾相识的一位故人一一疑痴。他曾任十一师三十三团宣传股长,曾源与他是在一次师部开会时相识的,也算有一面之交。后来听说他调到军部报社,如今担任侯的秘书,极有可能是1952年大整编军部撤销,有一部分军机关干部加人组建“防空军”指挥机关的行列,疑痴想必是这样的背景下被选调担任了防空军司令员侯世春将军的秘书。
侯世春将军早已闻名全军,他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抗战初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参谋长多年,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直属十八兵团司令员。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高级指挥员,在曾源的想象里定是一位威严的首长,没想到一见面竟是一位循循善诱、和霭可亲的长者。他主动介绍说我是海南岛人,不大会讲普通话,你们能听懂吗?”他得知程继章是广西人,略带诙谐地说:“咱俩算是半个老乡,彼此彼此吧。”他亲自为两位年轻人沏茶,说这是最近我去了一趟庐山带回来的当地特产一一云雾茶,你们尝尝味道怎么样?”他和善、慈祥,朴素得像一位农民大叔,毫无首长架子。
谈话转人正题一一甄家庄歼灭战。
1942年至1943年,晋绥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克服重重困难,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蚕食”,终于迫使疯狂的日本侵略者由进攻转人防御,最后被击退、被撵走、被歼灭。其间,痛歼日军八十五大队的“甄家庄歼灭战”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方针的一次成功战例。这次战役的胜利是在侯世春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取得的。
在访谈过程中,侯世春将军以一位职业参谋人员的冷静态度和务实精神回顾了战役的曲折发展过程,毫尤夸张、溢美之词,将功劳归亍解放区军民,归功于党的方针的英明和上级指挥的正确。
他说,1942年12月初,在晋绥党、政、军负责同志会议上,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时,气氛很活跃,大家一致认为,主席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提出把敌人挤出去,这个“挤”字大有文章可做。有的同志为了深刻领会这个“挤”字,互相肩膀靠肩膀,你挤我,我挤你。大家一面挤,一面推敲琢磨,慢慢地悟出了其中的不少奥妙。有人说:“毛主席早就预言,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4挤’敌人,就要从军、政、经、文几个方面全面地‘挤’”。有的说:“主席指示我们‘把敌人挤出去’,既是方针,也带来了方法。”“要把敌人挤出去,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充分发动群众,打好各方面的、持久的人民战争。”有人补充。后来的实践证明: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挤”敌的积极性很高,办法也很多,很精明,很有效,例如断绝水源,先是在井里丢放死猫死狗,后来又把剪碎的毛发投放水井内,任凭鬼子怎样打捞也打捞不尽。敌人被断水如困沙滩,再加上武工队的袭击,虽然愈来愈孤立,仍不肯搬走。后来我们有组织地将据点附近的群众搬出,把家搬到根据地去,不“维持”敌人了,叫鬼子喝西北风去。主力部队、武工队和民兵包围着敌人的炮楼,周围的群众套上车,赶上牲口,一夜之间,全搬到根据地,连个坛坛罐罐也没留下,只剩下孤零零几座炮楼,凄凄惨惨,活像几座孤坟。敌人被围在炮楼里吃不上、喝不上,一露头就尝到我们的冷枪,吓得连撒尿都不敢下炮楼,真正成了孤魂野鬼。先后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挤掉了敌人据点五十多个,摧毁了八百多个伪政权,建立了五百多个抗日村政权,争取了一百多个伪政权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改变了一千多个村的形势。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一天比一天扩大。某种意义上讲,“甄家庄歼灭战”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敌八十五大队孤军深入我解放区腹地,妄图破我步步压缩,达到“反挤”的目的,结果却带来自身的覆灭。
侯世春同志的成功采访产生了两篇很有特色的回忆录:《把敌人挤出去》和《甄家庄歼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