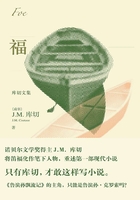从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便稀稀落落地下起了雪,中午渐止,下午又开始转为雨夹雪了。
医院停诊,但因这里被指定为急救医院,所以傍晚之前来了五名患者。其中三人是感冒,一人因交通事故撞伤了腿,一人是头部震颤症。病情都不重,拿了药打了针以后就都回去了。
八点做晚间巡诊时,雨雪已停,月亮出来了。因为处于大陆冷高气压圈内,天空虽然晴朗,但是寒气反而更厉害了。
住院患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暂时回家过年了,剩下的人不是无家可归便是病情严重。
医院现在只有常时三分之一的病人。晚间,院方给他们做了简单的拼盘和除夕荞麦面条。他们各自端着自己的套餐同对面屋或邻室的病友们凑到一块吃了起来。
九点钟,伦子到各病房去熄灯,发现患者们挤到一处睡着,有几个病房里根本没人。
两天前,石仓由藏住过的病房一直没有点灯。他近处的病房里虽然有人,但路过这间无人病房时,就连当护士的伦子也感到瘆得慌。
月光把床垫子照得白刷刷的。由藏死后,尸体搬走,撤掉被褥时,垫子上留有由藏腰部压下去的凹坑,以及如地图一样的汗迹和尿迹。
伦子从门缝中看见那张白床垫,不由得回想起了由藏临死前的面容。
她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走过去,过了走廊的拐角,跑下楼梯。从六楼依次熄灯,到三楼就全熄掉了。
伦子来到二楼时,朝走廊左端瞟了一眼。那边是医务部。
医务部点着灯,肯定是直江不去值班室而在那里待着。现在去值班室虽不合适,但去医务部却无问题。再说,今天一起值班的护士是那个反应迟钝的宇野薰,对她说熄灯后向医师报告患者情况也可糊弄过去。
伦子在院部门前犹豫片刻,然后狠了狠心敲了院部的门。
“请进!”
里面传来的声音果然是直江的。伦子走进去,背朝他关好门,然后转过身来。
“我刚去熄灯回来。”
“是吗?”
直江把看着的书放到沙发旁,从白大褂中掏出烟卷来。
“我给您泡杯茶吧?”
“不,不必啦。”
茶几上照例放着一升酒瓶和盛着半杯冷酒的酒杯。
“刚才从石仓老人的病房前走过来,好害怕噢!”
直江把烟卷点着火,吸了一口之后看着伦子说:
“不在这坐一会儿吗?”
“啊?”
伦子反问道。在医院里直江用这种语言对她说话还是第一次。
直江匆匆把散落在沙发上的报纸归拢好。伦子把茶几上的烟灰缸洗净、擦好,慢慢坐到直江旁边。
“喝酒吗?”
“我在上班。”
“无所谓,今天是除夕嘛!”
直江毫不在乎把自己刚才用过的酒杯递给伦子,并倒满了酒。
伦子轻轻沾唇以后又放回茶几上。
“明天您要去札幌?”
“嗯。”
“什么时候回来?”
“两三天就回来。”
“那么快就……”
伦子想:那样的话,是不是我也要早点从新潟回来呢?
“待多少天都是一回事。”
“札幌那里这时候雪积得老厚了吧?”
直江没有回答。伦子拿起刚沾唇的那个酒杯。她想象了一下在雪中行走的直江的身姿。
这时,直江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低声自语道:
“咱们一同去北海道吧!”
“……”
“我说咱们一同去北海道吧!”
“真的吗?”伦子有点不信,看着直江问,“真的领我去吗?”
“北海道现在到处是雪。”
“我知道。”
不管雪下多大,也不管天气多冷,只要能跟直江在一起,上哪去都愿意。
“明天你不是回新潟去吗?”
“不回去也行。”
“你母亲等着你吧?”
“跟母亲什么时候都能见面。”
直江不声不响地把杯中酒喝干。跟母亲什么时候都能见面,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跟直江就见不着了吗?伦子说完之后,自己也觉得刚才的说法欠妥。
“那么,明天走?”
“明天吗?”
我可真是个急性子,也许是个变化无常的性格,心想假如失掉了这个机会,也许以后就没有时间同直江一起去北海道了。
“不过,您是回母亲那里去,对吧?”
“不,我住旅馆。”
“在札幌您不是有家吗?”
“看母亲用一天就够了。”
“我若去不会给您造成麻烦吧?”
“我去看望母亲时,你待在旅馆里就行。”
“好。”
不论是同直江旅行,还是去北海道都是第一次。由于意想不到的喜悦,伦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明天几点钟出发?”
“下午三点的航班,连你的座位我也在今晚一起用电话预约吧。”
“旅馆有空房吗?”
“正月嘛,市内总会找到的。”
“真带我去?”
伦子重复叮问了一次。
“真的。”
“我太高兴啦!”
伦子朝窗外的天空望去。幸福,确实马上就要来临。侧耳静听,它的脚步声正悄然传来。倘若不紧紧抓住它,它就会变成一时的梦而消失。现在那念头正在冒起,不,也许正在消除。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伦子莞尔一笑,把脸偎依在直江肩上。
“在屋里虽然暖和,出门还是要穿厚大衣的。”
“要穿高筒靴?”
“短筒靴就可以了。”
伦子只有在东京穿的薄料大衣,短筒靴可在札幌买,旅行用手提包也是老式样的。外出用的冬季上衣和裙子想做也没做。新年期间虽说要回新潟探亲,但也没必要特别修饰打扮。不过,上北海道可就不行了。既然早有领我去的打算,何不早说,也好有个准备,这么急急忙忙地哪能来得及。
然而,伦子并没有因为这事太突然而埋怨。直江说的事总是这么突然,不到万不得已他不说。其实,也不是事先做好了计划忘说了的,而是临时想到才说出来的。在工作岗位上倒也罢了,对于伦子个人他也经常这样。不知不觉中伦子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
她既不觉得惋惜也不觉得烦恼。
也许伦子就是这种听从男人任意摆布型的女人。
“白雪皑皑的札幌一定很美。”
伦子想象着白雪中的宁静街道。不论是楼房、道路、树木都被大雪覆盖着。顺着那样的街道同直江并肩而行,这个梦明天就要实现,伦子觉得自己无限幸福。
“好宁静啊!”直江把酒杯里的酒又喝光了说,“一点也不像除夕之夜。”
远处传来电视机播出的歌声。今天是除夕之夜,留在医院里的病人们可能正聚在一起观看电视节目。
“今年又结束了。”
“是啊,结束了。”
直江把“结束了”说得非常重。伦子被他的声音所震动,抬起了头。
直江的眼里微微浮着笑意,真是好久不曾看到直江这种温柔的笑脸了。
当笑着时离去,梦幻不会消失。伦子看着直江的面庞,站起身来说:
“我走啦。”
“嗯。”
“我去拿点水果来吗?”
“不,我马上去值班室,不必啦。”
“那么,晚安!”
看到直江颔首,伦子才关好院部的门。
元旦那天是个晴天丽日。医院前的大街上挤满了参拜神社、互拜新年的人们,十分喧闹。姑娘们几乎全是长袖和服。原来寂静的街道充满了新年气息。
医院在平时分昼夜两班,到了新年休假时则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制,一天一个班。工作时间虽长,但患者少。二十四小时连续一班,以后可以充分补休,由于护士们希望这样,所以就这样定下了。
三十一日过后的一月一日交班时间是在上午九点钟。
元旦的值班大夫是小桥,护士是亚纪子和中西明子。
伦子向亚纪子等人交接完毕,正要换衣服回宿舍而来到衣柜前面时,小桥从走廊里慌慌张张跑来说:
“直江医师在哪儿?”
“我想是在值班室里,今早还没见到他。”
“是吗?不知他现在起来没有?”
“他每天起得晚,也许还睡着。”
“直江医师从今天起休息,到七日才来上班,对吧?”
“是的。”
“那可糟啦。”
“出了什么事。”
“我有三天没上班了,今天来到一看,接到了这么个通知。”
小桥把年初年末休假的一半放在年前休了。
“说对上野先生的输血从明年起不予报销了。”
“上野先生的?”
小桥点了点头,打开手中的信函。
上野幸吉因再生不良性贫血住院已经两个月了。一天夜里他在涩谷附近病倒,被当作急救患者送到医院来,由值班的小桥诊断,让他住了院。尚未来得及判明身份,就暂时把他送进了每日差额一千日元的三等病房。然而,等到后来弄清是医疗救济户患者时,院长埋怨说:为什么把这种患者送进那么高价的病房里?小桥说:因为病重只得如此,于是两人之间发生了争执。
开始时,其临床表现为高烧和贫血,病名弄不清。一周以后,根据直江医师的化验和分析才查明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对于这种疾病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只有输血。上野在今天仍以每天输血四百毫升维持着。这样只能拖长病期,不是根本性治疗方法,无法避免一天天衰弱下去的趋势。尽管如此,只要维持输血,病情就不会急速恶化。
上野由一位同龄老伴千代夫人护理着,但她也患风湿性关节炎,正在接受治疗。
“从明年起不予报销是什么意思?”
“过了年,从今天起。”
“哎呀,今天早晨的定量已经输完了。”
“今后,医疗救济不再予以报销了,让其自费。”
“自费?他们……”
上野夫妇两人都没工作,即使愿意工作也干不动。其收入也只是每月从区政府领到的生活补贴两万多日元。用这钱是支付不起每一百毫升八百日元的血液费的。这样下去,一天四百毫升就得三千二百日元,一个月的输血费就要超过九万日元。
“他们怎么能付起这么多钱哪?”
“就是把他家卖了也没有钱啊。”
小桥愤愤地拍着信函说。
“可是,区政府为什么下这份通知呢?”
“我也弄不清。”
“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搞错。这么郑重其事地用公函通知哪能错。”
小桥递过来的信件确实是公文,上面明确写着从新年起停止报销。
“也许因为医疗救济预算没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