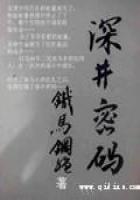过了十点,直江医师仍未来院上班。外科门诊只有昨晚值班的小桥医师一人工作。
尽管平时直江来得较迟,但很少有到了十点还不上班的事。
“直江医师这么晚还不来?”
十点一过,许多护士都有点沉不住气了。护士长关口鹤代也许是听了挂号室女办事员的报告,她亲自从三楼的护士休息室来到门诊室。
“直江医师还没来上班?”
墙上的时钟指着十点十五分。
“还没有来。”正为患者缠着绷带的高木亚纪子抬起头来回答说。
“患者们都等急了吧?”
“最早的那位是九点到的。”
直江坐的诊察桌上已经积压了五张病历卡。
“直江医师今天休息?”
“我想不会,因为下午还有手术要做。”亚纪子一边用别针别住绷带端口,一边作答。
“手术?”护士长看了看诊察桌后面的黑板。那里虽有“预定术”一栏,但什么也没写。
“昨晚我值夜班,下午得回家。”
“当然可以。”护士长环视了一下。门诊室里除了亚纪子还有宇野薰、田中绿,治疗室里有志村伦子和中西明子两人。做阑尾炎手术只要有两名护士就可以。
“什么手术?”
“好像是‘刮宫’。”
“刮宫?”护士长睁大了眼角略带皱纹的眼睛。
“手术是由直江医师来做?”
“可能是这么回事,因为今天不是妇产科村濑医师来院的日子。”
“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天哪,原来您也不知道?”
“不知道。”
“是由直江医师做吗?”一直给患者诊病的小桥朝她们二人这边转过头来。
“是的,您也没听说?”
“没听说啊。”
一个看完病的患者施了一礼走出去了。
“我也是昨晚才听说的。九点钟前后,直江医师打来电话说:‘明天下午要做刮宫手术,给我把手术器械准备好。’”
“太突然啦!”护士长很不满意地看了一眼亚纪子,“那事就那样吧。可早晨交接班时,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我以为护士长全都知道呢。”
“不但我,就连小桥医师也说不知道啊。”挨了批评的亚纪子不作声了。按惯例,手术预定是由医师决定后通知给护士的。小桥和护士长不知道这事,与其说是亚纪子的责任不如说是直江的责任。
“那么,接受刮宫的患者是谁呢?”
“这个……”
“天哪,你不知道?”
“他只对我说把器械准备好。”亚纪子噘着嘴回答。
“这么说,只有直江医师一个人知道喽?”护士长好像安慰亚纪子似的,口气柔软多了,“做事这么随意,真叫人受不了。”
小小的刮宫手术,并不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医师一个护士就可以进行。护士长之所以觉得难堪并不在于突然通知她,而是觉得她作为护士长的这个职务受到了冲击。
“这么说,患者需要住院喽?”
“可能是这样,现在住院的患者中还没有刮宫患者。”
“是谁呢,您不知道?”
“不知道。”
小桥冷冷地顶了回来,又拿起一份新病历。
“也太漫不经心啦!”
护士长看手表时,志村伦子从隔壁的治疗室走过来。
“这屋里有利尿剂药针吗?”
伦子手里拿着二十毫升注射器。
“哎,我说,你知道今天刮宫手术的事吧?”被小桥顶了回来的护士长又问伦子。
“不,不知道。”
“亚纪子昨晚在电话里听直江医师说的,谁也不知道。”伦子是第一次听到,“再说,直江医师还没来上班。”墙上时钟指着十点二十分多了,“是不是他不舒服?”
伦子想顶她一句:你问我这些干吗?我又不是他妻子,怎能知道?
“你能向医师的住处打个电话问问吗?”
“我不知道,请您自己打吧!”伦子转过身去从药架上取下两瓶利尿剂回隔壁去了。
“喂,叫患者!”小桥向愣在那里的亚纪子喊道。桌上的病历卡又增加了。亚纪子喊了最上面一张病历的患者。
“尽管有事,也太迟了。”
护士长好像要改换一下情绪似的从门缝向走廊看了看。走廊尽头的候诊室里有二十来个患者在焦急地等着。
“大夫,能不能先看这边的患者?”护士长指着直江的桌子说,“最初到医院的这位,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小桥不理,拿起刚刚走进来的患者病历。
“让他等得太久不太好吧。”
“我不看。”
“为什么?”
“那边是初诊患者和专门介绍给直江医师的患者,不该我插手。”
“不过,太迟了。”
“那你就告诉他回去吧,这是我们商定的。”
“大夫……”
亚纪子好像要劝告一下。
“好啦,你不要说啦!”
“糟透啦!”
护士长气呼呼地说完,向挂号室里的电话走去。
那天,直江医师在快到十一点钟才来到医院。
平时无事时脸色就够苍白的,今天显得更甚。头发乱蓬蓬的,有一部分甚至还直立着。
“哎呀,来得太晚啦!”他既不是向小桥也不是向护士们说。然后,坐到椅子上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合上了眼。眼圈发黑,显得很疲惫。
“大夫,您的电话。”直江刚刚坐下,挂号室的女办事员就来通知他,“说是山口的事。”
“山口?”
“他说他是山口的经纪人。”
“知道了。”
直江用手掌拍打头顶两三下,然后站起来。
“伦子!医师上班啦。”
这时候,护士长到治疗室去叫伦子。护士长最近以来有意识地把伦子安排给直江当助手,把亚纪子安排给小桥。
她满以为自己想得很周到,但伦子和亚纪子并不怎么领情。
“早上好!”
伦子进屋时,直江已打完电话,重新坐到椅子上闭目养神。
“您哪里不舒服?”
“不,没有……”伦子同直江三天前在公寓会面以来一直未见面。
“可以给您叫患者吗?”
直江睁开眼,看了看斜对面的亚纪子。
“我说,你给我准备好手术器械了吗?”
“只要消毒一下就可以用。”
“是吗?”
“我昨晚值的夜班,下午可以回家吗?”
亚纪子现在在外科上班,原来是妇产科的护士。因为妇产科医师每周只来两次,所以平时安排她在外科上班。
“可以!”
“现在就消毒吗?”
“再等一会儿吧。”直江把身子转向前方拿起最上面的病历向伦子说,“叫患者!”
那天,直江的患者超过了十五名,而且,不是初诊就是难诊患者,所以,要在上午看完这十多个人确实得花费很多时间。加上今天迟到,他自己也感到工作沉重。
他比平时更焦急,等全部诊完时已经过了十二点三十分,而小桥率先干完手头工作,已经回到院部去了。
“给我拿条凉毛巾来!”看完最后一个患者,直江靠在椅背上说。
“您不要紧吧?”伦子把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敷在直江额上。
别的护士们好像给他们两人留空,纷纷向食堂走去。
“您出了什么事?”
“不,没什么……”
“您又喝了很多酒。”
直江不答,抖着肩膀大口喘息。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嗯。”
“您到院部去吗?”
“……”
“我给您找个空床位吧。”
“到601去,那里大概空着。”
“请稍等,我去铺好被褥。”
“在沙发上就行。”
“不行,我马上就铺好。”
601是最上层六楼的特等病房。这是个休息室、护理室、病房等三室一厅的房间,附有浴池、厕所、电视机、沙发、写字台等,称得上是最高级的豪华病房,一天的住院费是一万五千日元。六楼共有三处这样的房间,另两个房间602和603已被某大公司的董事和文化界的某著名人士作为健康检查用暂住了。
直江脱掉白大褂,躺在伦子为他铺好的床上,合上了眼。这房间不临大街,所以,只能偶尔听到远方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根本想不到这里是处于繁华街道边上,实在静得出奇。深秋的午后阳光被绿窗帘遮过,使直江的脸显得昏暗阴沉。
“给您冷敷一下头部好吗?”
“不,不必。”
“您不觉得饿吗?”
“有橘子汁吧?”
“我去找找。”
“要凉的。”
临出门时,伦子照了照镜子,整理了一下白衣前襟,然后走出房间。
伦子重新回到病房时,直江为了避免窗外射来的阳光,已转过脸休息了。
“拿来了。”
“对不起!”直江轻轻抬起头,把倒在杯里的橘子汁一口喝光,“真好喝!”
“这里还有。”伦子脚旁还有一个橘子汁瓶。
“不,已经够了。现在几点啦?”
“十二点五十五分。”
直江点点头,脸朝白墙看去,也许因为窗上有遮阳帘,他的脸更加憔悴。
“您再多躺一会儿嘛。”
“不能躺啦。”
“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
“不是喝多了。”
“那是为什么?”
“好啦,好啦!”
直江又闭上了眼。
“今天下午不是有手术要做吗?”伦子把窗帘又拉上一些,房间更暗了,“刚才门诊室都在议论……”
“什么事?”直江闭着眼睛反问。
“护士长和小桥医师说都不知道下午有手术。”
“……”
“那患者叫什么名字?”
“山口明子。”
“那位患者最近到这医院来过吗?”
“来过一回。”
“那么,是您给她诊察后决定下来的啦?”
“我的一个朋友认识她的经纪人,求我帮忙。”
“经纪人?”
“山口明子是她的真名,艺名叫花城纯子。”
“花城纯子,不就是那个流行歌星吗?”
“是啊!”
“她要在我们医院做人工流产?”
“预定住这间病房。”
伦子重新环视了一下室内。
“原定在下午马上进行,但刚才来电话说也许稍稍晚到一会儿。”
“她从哪里来?”
“直接从福冈来这里,可刚才她没赶上飞机。”
“是不是因为去迟了?”
“据经纪人说,昨晚在文化中心演出之后,又去拜会各赞助单位。今天一大早便被商务会拉去搞什么签名活动,这会儿没能按计划搞完,所以……”
“那么,要什么时候到这里呢?”
“他说五点钟,也许六点。”
“手术要从那时开始吗?”
“你今天白班?”
“是白班,如果需要我,我就留下。”
“那就留下吧。”
“可是,从福冈回来立刻就动手术能行吗?”
“既然是个红歌星,也只好如此了。”
“然而,对自己身子有损害呀!”
“是自己的身体,其实又不属于自己。”
直江缓缓地翻了一下身子。这时,传来了仿佛是护士的脚步声,走近隔壁敲门后,站在病房门口说了些什么,内容不甚清楚,只听见有说话声。
“这么说,这事谁也不知道啦?”
伦子稍稍压低嗓音说。
“院长知道。”
“像她那样纯洁的人也……”
伦子话到口边停住了。她自己也难断定她自己永远不这样。
“尽可能在保密的情况下做完手术。”
“那么,对护士长也保密?”
“是我忘记告诉护士长了。”
“她可不高兴啦。”
“……”
“您今天这么晚才来上班,护士长肯定要向院长和夫人报告的。”
“别理她。我要睡一会儿,到两点钟时来叫醒我!”
直江转过脸去,背朝伦子。
“若是花城小姐来了,我就把她领到这屋来,可以吧?”
“反正也得五点过后。”
“是不是再留下一名护士?”
“有你,加上值夜班的足够了。”
“明白啦!”
伦子一边回答一边想象美貌的花城纯子堕胎后躺在这里的情景。
虽然已过下午五点,可花城纯子仍未到来。
医院的职员们在入口处打完出勤卡,陆续回家了。
尽管已是黄昏时分,直江却躺在院部的沙发上读着晨报。
“失陪了,再见!”在衣柜前换完衣服的小桥,穿上适合于年轻人的茶色短大衣,向直江道别。
“哎,小桥君!”
“什么事?”
“我刚才查房时,看见那个被啤酒瓶划破脸的户田次郎还在住院,听说是你给留下的。”
“是的。”
“他的住院押金已经用光了,你是怎么打算的?”直江从沙发上坐起来,望着站在面前的小桥。
“我认为他还有住院的必要。”
“然而,钱呢?”
“住院费由我暂时垫付。”
“原来这样。”
直江叠起手中的报纸,把它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这么说,从今以后,他的住院费和一切医疗费都由你来负担喽?”
“不是我来负担,只是在他父母没寄来钱之前,暂时垫付一下。”
“他的父母不寄来钱,就由你来负担吧?”
“寄来寄不来还无法断定。”
直江用自己的长手指摸了一下下巴。
“你的心情我理解,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我认为那个患者还应该住院。应该住院治疗的人,只因为没有钱这一理由,便被赶出医院是不合情理的。”
“是这么回事吗?”
“如果都让出院倒也没什么可说的,偏偏那些没有必要住院的人舒舒服服地住在医院里。我对私人医院的这种做法不赞成。”小桥站在原地俯视着直江说,“您认为这种做法对吗?”
“我当然不认为是对的。但是,这不一定都是私人医院的过错。”
“可是在现实里,院长不是正在赶走患者吗?”
“这不是因为他不付钱嘛!总之,如果你愿意代他付钱那就没事了。只是……”
“只是什么呢?”
“患者同医生以这样的方式亲近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呢?一个穷患者的医疗费由医生负担有什么不好?”
“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直江自问自答,“医生与患者之间尽量不要形成这种关系,最好要泾渭分明。”
“这一点我知道,不过,户田的事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呀!”
“同情也好,援助也好,都要看人而定。”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酗酒打架的二十五岁青年贫困。”
“然而,实际上,他正处于因为没钱要被护士长赶出医院的处境。”
“好吧,那就按你的想法去办吧。”直江重新从茶几上拿起报纸来。小桥仿佛在半路上被直江岔开了话茬,心里的郁闷无处发泄似的朝周围环视了一下,随即改变了主意夹起手提包说:
“再见!”
“你辛苦啦!”
从房间走出去的小桥后背上,散发出不甘示弱的意气。
刚才射满全屋的夕照阳光已经消失,屋子里很快就增添了昏暗色调。高楼林立的东京都内,看不见西落的夕阳。夕阳一沉下去,就进入夜晚了。
直江又躺在沙发上看起报纸来。医师中,小桥是最后一个回家的,院部里人都走光了。
直江感到有些困意,早起以后的倦怠仍旧留在身上,正当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之际,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伦子。
“您怎么连灯也不开,不嫌黑吗?”伦子按了一下门旁的开关,天花板上的荧光灯闪了两三下以后亮了。
直江脸上盖着报纸躺着。
“器械已经准备完毕,患者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是吗?”
直江挪开盖在脸上的报纸,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头上的荧光灯。
“您睡着了吗?”
“没有。”
“您还没吃饭吧?”
“嗯……”
“我去给您拿来?”
“暂时不要。”直江伸了伸懒腰。
“今晚的值班换了吗?”
“我同内科的河原大夫调换了。”
“我也求院部给调换一下就好啦。”
伦子盯着直江的脸,但直江不答,两眼看着天花板犹豫不定。
伦子凝视了直江一会儿,便坐到沙发的一端。
“这几天您有点瘦了。”
“瘦了?”
“最近测体重了没有?”
“没……”
“我看肩膀一带好像变薄了。”
伦子爱怜地扫视直江全身。
“生活不检点,只能糟蹋身体。”
“今晚的值班护士是谁?”
直江慢慢坐起来,因为刚才躺了半天,后脑勺的头发压得很乱。
“是杉江小姐和中西小姐,动手术时,只我一个人做你的帮手行吗?”
“行吧。”
直江回答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有人敲门。伦子马上站起来,赶忙去收拾桌上的茶具、茶碗。进来的是办事员村上。
“有个叫山口的人来电话说:现在已到羽田机场,马上就到医院来。”
“知道了。”
“打扰了!”
村上朝收拾茶具的伦子那里扫了一眼,然后施了一礼退出房间。
“现在看来,如果山口七点钟到医院的话,开始做手术也得七点三十分。”
“差不多。”
伦子在水龙头前涮洗茶杯。
“花城纯子小姐的男友是谁?”
“……”
“从前听说跟牧田歌手关系暧昧,连女性周刊都有过报道,大概是他吧?”
“不知道。”直江搔搔头发,看着昏暗的窗户。
“给这种名人做手术,您不紧张吗?”
“如果发生了差错,影响面是很大的。”
“不管她是女演员还是女歌星,身体都一样。”
“那当然是。”
“我还要再休息一会儿。”
直江重新躺到沙发上,伦子把洗好的茶具装进橱子里。
“您要不要喝杯茶或是咖啡?”
“不,什么都不要。”
“噢。我去楼下手术室放放蒸汽。”
伦子刚走到门口,又站住了。
“哎,明天您有空吗?”
“明天?”
“到您住处去行吗?”
“可以。”
“那么,七点左右去。”
伦子说完,放心似的走出了房间。
花城纯子到达东方医院时,已是七点多钟了。
纯子戴着深色墨镜,穿着白黑混色的天鹅绒上衣和黑开司米喇叭裙,手里拿着件短大衣,即使没有人说也可以看得出她不是一般的女职员。
“我叫山口,直江医师在医院吗?”
这个人穿着华丽的条纹西装,身材高大,他向挂号室的人问道。挂号室的饭野静代把两人打量一番之后,电话通知了直江。
直江来到门诊室时,纯子和经纪人大庭正并排坐在候诊椅上。
“我们来迟了,很抱歉!”
经纪人站起来致歉,然后介绍了花城纯子。
纯子慌忙摘掉太阳镜,低头施礼。
“福冈的日程安排得太紧了,所以来迟了,实在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