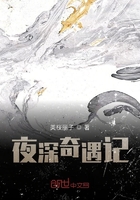当前面对着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人类学家应当积极参与其中。但是如何参与确实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我想,既然你是学者,在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参与机会时,就应当不要忘了如何用你自己的知识作出独特的贡献,而不是人云亦云。否则由政府机关的人来做就好了,干什么还要学者来参与呢?政府机关现在的公务员了解实际情况,对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也比多数学者清楚得多,人类学家们和他们相比有什么优势呢?正是人类学方面理论方法的训练和从事人类学研究养成的职业立场与态度。如果我们在做政策咨询等方面研究时,没有发挥这些优势,最好还是不要混迹于西部大开发的咨询队伍中装腔作势了,省得浪费了国家、社会和民众的资源。中国学者应当更多地学习和运用人类学项目咨询研究、应用项目调查的方法和技巧,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吃得更透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西部大开发带给中国人类学界的机会。其实有许多人类学可以提出的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都应当给予更多考虑,如西部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持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对原有生活方式的冲击、全球化形势下族群认同的加强、经济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资源产出地民众在资源开发中的位置等等。希望通过人类学家的努力,使得西部大开发更好地造福于西部人民。
徐:您对21世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前途和走向作何分析?
王:中国人类学实际上包括两种不同的范畴。第一种是关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目前,从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来看。有关中国的人类学还很薄弱,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相对比较低。就美国人类学界来说,除了专门作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在美国人类学界内部,有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比较其他区域的人类学研究来,也是相对较为薄弱的。比如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对非洲、大洋洲、南亚、东南亚族群与文化、拉丁美洲和北美印第安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人类学理论,在人类学方法论上的发展也主要是得益于上述这些地方。相对来说,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学研究就逊色许多。有关东亚和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理论上的贡献较少一些。就是否存在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的问题,我曾经和一些美国人类学家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对国际人类学学术理论相对贡献较小的状况,究其原因,其一,由于对西方学者来说,作中国人类学研究需要学习语言,一个专业学者在语言学习上所花的功夫比起作非洲、大洋洲等地研究要多用许多时间。中国历史悠久,文献资料丰富,研究中国不仅要学习语言,而且还要学习文字、利用文字资料,说到利用古代文献,对西方人就更困难一些。其二,美国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受到费正清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影响,有一部分学者区域研究的兴趣要大于对人类学学科的关照,理论讨论的焦点往往是一些和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而稍稍忽略了对学科中更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三,中国和东亚不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区域,在这一地区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些传统区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差别,不太为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人类学家所重视。不过,随着学术界的理论反思愈来愈深入,人类学愈来愈向全球化的知识发展,人们的信息沟通愈来愈方便,有望走出上述的窘境。
近些年来,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已经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站住了脚。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最有名的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就是来自斯里兰卡的汤·巴亚尔德教授。我刚才提到的努尔·亚尔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也有一些已经取得较高学术位置的中国裔教授,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曾经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的许烺光教授了,此外还有萧凤霞、陈中民、黄树民、王保华等人。阎云翔、景军、施传刚、宝力格、刘新、张鹂、乌尔丽歌、任海、谭乐山、田广、杜杉杉等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的,他们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大学中教授人类学及其相关课程,其中一些人已经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在美国人类学会和亚洲年会上,有关中国的讨论会有许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参加,阎云翔还担任了亚洲学会一个委员会的委员。不难想象,在几年乃至十数年以后有关会议上,会有许多中国裔人类学教授扮演重要角色。这也是中国裔人类学家在世界人类学对学科与他者(other)的关系思考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实践所做的一种贡献。
中国人类学的另外一种含义是中国人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境内的学者们所做的人类学研究。我们已经在《中国民族学史》中说到过许多这方面的发展过程及近年的情况,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刚才也谈到有许多困难,学术发展总会不断地遇到问题,否则就不需要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了。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中国人类学家能够走出国土,进行一些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研究,对中国人类学的进一步成长和完善、中国人类学在国际学术圈中占有位置都会有很大帮助。我相信,中国人类学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在人类学重建之后,在老一代学者的带领下,已经有了二十年的积累,有了一批初步掌握国际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中青年研究者,总的来说,在21世纪中,中国人类学学科会更加普及,会进行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会越来越经常化和规范化,学术研究水准会不断提高。也就是说,在学术发展的广度和宽度上都会有所进展。
徐:您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册学术界评价很好,但对您与其他人合作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史》下册却有一些不同看法,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王:这的确是一个很尖锐的、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既然您已经提出来,我只好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也许某些想法是错误的或片面的,只好请您、也请广大读者多多谅解。
学术史研究本身可能是非常大的挑战,首先是你必须读许多书,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再就是做访谈,了解亲历者们的故事和体验,这样就必须有许多积累,需要下许多苦功夫。但并不是下了功夫就可以了,学术史写出来是要给人们读的,读者可能分成几种类型,一种是学科的入门者,可以通过学术史了解和把握这个学科,学术史是掌握学科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第二类读者是学科中人。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学术史了解个人所未能掌握的情况和有关的研究线索,体验和理解学术发展过程,以推进自己在更专门领域的研究;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学术史中所涉及的学者或者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能对学术史做一种强烈的情感性阅读。原本我们写作《中国民族学史》的这种风格和选题的学术史是讨论学科发展总体状况的,为读者勾勒学术发展的线索,说明学术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中的一些主要的变化,并说明这些变化的原因。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难免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也希望同行们给予批评指正,以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更好的发展前程。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学术史并不是学者个人的传记,也不是学术机构的记功簿。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学科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了解不够,再加上篇幅有限,没有能够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读书的时候,一些人可能会误读学术史,在阅读学术史时过多地考虑书中涉及的个人和研究群体的学术成就及其评价。
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记忆和个人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大家总是选那些愿意记起来的事情来记忆,而忘却另外一些事情。尽管记忆可能有着社会群体的一致性,每个人因为个人的学术生涯和生活经历不同,这种记忆也会有差异。早一些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可能遗忘得比较多,随着时间的飘逝,在社会性记忆的整合之下,在特定的群体中,对有些事件的记忆会相对来说比较一致一些。而新近发生的事情因为相隔不远,就会有更多式样的个人记忆,而且因为每个人在事件中的位置不一样,记忆会有不同。我们在写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的时候根据资料写出来的那些东西,只是我们站在特定的角度上的理解和记忆,其他人未必是如此。这样,不管学术史写作风格如何,离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越近,就可能会受到越多的非难,要担更多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不愿意写当代历史的缘故吧。只是为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需要,我们冒了这个险。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注意多引用他人的各种说法和各方面的资料,不轻易地下结论,也许是历史学训练给我的影响,试图通过材料说话。用资料勾画历史发展的线索。写作学术史时是用各种资料来回溯过去,材料丰富才可能使过去变得更清晰一些。多引用些材料不是为了抖落什么人的旧事,而是为了说明特定的时代带给学科的那些东西,包括辛酸、艰难和不堪回首的曲折过程,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从中总结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让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不再一次经历那些痛苦。我相信,经历过反右派斗争、批资产阶级民族学、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一代人类学民族学家对此都深有体会。同时多引用一些材料。也可以适当地丰富我们观察和思考的视角,使人们能够看到对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不同理解。与此同时,我们总要做一些学术评论,特别是在下卷中,为了把书写的更个人化一些,可能评论更多一些,但这些评论只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和认识。尽管在大多数评述中我们采用的语言较为平和,但是那些被人们认为略微带刺的地方总不会是也不可能是每个人都乐意去读,或者心平气和地去读的。同时,应当说明,史料或者材料本身是有力量的,也有人愿意用权势(power)一词来说明史料的这种作用。有些材料虽然也是白纸黑字印刷出来的,事过境迁,也许有些人并不愿意再提起这些事情或者旧时的论说了,再加上中国旧史官长期遵循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禁忌,材料的使用更会为人们关心。和中国古代历朝各类史书一样,当代历史着作也不可能解除这种史料或材料的力量,甚或会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学术着作写作多元主义态度的采用而加强。其实,对下卷的一些批评就是冲着我们引用的某些材料来的,我们当初如果牺牲一些对不同读者来说作用不同的材料,也许会少一些批评。然而如果这样做,作为一本为今天也为明天的学者提供有用文本的学科史着作来说,实用价值可能也会降低不少。
《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主要说的是老一代学者的事情,离开现在时间也比较久远,通常不会太敏感,老一代学者多数经历丰富、虚怀若谷,不会太计较我们这些后辈的评价。上卷中引用的许多材料也是许多人平时不太容易看到的,我们主要根据这些材料来建构那一段的学术史,因此可能会评价更高一些,也比较一致些。而在下卷当中,虽然我们的资料搜集工作并不比上卷轻松,也为读者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也许学术圈子里面的许多人也掌握丰富的材料,根据那些材料能够建构出不同的学术史来,我们又试图比起上卷来发表更多一些的个人意见,多一些个人的理解,评价当然就有一些不同了。《中国民族学史》出版之后,许多读者给了我们不少鼓励,不仅是大陆学者,而且美国、俄罗斯、法国和我国台湾、香港都有人与我们进行讨论,有些国内外大学将这套书列为有关课程的必读或者重点参考书。但是我们的评价不可能使所有人满意,而且,就像历史学已经逐渐成为具有争议性的学科一样,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也必然要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涉及到更近一些的历史时,尤其如此。
不知道对《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有些批评意见的人中间到底有多少人仔细地读过这本书,我是说。完整地读过这本书。有些人看到了一两处感到不太舒服的地方,却没有去想想那些另外一些人看了也许还会觉得对这位批评者评价过高的地方。这也是人的本性,原本没有什么奇怪的。学术界中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在书中也谈到了一些,但是,也许不幸被我们言中:有些人还没有看到书,就在向其他人散布说书中批判了许多人云云,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和紧张,也制造了对立性情绪。不过,在仔细地读过书之后,而不是只抓住其中的几个段落,我想其中许多人的意见会有所改变。另外,我们原本非但没有制造新的学术矛盾的意思,反而想通过我们的见解去消弭一些东西,但可能有些对事不对人和机构的评论中个别锤炼稍有欠缺的词句对其他人还是有些刺激。我想,《中国民族学史》的评价可能也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现象,也值得更多的人去研究和思考。人类学在中国要发展,就要不断地讨论,集思广益,如果是有根据和见解学术讨论和批评,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意见,并且希望在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展开讨论。通过这种讨论,有更多的人和我及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关心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就达到了我最初做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
徐:哈佛回来后您在人类学研究上有什么新的打算、安排?
王:学术访问只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经过学术访问回到国内,我想得比较多的是怎样在自己从事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和教学中更好地将这些成果加以运用。目前阶段日常工作主要是讲讲课、指导研究生、查找资料、进行田野调查、撰写研究着作和论文,其中一些是已经应允要做的。我现在担任心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哈萨克族史等本科生专业课程,我想在近几年备课的过程中,在不断的学习过程里,把带回来的最新资料融到这些课程教学中间去,给学生更多一些新的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也许将来能把它们编写成教科书。另外,我也在指导人类学专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在研究生课程中,有关人类学理论、历史与方法等方面也需要补充许多新的东西,才能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培养有用的人才。再有就是关于新疆民族与文化方面和其他一些题目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中国人类学史的继续研究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研究应当有更深入一些的专题研究着作,也需要收集更多的资料,做更多的研究。我希望在大家共同营造的更好的学术氛围中,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在与国内学术同行们的交流中,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来完成这么多的任务。这也就是我这样的读书人为社会所能够做的最好的回报吧。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