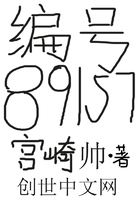听说12月30日,也就是前天,日美德法英俄六国公使集会复议大借款合同中关于财政监督各节,声称如果中国不能实行,各国将以国家名义进行干涉;除赔款外,尚有内外到期未付之款,必须一并由借款项下划付,革命以来外国人的损失也须在借款项下扣除。
此事照例应由外交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代表赴中国外交部说明,但朱氏因目前英国与中国有西藏问题、鸦片问题的交涉不便前去,就由日法两公使代表向中国外交部照会。这件事成了民国元年末日的一大纪念,而政府却视之平平无奇,大家且乐得个得过且过,快活过新年。
远生于上午11时准时来到柯宅,先是祝贺Happy New Year,寒暄了一阵子。然后就转入正题。
谷利斯浦团是银行团以外的财团,柯敦是谷利斯浦团借款张本人之一,在北京驻外记者中柯敦算是对中国有好感的人。远生和柯敦同是记者,谈起来很上路。
远生说:“我国民对于谷利斯浦及柯君等为我等借款之事尽力,非常感谢。”柯敦微笑:“此事大费周折。不过,我专管政策上的事,经济上的事由前代表巴斯及新代表克列劳先生主任,关于为什么突然取消借款,连我也不太清楚。只是谷利斯浦自承担借款以来,三百万镑、两百万镑付款并无延误,而贵国政府却给以种种为难,忽然取消。当然这并不全是贵国政府的过失,但伦敦借款契约原订谷团与中国各出百万镑组织银行,而贵国政府又以多种托辞,不能履行此约,因此谷团中的英国、法国、美国各资本家都纷纷责难,并退出团体。”
远生也知道,自去年七月初垫款中止,致使北京财政惟恃搜罗主义及小借主义,据说连袁大总统都对人说:“我宁做土匪国,不肯借此屈辱之款。”而外国人在一旁议论纷纷:英国公使朱尔典说,中国政府真可笑,发行一千万镑债票岂能秘密行事。英使馆参赞巴顿则说,最好是中国政府不借款,因为国家欠债太多,已有的债务没有还清,去年10月至今年12月的利息大约在五百万镑以上,中国怎能负担得起?再说,中国借债并非用于生利事业,大半是耗蚀费用,比如用以运动南北统一;比如兵饷不实,上报有二千兵,其实还一千五,吃空名额。而中国官吏把这种现象说成是改革之际混乱,不能避免,以后就不会这样。这如何能取信于人。
借款,借款,自临时政府成立后,北京政界最大的问题是借款,今日说借款成立,明日说借款破裂,直到新年来临,即昨天,12月31日,大借款还没有结果。
想到这里,远生说:“君所言之意,我等非常感激,但我中国政府为种种情势所迫,非有急速之巨款,不能度此新年。所以曾要求谷团再借千万镑过年,谷利斯浦君在伦敦演说时也曾声明愿意再借千万镑先救急,各国不应以拖欠还款为借口难为中国。听起来有很大诚意,可为什么光说不做,借款竟成画饼,实在令我们不解啊!”柯沉吟了半天,说:“此事很复杂。”
其实远生从别处也听说,六国银行团这次磋商借款条件保密异于寻常,银行团代表共同监督约束,即使至亲密友也不得向其他人泄露所议内容,就连周总长的翻译也不用中国部员而由六国团代表之一的梅雪尔担任。但这么秘密的事,还是被法国汇理银行中有一书记(法国人)私下里将大借款磋商内容泄露给谷利斯浦团中人。所以谷团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横插一杠。没承想到头来借款之事还是没有办成。
远生还获悉,当局中关于最终向谁借款也分成两派,有倾向六国团的,有青睐六国团以外的银行的。还有些人则是懵懵懂懂,只知道今日议何条项,明日如何签押。总的来说,政府中对国际大势,对六国团的内幕、派别与其政府和驻使的关系以及欧洲金融大势,没有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甚至国务员、议员中有人连大借款的条件都不知道。
远生觉得福生有基,祸生有胎,亡国之事,难以侥幸。今天的北京成了亡国奴之陈列所。试问民国二年,我中华民国将在国际上陷落到何等地位?瓜分乎!共同保护乎!瓜分边疆而共同保护本部乎!
六国团用种种挑唆手段进行离间,使中国徒受反复波折之苦。实际上今日六国银行团已是纯粹的一个外交性质的团体,即六国国际保证监督中国财政的委员会和殖民银行的总汇。时下内外争传列强将开列国会议处分中国,叫嚷中国将亡,将亡!其实,就算大借款成功,因蒙藏事未了,实际上已形成列强瓜分中国边境并共同监督本部的局面。关键问题是到现在当局在外交上只是一知半解,根本没有一个稳固的活路。
远生一想,就算千辛万苦借到二千五百万,除去六国扣除的种种款项,能到手的必然还不到千万镑以上,任你财政总长周自齐如何解释,参议院如何原谅,如何赞成,一旦中国的财政监督权在外国人手中,审计处、公债局均由外国人当顾问,盐政总稽核处分稽核处有外国人会办,有银行团代表随时调查,那么实际上六国银行团成了监理中国财政的混合委员会了。把中国的财政权、盐政权,各省的赋税权一律送尽,而只换得一年还债及零碎日用。辗转间断送国家到这种地步,真可谓亡国之臣,败家之子。有人还讴歌大借款成功,周自齐果然有旋乾转坤之手腕?
最可憎的是,六国团屡次迫使中国取消别国借款,但取消后他们又不肯付款了。他们还在合同上做手脚,按财政部译文,借款合同上他们已允垫款若干,但洋文原函上却只称中国要求垫款若干。前清张之洞等同外国人订合同时,总是按照汉文译本,为国家争得权利。此次银行团实允垫款若干,但他们的洋文合同中却不是这样。在取消谷团优先权时,银行团也说年内垫款若干,而年底却一毛不拔。一个国家受人欺凌至此,中国人真是生不如死。
远生谈了一会,又换了一个话题,问到中俄交涉。柯眼珠一转,双眉颦蹙:“中国之大误特误,就在于不能将满蒙各处开放,以至于这些地方只见有日本人、俄国人的事业,并无中国人的事业。其他各国事不关己,谁肯为中国说话?就好比中国有一块极好的饼干,既不自吃,亦不请人,结果乃被他人强拿着吃完而已。”谈到西藏问题,柯说:“我们英国并无心扰掠西藏土地,但不能不维持西藏秩序,以免扰及邻境。”
起先曾为中国借款热心尽力的柯敦,而今已作冷眼旁观。虽然在接受采访时柯氏说话很和气,但最后他却说了些意味深长的话:“为中国的命运感到悲哀,中国之命运终究还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
采访完毕,远生与柯敦握手道别。柯氏又对他说了一句Happy New Year,但远生没有丝毫幸福感。
出得柯宅,远生心情特别沉重。坐在车上,满脑子都是他写的那篇评论标题:《奈何桥上之大借款》。行至前门外,碰上塞车,车马纵横,看不见尽头,他的车停在路中两个多小时才通过,这是近几年新年期间所没有的,尤其是车马之多为过去所未有。远生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马车中坐的大多是高帽华服的政客,偶尔也可见到二三个外国使馆的人。这些人大概都是去天坛参观古物陈列所或看提灯会的,一个个显得洋洋乎乐哉!远生越看越来气:“唉!这就是担负民国运命于双肩的政客。然而,国家现状这么惨,去年贫无立锥之地,今年贫得锥也无。”
远生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只因为当了新闻记者,就不能不谈政治,不能不发政论。为了使自己所发的政论持评判的态度,不“信口开河”地乱说,必须做到采写的素材力求真实,因此,元旦之日,别人过年,而他忙得马不停蹄。晚上又听到一件怪事,即前清时东西长安门之内不能直通,所以叫禁门,去年把大清门改为中华门,内务部就决令开放东西长安门,以便利交通,并设市场。这本来是好意,却风潮大作,原因是公告上写着:此处只准马车、东洋车通行。
在这新年之夜,远生百感交集,今日所见所闻说明了什么?北京只有政界及洋式饮食店、洋式杂货店等有新年的气象,而普通百姓毫无新年的感觉,最可怜的是商家票号困苦颠连,已经倒闭四处,正在商议请政府借款二百万维持市面,否则,凋冽之后,力不能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罢市了。看样子到旧历年末腊月三十,恐怕更加困苦。远生想着想着,便提笔撰写一篇北京通讯,标题是《幸福之新年乎,痛苦之新年乎?》
他在文中写道:借款交付如此,蒙藏交涉又搁置起来,而人们忧虑的政局问题比国际问题更加迫切。对于正式国会的前途大都莫不惴惴恐惧,谣诼之繁风声鹤唳之紧,遂令记者失其记者之自由。唐人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清洁无辜的国民,难道是如此商女如此后庭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