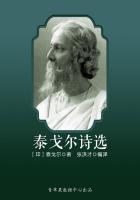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输华商品,除了紫铜一项,其它都有幅度很大的下降,其中日用品下降幅度最大,降幅最小的布,也有一半以上,其实日本伞下降幅度最为恐怖,从将近8万把降到了0。这跟各地纷纷抵货中,人们拿日本雨伞出气,拆毁而且再踏上一只脚的场景,遥相呼应。另外,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写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运动持续的一年里,日本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损失,对华输入减少了40%。走私的减少量,还没有计算在内。当时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报告里承认,出于运动的缘故,各业对日交易陷于停顿,金融业“对凡于日本有交易关系者,则不与之交易;正金与台湾两银行之纸币几乎完全不能流通,因之除极少数之外国商品或中国土产品外,对本邦商人之交易完全停顿;尤其报关运输行等,因排日关系,日本货品完全不能搬动。日清汽船、戴生昌以及满铁等轮船公司,自从19日中国报关业公会决议不在日本船只上载货以来,虽尚有若干乘客,中国人之货物已完全不交载运。日清汽船比平时减少三分之一,戴生昌减少四分之一,满铁减少三分之二,尤其如日清及戴生昌以长江或内河航路为其唯一生命而竞争又甚激烈之轮船公司,其受打击甚大,料不易恢复原状。其他一般商店,除日本货商店及少数贩卖当地日本工厂制品者外,固然期货交易已不存在,即使已订契约之商品,亦不履行,交易成为完全停止状态”。另据马寅初考察,“以1919年为例,日本日清汽船会社往来沪汉间所载之货量,4月份为5552吨,5月份降为2157吨,6月份为37吨,7月份为87吨,9月份99吨”。台湾老资格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开封的一个中学生,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抵货运动,在交通要路检查日货,他回忆说,眼见得,逐渐日货就没了,“而美英货却渐渐多了”。一位参加运动的云南人回忆说,1919年到1920年间,日本棉纱对云南的输入,少了“十分之九”。但是,查阅日本大藏省编辑的《大日本外国贸易年表》却发现,在抵货前的1918年,日本对华贸易输出额为359,150,814元,输入为281,707,333元。次年,的对华贸易输出额为447,049千元,输入为322,100千元。在抵货高潮中,日货输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种增加,在中国如火如荼地抵货声浪中,显然有些不合情理。显然,从前引史料看,不可能是抵货的有效性出了问题,只有一种可能,1919年正好是北京政府用日本贷款大规模购买日本军械的时候,应该是武器的输入,抵消了日常用品的减少。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在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日货倾销地的情况下,总体上由于中国人消费能力过低,绝大多数农民,实际上不怎么购买日用工业品,牙粉、洋瓷盆这样的东西,农民根本就不用,消费者仅限于城市里的学生和部分富裕的市民,所以,日本输华商品量虽然对于日本的某些城市而言是不小的,但就日本的整体贸易来说,尚非最主要的部分。1918年日本商品输出总量为1,962,100,668元,对华输出为359,150,814元,1919年总量为2,098,872,617元,对华则为447,049千元。中国市场固然对于日本很重要,但这块市场销量的减少,还不足以制日本的死命,所以说,通过抵货就可以让日本衰落的想法,显然并不现实。况且,当时中国农民消费洋货最大的部分,是购买机制棉纱,然后自己织布,但是日本纱厂很多却是在中国开办的。抵货运动当时并没有深入到农村,即使深到了农村,想将日纱完全驱逐,也是相当难的一件事。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是五四这种持久而深入的抵货运动,抵货的效力,也是有限的。
抵制日货的是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很难说。一方面,当时中国这样的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的弱国,在一个正在走工业化上升路线的强邻压迫下,孱弱的民族工业,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事实上很难出头。明眼人都明白,仅仅靠市场的竞争,国货一时半会儿是无法跟日货匹敌的。抵货运动的初衷,是通过不买日货,削弱日本的实力,但最终却是落到振兴国货上。不管怎么说,五四运动中全民规模的抵货,给了民族工商业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常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里面应该有抵货运动一份功劳。五四的抵货运动,跟五四示威游行一样,从后来的结果看,不唯拉动了民族工业,而且的确起到了唤起民族觉醒,向世界展示民族力量的作用,对于不久后的关税自主争取,也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但是,抵货毕竟伴随着暴力和强制,一种在爱国道德至上的暴力和强制,至少在抵货高潮的时候,非法地伤害了日货经销商和购买者的利益。这些人不仅物质利益受到很大损害,精神上也受到很大侮辱和刺激。他们买卖日货,但也是正当的商人,被冠以“卖国贼”、“奸商”、“亡国奴”、“冷血动物”加以羞辱,也是一种伤害。显然,这些人,即使贪图私利,也似乎没有多大罪过,跟卖国根本沾不上边。买卖日货,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仅仅是谋生的需要,不大可能有哪个人真的是出于日本的利益坚持买卖日货的。他们的“过错”,从道理上讲,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大局,从当时的情势来说,则是不服从集体行动,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并未争得他们的同意。
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一般的国民,有没有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出自国民的自愿,当然没有问题,值得称颂。但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强迫他们遵行,不仅妨害了他们的自由,而且造成身体和财产的伤害,这样的强制,是否像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天然合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采用暴力和强制,全民性的抵货能否贯彻下去,又肯定会是个问题,就像西方工人罢工一样,如果不组织纠察队,强力阻止厂主从外地招工进厂,任何罢工都坚持不下去。但是,不管怎样,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个人自由的旗帜,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面前,肯定是萎缩了,萎缩到连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在这个意义上,从新文化运动走到五四街头抗议的一代五四青年,是走到了原来主张的反面。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对于抵货的意见。当时,严复的儿子严琥正在唐山工业学校读书,也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严复闻讯,去信责备。信的最后有几句话,很有点意思:“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同,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是啊,在爱国的大帽子下面,有谁还敢提出异议呢?没有异议,自由将如何安放呢?
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两难的难局。之所以有这个难局,关键在于当时特殊的情势,国家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市场变成了日货的倾销地,而中国的政府,没有这个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民众自行设法。演成这样一种局面,事实上对于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也是不得已。即使在当时,要想根本禁绝日货,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越是小地方,日本产的日用消费品销量不大的所在,抵货运动的阻力反而越大,因为在没有相应便宜的国货替代的情况下,抵制日货的结果,是直接损害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费。一位当时山东诸城的小学生回忆说,他参加抵货之后,回到村里,靠做小生意为生的亲戚都躲着他,一个大叔对他说:“实话说了罢,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作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厂织的布,你念的书也是日本工厂出的纸印刷的。”另一位在洛阳参加抵货的中学生回忆说,洛阳的商家对抵货就不热心,自己的一个做店伙的表兄,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抵制日本货,惹恼了日本人,派兵打来,看你们怎么办!”学生们抓到了一个偷运日货的“奸商”,捆了起来,这个“奸商”不但不服软害怕,反而愤愤不平地跟学生大叫大嚷。安徽芜湖的商会,对抵货也不积极,以至于愤怒的学生把商会砸了,“首先拆了商会的电话,后来又把商会办公室内的家具打得一塌糊涂,有些东西简直被砸得稀烂”,连商会会长的头都被学生打破了。
更进一步说,即使禁了日货的输入,那么在中国的日资工厂产品怎么办?抵货的时候工人可以罢工,但不能总是罢下去。很多农民织的土布,实际上用的棉纱,却是机纺的,其中就有不少来自日本开的工厂。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实不待全球化,当时已经出现了。就算抵货运动对国货的保护和民族工业的推进,效果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得承认,由民族主义高扬而发生的抵货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刺激,只能是暂时的,民族工业的壮大,从根本上说,还得靠工商界自身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扶植和适度的保护。这一点,其实抵货运动中的一些明智者,已经看到了。1919年7月24日,《南开日刊》上的一篇评论说道:
我们想想,现在中国的“家庭工业”、“手工制造业”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外国来的“机器制造品”打灭了。我们日用的东西,几乎离了外国舶来品便不行了。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做了外国的“工业战利品”,已经失了自己的“独立权”。我们如果不把这独立权恢复转来,有甚么方法,可以达到我们“国民自决”的目的呢?所以我们今天顶要紧的就是要能够“国民自给”。中国人方才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方才有主张国民自决的勇气,方才有实行国民自决的力量。
不错,不错,大家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大家在那里提倡国货,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大家所提倡的国货,是不中用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些物品,和舶来品竞争,已经打过好几次败仗的了。今天靠着大家的“爱国狂热”是可以畅销的,明天这群众的“爱国狂热”减少了,中国的市场,仍旧要被“舶来品”占领去的。所以我要大声疾呼的向着中国的工商业家说几句话:
(一)赶快的去你们的旧脑筋来相信科学。
(二)赶快集合你们的力量,办一个大大的“化学工业试验所”。
(三)赶快的把工商界和学术界用有力量有系统的组织打成一片。
(四)赶快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的大工业。
这些在90来年前的话,在今天读来,依然很耐人寻味。值得一提的是,跟五四抵货差不多同时,印度的甘地,也在领导一场针对英国人的抵货运动。五四的抵货运动,没有像甘地那样,提倡回到土纺车纺纱织布、土法煮盐的中世纪状态去,而是加快自己的民族工业的建设,应该说,这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事。最后,必须一提的是,在整个抵货运动期间,日本方面虽然多次提出抗议,在华的日人,大体上还表现比较克制,只有在日本势力特别大的山东和福建,才出现了一些冲突,也只有福建的福州事件闹得比较大,最后演成中日间的外交纠纷。也可以说,虽然说,是抵货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表现了最大的克制,尽量避免波及日本人,发生跟日本人的直接冲突,但是,对于中国的抵货运动,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应对,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也是运动最终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对抗,和平落幕的一个外部因素。当然,抵货运动中对人权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说明即使这样一个具有学习西方背景的运动,一旦有了爱国的集体道德诉求,自由会被压缩到何等地步。五四运动尽管有大量的自由主义者参与,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运动过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高扬,但自由却萎缩了,成为五四政治成果,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科学和民主也在激进步伐中变了味道,中国政治进一步在民主的轨道上步入下降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