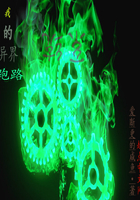红姑回过头来,耸起一只肩头,感兴趣地望着亦微,答道:"姓傅,傅松岩。你听过?在东北,黑白两道都得买他的账",接着她眼神一跳,整张脸突然闪出一种魅艳的光芒,"信不信由你,早年我跟他,有过一段情。这间酒吧,是他送给我。"江亦微信。一个女人,再沉沦,再疲惫,当想起自己曾经被爱的那一瞬间,她的脸,依然会亮如神迹。但现在亦微的担心被证实了-那个大闹婚宴的tough bitch,就是钟采采。
仲夏的西班牙开着一种花。
紫色,花瓣的质地很厚,从高高的树顶坠下来,发出很响的啪嗒声,像自杀,起风时落得一地都是。
亦微对植物一窍不通,却也认得这种花其实国内也有,只不过颜色没有那么艳,花朵也小一点。
客里无宾主,花开即故山。蓦地,亦微记起有一年冬天,唐清容在狂风中摇摇蹲下,对她说的"我好痛";还有那年承友喝醉了酒,额角流血,蛇一样蜿蜒,对她说的"坚持没有意义"。亦微心里很重,坠着她,不能动,不能起落。
胡安觉她今夜尤其静默,看她时,只见伊人正襟坐在副驾驶位,右手微微掩着胸口,面孔上没有表情,甚至没有年龄,无色无相,似一尊观音。
这时亦微却已想到那年初春,佻达的白色日光里,采采艳丽如蝶般靠近,她说"万幸我不懂得爱情",而如今她懂了,并且,没有办法假装不懂。爱情就是,天地之大,没有你,走到哪里我也只是异乡客。没有你,我如此孤独。
然而,人必须承受孤独,正如他们,承受生命。
但性爱又黑又甜,如火如荼,情人的嘴唇和手指都在激烈地邀约她,共赴温柔与暴烈。
于是江亦微再一次臣服了,黑暗中,她的双腿无比驯顺地延展,白蛇般盘绕上胡安的腰线。他的腰细实光滑,就像豹。他起伏如兽。
忽闻车外啪嗒啪嗒两声,她跟他都听到了,以为有人,就停下来,但两具身体仍缠在一处,四手四足,是欲念最原始的造像。听一回,没有动静了,他们再继续。餍足过后亦微才想到,其实那声音不过是那种紫色的花,落在车顶。